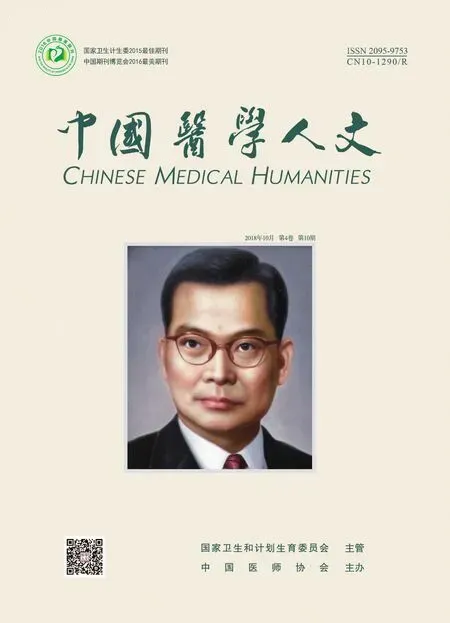我心在高处
——我与帕米尔高原的故事
文/燕娅娅
2012年我将油画作品《帕米尔的阳光和塔吉克的孩子》带到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将其陈列在了医院的环境中。在人们的观念里,油画的展示和宣传应该在美术馆或者展览馆,而不应该出现在医疗机构。
但是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将艺术作品和医疗环境融合在一起时,其实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让人类最本质的情感传递给来到医院的那些脆弱的、需要关爱、需要被呵护的人群,让他们知道这里有爱,有阳光,有温暖。我的画展示在医院的时候,已经不是技术和能力,而是艺术家的一份责任感,在这里展示的应该是一份很浓带着温暖的真爱,还有这种温暖之后的关怀。
在医院艺术长廊里,我经常看到来自大山深处的牧民,他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在油画作品前久久地驻足停留,也许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油画,也从来没有见过油画,更不懂艺术。但他们站在《尼撒汉奶奶》那幅作品面前,我看到他们眼里含着泪花,那一刻我知道了能不能看懂不重要,是否明白作品传达的寓意也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的作品是否

尼撒汉奶奶 油画/燕娅娅
能与他们的心相通,那才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的作品里有阳光,有鲜花,有歌声,有小鸟,其实我想让最美妙的色彩可以迎接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让他们降临世间后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到我作品中的这些温暖,让这些温暖和爱永远陪伴着他们。就像我画面中这些孩子永远沐浴在阳光中,在小鸟的歌声陪伴中茁壮成长。
我的作品被许多国内外的收藏家收藏,我其实也在想,我的作品难道只是需要被这一小部分人欣赏吗?只是需要装饰他们家的一个角落吗?肯定不是的。我把作品展示在医院之后,发现油画有了力量,有了温暖,有了爱,从此以后意义不同了。我也觉得,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特别自豪和幸福,因为我可以把温暖带给很多的人,我也想让我的作品中所有的爱能够永远留在所有看过作品的人心里。
19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帕米尔高原,此后30多年间去了20余次。现在去帕米尔高原,从北京当天可以飞到喀什,第二天换汽车六个小时就到了。但是30年前不是这样的,从北京要长途跋涉,路上非常不容易,还要在戈壁滩上颠簸七天,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到帕米尔高原。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年七八月份到达帕米尔高原,可以说是山上家家户户都成了我最亲的亲人。一说帕米尔,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因为我很多时间想着去但是去不了。在这期间我创作的一幅作品可以说留在了许多人的心里,这幅作品叫《尼撒汉奶奶》。
1985年冬天,我记得是11月底,那一年很奇怪,没有心思做任何事情,唯有一种迫切的心情——想上山,然后我背着包上山了,到了帕米尔高原之后,发现大雪纷飞,那一年非常冷。我每一次上帕米尔高原的时候都要经过尼撒汉奶奶家门口,这是去帕米尔县城唯一的必经之路。
从他们家经过的时候,每一次都能看见一个老人,她的个头很高,一米七多,永远穿着黑色的长袍,我每次去都会停下来跟她招手,然后再到各个牧场。到了牧场之后不是说你想返回就可以回来,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海拔比较高,我在山上几次发烧感冒,肺气肿,但是奇迹般都抗过来了。
上一次山不容易,我每一次去都想多待,每一次扛过来下山都有一个奇妙感觉,这个奶奶就是女神,她一直在保护着我,她在我心中的位置越高,我反倒越不敢走进她。我一直在画孩子和妇女,我不敢画老人。
2005年,我冒着大雪上山,从这个乡过去的时候停下脚步,我想这么大雪奶奶还会在山上吗,我抬头看了一眼,看见奶奶依然在山上招手,我就控制不住往奶奶站的方向走。这中间有八年时间都是奶奶跟我招手,我跟奶奶招手,仅此而已。八年之后的2005年,我顶着大雪,风雪中我看见奶奶正在向山下走,向我走来。我冲向山上,当我们俩面对面那一刻的时候,我看见奶奶双手伸过来,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看见奶奶的眼泪也像瀑布一样下来了,奶奶抱着我的额头亲了一下,我说奶奶我知道我怎么画你了,我一定回去把奶奶画出来。
后来,我在奶奶家住了一天,画了大量的速写和写生,我把奶奶扶回家,跟奶奶讲了很多我在北京创作的情况。因为奶奶当时身体不是很好,我说奶奶你等着我,我马上下山,把奶奶画好以后会第一时间拿来让奶奶看。因为奶奶一生没有拍过照片,她不知道自已是什么样子。奶奶18岁时丈夫去世了,带着六个儿子在帕米尔高原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到现在,可以想像,她多么不容易!
我几乎是流着泪在工作室40天一气呵成,创作了《尼撒汉奶奶》。谁都没有让看,我跑到楼下洗了一张照片,迅速到了机场,然后换汽车,奔向奶奶的家。特别神奇的是,因为奶奶有六个儿子,我不知道他在谁家,我挨个去找。
奶奶看见我手中的这张照片,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了,双手在颤抖,我当时想这张画成了,因为奶奶都可以画成这样,我相信能够感动她,也可以感动许多的人。2007年,香港地区政府邀请我去香港办画展,他们说在香港,人与人之间谈得最多的,是怎么挣钱,怎么做生意,而很少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你能不能讲山上的故事,告诉所有人有一个尼撒汉奶奶与你的真情。
在香港的画展很轰动,很多人去看奶奶,并且在画前献了花,很多人流着泪,留了言,有一大本写给奶奶的话。我抱着这些话重返帕米尔高原,特别想把这一本大家想跟奶奶说的话念给奶奶听,找了三天,跑遍了帕米尔找不到奶奶,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不告诉我,我后来到她四儿子家的时候,她儿媳妇抱着我哭了,我当时想,奶奶可能真的没有离开人世。
这幅作品成了我很难超越的一幅作品,我把这个作品展示在中国美术馆,展示在国外,展示在很多地方,其实很多人看到这幅作品时他们不知道谁是燕娅娅,也不知道奶奶是谁,但是很多人站在这幅作品面前流泪,这让我备受感动,让我知道其实一个艺术家创作一幅作品不是说只是这个形象好看不好看,这个形象你感不感兴趣,而是这个作品是否把帕米尔真正的灵魂表现了出来,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作品。
完成这幅作品之后我在想,帕米尔跟我之间的深情,已经不是因为在山上,跑得多了,待得久了,住得时间长了,我们之间的情谊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
记得有一次,也是去采风,我越走越远,这个地方几乎没有路,车很难过去,你不能往下看,下面是悬崖,没有人敢进那个乡。我一直想找与世隔绝的塔吉克,想看到从未走出过高原的塔吉克人是什么样子,很多人劝我不要进去,我说我必须进去。
当时正好赶上边防武警派出所巡逻,他们要进山,说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我说当然了。我记得我们有七八个人,我在队伍最后面走,我远远看见有一个小山,山下面有一个黑色的小土房子,有一个老头领着一个小女孩站在土房子门口,我低着头在后面走,走着走着感觉有一个小女孩冲着我过来,我抬头的时候惊呆了,小女孩不会汉语,但妈妈两个字说得很清楚,冲过来抱着我就喊妈妈。
我把孩子抱在怀里,我说你这么小,在这个地方没有人照顾你,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我要永远照顾你,很多人说艺术家容易冲动,你想好了,这是一个孩子,你如果带她走,那就得一辈子,我说我相信,我的画能养活我,也一定能够养活这个孩子。我后来这个孩子一直带在身边,现在已经17岁了,上中学了。
这些年我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有过两次很大型的个展,也在国外做了很多个展,很多人对我的画给予高度评价,但是我也在想,其实这么多的作品,无论展示在甘肃省妇幼保健院还是中国美术馆,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的价值在哪里,艺术家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现在,我也看到很多作品在市场上价格炒得很高,而且是越来越高。好像衡量一幅作品好坏是以价格来确定的,但是我也在想,不管别人怎么创作,我的心是永远在帕米尔高原。有一句话一直在提醒我:你是帕米尔的女儿,你是昆仑山的女儿。其实每次画画的时候,我一定要听着帕米尔的音乐,这样我始终知道我是在为谁创作,我创作的作品应该传递的是温暖还是热情,还是关爱,还是更多的去卖一点钱呢?
其实一个艺术家每年都要创作很多的作品,但是作品的价值应该是艺术家自己去把握,我相信只有用心去创作,用心去感受,作品才能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我最希望的是我的画能够永远留在所有人的心里,这才是我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