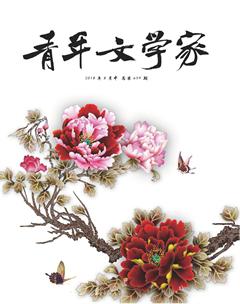试论大洼诗佛的“平淡”诗学
摘 要:大洼诗佛是日本江户后期的汉诗人,其《诗圣堂诗话》是日本反古文辞派诗话代表作之一。诗佛受其师山本北山以及中国明代袁宏道思想的影响,提倡诗应求新奇,而后至平淡,形成了诗佛独特的“平淡”观。
关键词:《诗圣堂诗话》;大洼诗佛;平淡
作者简介:张悦(1994.1-),女,汉族,江苏扬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1
一、关于日本诗话
诗话是关于诗人以及诗歌的理论批评形式。诗话之名源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正如其开头所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诗话主要谈论诗人以及关于诗歌的逸事,从而确定了诗话的本质。之后南宋的许渊在其《许彦周诗话》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不仅对诗话内容进行了说明,同时也对诗话的创作目的进行了阐述。
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诗话作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体裁,也被传到了日本。早在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的文人对于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空前的热情,纷纷模仿中国进行汉诗创作。汉诗的隆盛对于诗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将汉诗文的作法规则进行全面的介绍,日本的空海大师编纂了《文镜秘府论》,这部书不仅收录了王昌龄、沈约的诗论,还保存了大量六朝到唐代的诗学文献,对于日本汉诗创作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虽然没有以“诗话”命名,但是作为日本最初的诗论著作被看作是诗话的前身。到了平安后期,汉文学衰落,再到镰仓时期,五山禅僧兴起了汉诗文创作之热。这个时期出现了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作品,那就是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这部作品不仅引用了许多中国唐宋代诗人的诗歌评论,还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到了江户时代,迎来了日本诗话创作的隆盛期。这个时代儒学文人辈出,进行了大量的汉诗文创作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诗话作品的出现。并且由于诗文观的差异产生了4种主流诗话流派。江户初期,以藤原惺窝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主张“诗言志”的教化功能。到了元禄年间,以太宰春台为代表的反朱子学派提倡诗歌应该以传达人情为主。而到了享保年间,以荻生徂来为代表的古文辞派标榜复古主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是,这一学派一昧主张学习“格调”,模仿古人的诗句,结果陷入了模拟剽窃的境地,逐渐衰落。到了文化文政时期,反古文辞派诗人倡导诗歌要体现诗人个性,力求新奇。一时之间诗坛大力排斥模拟剽窃,诗人纷纷追求诗歌的新奇性。诗佛不仅主张诗贵新奇,更推崇这种诗歌经由新奇,达到平淡的一种境地,其《诗圣堂诗话》中就鲜明地提出了这个观点。
二、“平淡”的本义追溯
“平淡”一词根源于“淡”,“淡”字可以追溯到《老子》以及《庄子》这些思想作品中。《老子》以“淡”论“道”:道之出口,淡兮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也就是說“道”因其“淡”而拥有用之不尽的效用,这里用“淡”来说明了“道”的本质。而在《庄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澹然无极而衆美从之,此天地之道也”,将“淡”作为“万物之本”以及“天地之道”也就是指出了“淡”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之理。老庄中的“淡”大体同义,将“淡”与自然万物本质相连,赋予了“淡”哲学本体的意义。在这之后,最早可以确认“平淡”一词的文献是三国魏刘邵的《三国志》,在这本书的开头说:“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贵,必平淡无味”,这里将“平淡”作为评价人物的一种资质,将“平淡”作为“中和”的本质。“淡”最早被赋予诗学意义,用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是在南北朝梁刘勰编纂的《文心雕龙》中。但是在此部作品中,“淡”只是作为对于诗歌风格构思过于简素的一种负面评价。而真正一改“淡”的负面评价的是晚唐的司空图,他在《二十四诗品》中专设“冲淡”品,认为“淡”是一种妙趣横生的境界。到了宋代,“平淡”就被视作诗歌的最高境界。
三、诗佛的“平淡说”:渐老渐熟之境
大洼诗佛在《诗圣堂诗话》中论及僧侣的平淡之诗时说:
或毀緇流之詩云、不免蔬筍之氣、余以為不然、緇流之詩之所以可愛者、以其有蔬筍之氣也、余譬之於花。海棠花也、牡丹花也、李梅桃杏齊皆花也、雖有黃紅紫白之異、要之不過妝點一種之春色耳。緇流之詩、求之於花、即梅也、余愛其字瘦句寒味淡也。
诗佛以“梅”作喻,高度评价僧侣诗的平淡,可以看出诗佛对“平淡”的偏爱。而对于如何到达“平淡”之境,他这样说道:
然平淡不經奇險中來、則徒是村嫗絮談耳、全無氣力焉、故學詩先覓奇險、而後平淡、詩到平淡、而詩之能事畢矣。
要达到“平淡”必须先历经“奇险”,这里所说的“奇险”可以理解为作诗不踏袭古人,追求自我新奇的一种倾向。最早将“奇”引入诗学范畴的是梁的钟嵘,他说:“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高度评价超越世俗的“奇”,但是到了宋代,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一昧追求“奇字僻典”、“拗律险韵”的技巧,诗文一度陷入难解境地。为了矫正这一诗风,宋人提出了“平淡”的理念,但是这种“平淡”并不是“奇”的对立概念,而是与“奇”互补,一种新的境界。诗佛引用苏轼《与二郎侄》中的话说明了到达“平淡”之境的路程:
東坡云、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作诗最先追求文辞地华丽,渐至成熟,到达“平淡”之境。“平淡”的获得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一种渐进练习的过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诗佛诗风的变化。诗佛对于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卜居集》评价不高,原因在于该诗集中的诗大多为蹈袭前人之作,缺乏新意。而在后来的诗集《诗圣堂百绝》中就多见一些富于变化的诗,并不是原原本本的复刻古句,而是利用古句之形,塑造出一些绝妙的意趣,逐渐练就高超的作诗技法。
诗佛深受宋诗平淡理念的影响,将“平淡”与“奇”相关联,提出了自己的“平淡说”,“平淡”是经由“奇”而达到的渐老渐熟的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