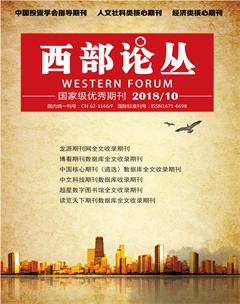道德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关系之思
都东平
摘 要:汉纳·皮特金曾提出道德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区分,而对这两种话语的关系之思考可以让我们加深对这两种话语的理解,从而允许政治哲学、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以一种更加契合的方式施加对政治的规范。本文通过分析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墨菲的“激进民主”中蕴含的两种话语的关系,揭示政治话语内在的政治向度、道德话语对其的忽视,从而反思这两种话语之间应有的关系。
关键词:道德话语 政治话语
汉纳·皮特金曾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与正义》一书中,将道德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作出了如下区分:“道德话语是个人的对话,政治话语关涉公众、共同体,并且一般地总是发生在成员之间……离开了相互抗衡的主张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领域就没有了主题;就无需做什么政治决策。”我们将从这个角度,观察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M.桑德尔等人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和对他们的批判。
罗尔斯:个人道德语言替代政治语言
罗尔斯认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目标在于提出“正义的一个政治观念,它不仅要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合法化提供一种公平的公共基础,而且还要有助于确保代代相沿的稳定性。”搭建这种“公共基础”“稳定性”的基石,应该由个人对一种政治的重叠共识来建立。在这里,罗尔斯以 “康德式构造主义”的方式建立个人:个人同时服从关照个人利益的理性、和关照道德、社会合作的合理性;由此,个人被视为理性的道德人。
社群主义者揭示出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主体背后的个人主义逻辑,并批评这种抽象的、理性化的个人主体遗忘了政治和群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不能建构出处于共同体之中的、参与共同体政治的形象;
而施米特认为,纯粹、严格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不能产生任何政治概念,因为个人主义要求个人必须是起点和终点,从而在实际的政治层面上“出现了一种自由政策。它以爱争论的、对立的形式反对政府、教会或其他束缚个体自由的机构、制度”(可以联想到许多美国喜剧中对政府的抨击、不信任、讽刺挖苦已然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这背后“不是一种自由政治学,只是对政治学的一种自由批判”。因而对于施米特,自由概念只是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徘徊(这与罗尔斯的“康德式构造主义”恰相对应),但唯独回避了政治。结合前述的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使用的是一套个人的而非群体的、道德的而非政治的话语。
社群主义:以群体道德语言替代政治语言
社群主义者从自由主义的“权利先于善”走向了“善先于权利”,并且这一转向和市民共和主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强调积极参与政治的“市民德性”以及围绕这种“市民德性”所建立的共同体所共同分享的“共同善”。“共同善”指向了共同体内的道德次序,在其之上才能建立共同体、政治、个人权利等范畴和概念。而“市民德性”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对人作为“政治动物”的界定,其中个人的善和城邦的善的统一性直接支持了后来市民共和主义中的市民政治参与对于个人的至高重要性。
墨菲却指出了这背后蕴含的道德话语。墨菲在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于“权利先于善”和“善先于权利”的无休止的“两难”间发现,他们两方已然都混淆了两种善:实质性的道德善和制度性的政治善——前者标识的是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底线,而后者是民主政治的底线。自由主义者将两种善都试图划入私人并对其中立,因而取消了政治的公共维度,只能从个人出发并回到个人;社群主义者则将两种善都置于公共领域,因而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不分公私。同时,社群主义所建立的实质性的、同一性的共同体,和自由主义的理性个人一样,没有为共同体内部的冲突性留下空间(因而内部冲突很可能被极端化,如反对者被描述为“民族的敌人”),因而只是以群体的而非个人的道德话语代替了政治话语。
墨菲式的分离:是否超越了当前矛盾?
墨菲通过分离实质性的道德善和制度性的政治善,間接分离了道德语言和政治语言;但是,这种间接分离是否成功?
墨菲自己的政治主体便是在以两种善的分离为前提下建立的:它认同共和主义是政治应有的规则。这里的“政治应有的规则”是指这样的行为规则、前提,即必须把其他人看成自由和平等的人(政治善),而不论这一行为有任何具体的、实质的目的(道德善)。墨菲鼓励以这一标准重塑政治主体的“斗争性”,以此划清认同这一概念的“我们”和不认同的“他们”。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政治主体的观念,在身份政治的观念市场里其实是很无力的:共和主义本身已充满争议,而这种争议在普通民众看来是十分专业化的,相比“民族”、“种族”、“阶级”、“宗教”就已是抽象的、学术的、不直接的。因而这一“斗争”似乎成了学者间的斗争,而其期待的围绕共和主义的“团结”似乎也与民众绝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墨菲分离政治善与道德善时,她却未能在重提“斗争”时,支撑起“团结”的概念,这一“团结”在民主革命时,曾被个人道德话语所吸纳,以“平等”“博爱”为名会聚起革命者,也曾在民族独立时,被群体道德话语所采用,以“解放”为名召集起独立军,从而将道德话语政治化。政治话语的两个重要向度在这里显现:个人—群体、斗争—团结,任何一种偏向这两个向度中的一极的话语似乎都将趋向道德话语:当今的自由主义忽视群体与斗争、社群主义忽视个人与斗争,而墨菲的共和主义忽视了团结,它们都最终成为了道德话语。
可以这样说,“分离”“代替”都不能很好地被确立为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分离”“代替”视域下的两种话语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失去了政治的某种向度,本身便是以道德话语展开的,因而对具体的政治实践而言可能过于抽象与理想化。政治哲学、伦理学或是道德哲学固然不会满足于对政治的纯粹的“实然描述”;但沉迷于忽视了政治向度的道德话语,却也不利于其本身所期待的对政治的规范、约束;尤其是当时代的问题正召唤智慧、思考时,如何让道德话语更有效地介入政治,是极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汉纳·皮特金.维特根斯坦与正义[M].贝克莱. 1972, P216
[2] 罗尔斯.一种重叠共识理念[J]. 牛津法律研究.1987(7) 第一期:P12.
[3] 罗尔斯.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构造主义.[J].Philosophy. Vol.77, 1980(9), 第九期
[4]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 Rutgers,1971,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