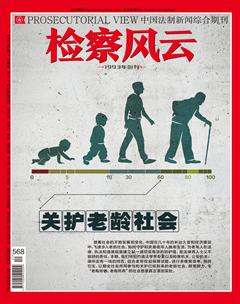老龄社会权益受损案评查报告
庄嘉

人口的老龄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极易显现的一种现象。在世界各国的人口结构比例中,人口的老龄化已然是普遍现象,比如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若某国或某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标志此国或此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回溯我国,根据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这意味着我国早已迈入了老龄社会。另据《“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至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至2.5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提升至17.8%”。
老年人权益受损的动态分析
老龄社会,在社会阶层隔离、社会资源集中向下一代倾斜的现实面前,独生子女父母已是老年人群主体,少子无子家庭增多,高龄、失能、空巢等多种现象叠加,渐渐给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当下,老年权益保障俨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难题!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我国老年人享有的权益主要包括物质保障权(第4条)、获得赡养权(第2章)、社会优待权(第36条)、婚姻自由权(第18条)、诉讼权(第43条)等。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赡养、扶养不作为(如拒绝履行赡养、扶养义务,又如不履行赡养、扶养协议);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如阻止老人再婚);侵害老年人合法财产权(如侵占、挪用、冒领养老保障等资金);歧视、侮辱、诽谤老年人(如故意大声谩骂老人);虐待、遗弃老年人或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侵害老年人的居住权(如提供的住所条件差)……近年来,老年人更是成为各类不法分子的香饽饽,从营养保健产品陷阱,到“亲情诈骗”,从人身权到财产权,从民事层面到刑事犯罪,刑民交叉的情况日益凸显……
【从“养儿防老”到“养老防儿”】
目前,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仍是“养儿防老”。有的家庭中,60多岁子女赡养八九十岁父母的情况并不鲜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子女应当“常回家看看”,地方性法规(如江苏省、苏州市)亦规定,子女如果不“常回家看看”,可能拿不到一分遗产……由此,法律为“养儿防老”正名。但事与愿违,有些子女偏偏就是對法律的规定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违背传统道德和伦理,有悖公序良俗。不养老就算了,“啃老族”却演变为社会群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俗语有云“养儿防老”,今朝演变为“养老防儿”!百善孝为先,如今演变为不孝者屡见不鲜。
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涉老民事审判白皮书》,“截至2017年9月30日,静安区人民法院涉老民事审判庭受理的1004件涉老案件中,权属、侵权类纠纷239件,合同类纠纷581件,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174件,特别程序10件。其中不乏因‘啃老引起的民事纠纷”。尽管一些地方性法规已然开始对啃老说“不”(如《吉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从立法层面为老年人拒绝啃老提供“法制保护伞”,然而“啃老”依旧难以根除。多数老人往往出于息事宁人、家丑不可外扬等考量,寻求亲属调解、自己忍气吞声,至多是寻求居委会或村委会居中调停。即便真走上了打官司这条道,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之事”,最后老人妥协的也不在少数。
比“啃老”更令人难堪的还有老年人的婚恋自由权,也就是所谓的“黄昏恋”。热播剧《我的前半生》中,热情外向的罗妈妈遇到自己的晚年幸福崔叔叔,两人的“黄昏恋”便遭到了崔叔叔儿子的强烈反对……阻止老人再婚往往成为家庭纷争的导火索,甚至成为继承私欲的挡箭牌!
【从“家庭暴力”到“机构虐老”】
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从立法层面对“家暴”依法惩治,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措施的出台更是让被家暴者看到了用法制之剑斩断阴霾的曙光。比如,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母亲罗兰与儿子杨苗之间因房屋权属发生激烈矛盾。2016年7月8日、12月30日,2017年6月13日、7月25日,罗兰先后4次报警,称杨苗损毁家中物品,电话线被剪断、餐桌腿被踹断、房门门锁被撬开,杨苗竟还辱骂、推搡罗兰。2017年10月,罗兰忍无可忍,终向“北京老年维权热线”求助,依靠北京老年维权服务工作站提供的法律援助,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同年10月31日,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核后认为,罗兰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第27条的规定,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儿子杨苗对罗兰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骚扰、跟踪、接触罗兰;责令杨苗迁出罗兰的住所。然而,罗兰的个案无疑是幸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对于家庭暴力而言,对于老年人而言,客观上存在运用难点,不少被家暴的老人还是需要依附在子女的庇护之下。据《法制日报》报道,很多地方保护令支持率少于20%。
在家中得不到安宁之时,养老护理机构似乎成为不少老人的可靠选择。然而,质优价廉、口碑好的养老护理机构常常一床难求,而纯营利性质的养老院费用高昂。近年来,养老护理机构不尽职、不尽责,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比如,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民政局下属敬老院虐待老人事件。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被虐待的72岁老人张老伯于2018年7月经医院检查,双足严重感染,局部溃烂生蛆,趾趾周围组织腐烂。显然,事发敬老院存在着明显的过失。区民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看护不周到这个地步,当地上级部门居然对老人的健康情况毫无察觉。不得不说,养老护理机构“置之不理”与主管部门的“闭目塞听”存在着紧密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发布的《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2012—2016)》,2012年至2016年涉老民事案件审判中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突出领域就涵盖了养老机构服务领域。该白皮书更是指出,“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养老机构服务进行社会公示,监督其善待入住老年人”。
【从“保健欺诈”到“亲情诈骗”】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人可支配财产正在增多,部分老年人在经济上已然处于阔绰、甚至富裕的阶层。这恰恰已沦为不法分子侵犯的主要对象。诚如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健盛所言,“当前的保健品产销链已经演变出环环相扣的产业分工。分布在社区的营销点,只负责保健品的体验和展示,不进行实物销售。接着,举办旅游或者讲座,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产品推荐会。当你被忽悠进去而对某款产品感兴趣时,他们会告诉你,该产品在这里买不到,我给你一张优惠券,你可以到指定地点购买。”此种分步走的营销模式将虚假营销和实际销售分开,给执法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而情感戏、专家牌、会销现场的鼓噪等骗术的叠加使用,往往令深陷其中、缺乏辨别力的老年人被蒙蔽入坑。2017年3月11日,青岛一位60岁老人在海边身亡,留遗书称被保健品“坑死”的新闻,便引发了各界的极大关注。
此外,亲情诈骗也成为不法分子引诱老年人“自愿出血”的不二渠道。据上海市反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中心平台统计,“自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上海‘联动劝阻工作通过各类预警系统劝阻电信网络诈骗潜在被害人17.3万人,避免经济损失人民币43亿余元。其中,不乏针对老年人实施的‘亲情诈骗”。不法分子依托金融、电信等部门的漏洞,获取犯罪对象老年人的个人信息,通过打电话、指定第三人上门等方式,在隐姓埋名的情况下欺诈、恐吓、诱骗老年人,让其误以为至亲缺钱,主动自愿将存款打到指定账户,然后提取现金。比如,中央电视台于今年8月17日报道的“上海老人遭遇诈骗交赎金,民警发现成功劝阻”……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老年人权益受损多发归因
老年人的权益容易遭受侵害,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存在弱点,如迫切冀望延年益寿、崇尚勤俭节约、空巢老人缺乏亲情关怀;另一方面则碍于救济途径不合理和社会公共服务不健全。
【维权救济途径并非坦途】
在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体系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核心。正如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刘金霞教授所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老年权益保障方面的小宪法”。然而,仅仅有核心还远远不够!因此,地方性法规显得尤为重要,它就是执行细则。但从总体而言,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规定仍然较为笼统,内容不够具体明确,针对性措施不具可操作性。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但对如何追究實施上述行为的违法行为人,却没有更具操作性的规定予以衔接。又比如,失独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养老权益如何保障?与一般老年人相比,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是否区别?再比如,根据国家民政部的规定,民政救助对象限于优抚、低保、“三无”“五保”等部分老年人,却没有涵盖全体老年人,尤其没有适用于失独、孤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由此可见,我国的老年立法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在制度设计、配套规定、范畴厘定等方面与当前老年人需求存在不适配,老年人仍然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法律支持。
在立法滞后的背景下,司法和执法亦面临困境。对老年人而言,若依托现有的一般诉讼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势必将增加老年人权利救济的负担,其本身法益受到迫害的紧迫性无法得到即时缓解。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于诉前财产保全,其适用范围有严格限制,获得法院支持的概率亦不高。而保健产品欺诈的归罪,更多的在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暴利和广而告之的虚假宣传。那么,现有的规则该如何规制此种商业模式?即便是该商业模式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会销”(即以集体开会的形式,促使老年人相互影响,在群体认同感中制造对产品强烈的购买欲望),在法律法规层面亦未被认定为非法,只能作为一种商业手法看待。因此,保健品欺诈案件多属于工商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监管的范畴,至多受到行政处罚,如同隔靴搔痒。
【社会养老服务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机制散见于《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19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国办发〔2017〕52号)等职能部门规定的文件中,但并不健全,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存在缺失。
以“老年护理”为例。根据民政部联合质检总局、全国老龄办等六大部门于2017年3月22日印发的《关于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民发〔2017〕51号)的规定,只有通过国家人社部指定的老年护理专业培训,并考取《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才能获准上岗开展老年护理工作。养老机构对专业从业人员配置比例不得低于30%。但实践中,不少养老机构的老年护理员等工作人员均不符合上述职业准入机制,造成了类似浙江敬老院95岁老人被虐待事件的发生。
又比如,“老年监护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全国人大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民法总则》,第二章“自然人”第二节“监护”中专门规定了成年(包含老年)监护制度。由此,我国从法律层面建立了老年监护制度。但实践中,老年人监护常常由于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督,造成老年监护制度流于形式,监护人侵害老年被监护人的案例并不鲜见。
构筑老年权益保护的多重围栏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人口“银发浪潮”即将袭来。除了老年人自身做好防骗防盗、提升自身辨识素养和知识架构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更应为老年权益保护架起多重围栏,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特殊权益。
国务院于2017年3月6日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完善老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因此,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机制尤为重要,将成为老年权益保障的第一重围栏。厘清国内现有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从周延和即时视角完善立法体系已是当务之急!诚如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美老龄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永杰所说,“在社会法领域当务之急是健全老年劳动权益保障法、养老服务立法、老年救助法、老年福利法、残疾人特殊保护法等相应立法。”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颁布的《广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已经对“啃老”开例,明文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以及其他亲属向老年人要求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将共同生活的老年夫妻强行分开赡养,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的,若构成犯罪,则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啃老刑拘”一时间广为热议。
又比如,《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均规定了独生子女的带薪护理制度,方便其照顾年满60周岁患病住院的父母,彰显了立法与时俱进,破解当下难题的社会功能。
从司法层面而言,可以从老年人维权的角度设计一套行之有效、可操作性强的机制。在机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厘清涉老案件中民事、行政、刑事三者的分水岭。上海市消保委委员、律师江宪认为,“在保健品监管中,要厘清三种关系:一种是民事法律关系,比如消费者就某样保健品进行投诉,是个案处理;另一种是行政法律关系,比如虚假宣传、无证经营、成分非法添加等,应由工商、食药监等政府部门处理,是集中案件处理;还有一种触及刑事责任,则由公安司法部门处理”。
在诉讼机制方面,是否可以根据老年当事人的心理、生理特点,结合案情,对老年当事人采取特殊的司法保护措施(借鉴诉前财产保全)?是否可以借鉴未成年检察工作来开展老年人检察工作,或者公益诉讼机制,由公诉部门统一搜集证据材料,对老年人集体权益进行维护?在诉讼成本方面,是否可以借鉴《广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的“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法律服务”……通过类似于全国老龄办、最高法、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法律维权工作的意见》(全国老龄办发〔2016〕102号)的形式,将“司法护老”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推崇,形成老年权益保障的第二重围栏。
在社会养老服务层面,党的十九大早就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因此,构筑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综合体系势在必行。以“长期护理”为例。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人社厅发〔2016〕80號)规定:“在青岛、上海、广州等15个城市探索建立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但实施至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未真正建立起来!而邻国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的实践经验值得参考。日本早在2000年4月就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法》。之后,日本政府又进行了五次改革,与时俱进地创立了针对长期疗养的护理医疗院,提高收入较高者的个人自付比例,减低低收入者的保险负担,为日本国民提供了高品质的长期护理服务。
当然,保护老年人权益,不仅需要从老年人自身、立法、司法、养老服务层面下重拳,更需要政府、社会、机构、家人各方面久久为功。维护今天他们的权益,便是保障明天你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