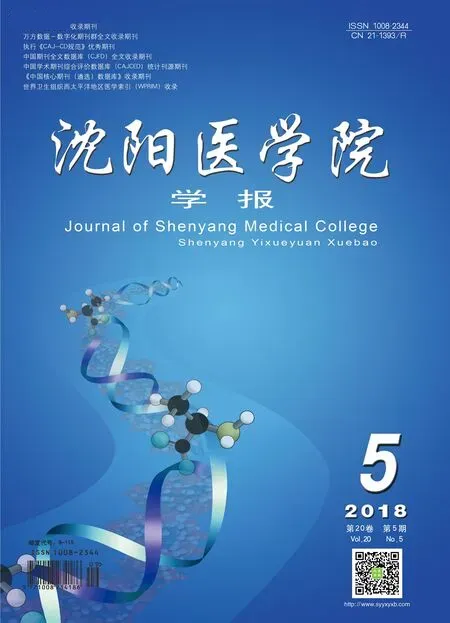从进化生物学观点谈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的关联机制
周明生
(沈阳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辽宁 沈阳 110034)

胰岛素抵抗综合征又称为代谢综合征或心脏代谢综合征[1]。代谢综合征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而是一组包括腹围增加、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和胰岛素抵抗的临床症候群,常伴有心血管系统的功能损伤,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2-3]。代谢综合征在发病机制上与心血管疾病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增加氧化应激、脂质和葡萄糖代谢缺陷、慢性低度炎症和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等。因此,也有些学者提出应将代谢综合征伴有肾功能损伤、蛋白尿、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左心室功能失常等明显心血管损伤的状况称为“循环综合征”[4]。
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是代谢综合征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重要组成部分[5]。临床研究表明,50%的高血压患者伴有高胰岛素血症和糖耐量异常,80%的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有高血压[6]。胰岛素具有调节代谢,刺激血管内皮细胞生成一氧化氮(NO)从而诱导血管舒张的功能。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不仅存在于胰岛素敏感组织中,而且还存在于心血管系统中。一般把损伤血管胰岛素信号通路的状况称为血管胰岛素抵抗,血管胰岛素抵抗可引起血压升高和心血管疾病[7]。
人们常把胰岛素抵抗与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联系在一起[8]。然而,在人类进化史中,胰岛素抵抗可能作为一种生理适应性机制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饥饿、感染、外伤等应激情况下增加生存的机会。同样的机制在现代生活环境中被不适当的激活而导致高血压、胰岛素抵抗或代谢综合征[9]。本文从进化生物学的新角度,论述了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之间的关联机制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对它们的影响。
1 胰岛素抵抗作为一种生理适应性机制促进人类生存
在长期的生物种族进化过程中,生物种族的生存要依赖于机体进行能量储存来抵抗饥饿,激发免疫反应来控制感染[10]。饥饿诱导的生理性适应包括增加脂质氧化、酮体合成、葡萄糖的生成和摄取,以及降低葡萄糖的氧化,这些反应有助于减少蛋白质的丢失。由于脑组织主要依靠糖代谢获取能量,脑组织对葡萄糖的缺乏非常敏感。在饥饿、感染和妊娠的状态下,机体可通过胰岛素抵抗和其他的生物适应性反应增加葡萄糖的储存和维持血糖的浓度[10]。
胰岛素是一种促合成的激素,在肝脏和骨骼肌中可以通过增加糖原合成而增加葡萄糖储存,在脂肪组织中通过增加甘油三酯合成的方式而增加脂肪酸储存。在胰岛素抵抗时,脂肪组织葡萄糖摄取和糖原储存能力降低、甘油三酯降解增加、游离脂肪酸和甘油向肝脏转移增加、肝脏糖异生增加引起血糖升高。此外,胰岛素抵抗还可促进能源物质的再分配,如胰岛素抵抗时由于血糖浓度升高可保证大脑和免疫系统葡萄糖的供应和利用[10]。因此,抑制胰岛素信号通路可认为是在饥饿、感染、妊娠等应激状态下的一种生物适应机制。然而,长时间持续激活此机制,可能是形成代谢综合征的基础[10]。胰岛素不仅调节能量代谢,而且还具有复杂的心血管效应,如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生成和释放NO、诱导血管舒张、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炎症等心血管保护效应,并通过激活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通路引起血管收缩、平滑肌血管增殖和炎症等血管损伤效应[1]。此外,胰岛素还可促进交感神经兴奋,增加肾脏对钠离子的重吸收。胰岛素抵抗时,胰岛素激活NO信号通路可能选择性的受损,代偿性的高胰岛素血症激活MAPK通路,引起血管收缩、炎症、水钠潴留和血压升高[1]。另一方面,在饥饿、感染等应激状态下,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血压升高可能是一种增加脑血流灌注的生理适应性机制。
2 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常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慢性系统性低度炎症有关
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被认为是一种西方文明性疾病,与过渡能源摄取的不健康生活方式以及慢性系统性低度炎症有关[11-12]。在古代,获取食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食物丰富时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能源用以抵抗可能随之而来的长期饥饿是古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机制[13]。现代人类遗传了古人类存储脂肪的特性,然而现代生活由于丰盛的食品供应,常有过多的能量和盐分摄入以及运动不足,从古人类遗传下来的节俭基因在现代生活方式下很容易导致体内能量和脂肪积累过剩[13]。当脂肪组织储存脂肪的能力超过安全储存限度时,脂质就会流到非脂肪组织中,引起慢性的系统性炎症,引起高血压等代谢综合征[14]。
肥胖可看成是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而引起的一种能量不平衡状态[10]。脂肪细胞是机体重要的能源储存装置,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各种应激激酶、炎性细胞因子和化学因子等,这些脂肪分泌物质统称为脂肪素。脂肪素参与脂肪储存、能量代谢和炎性反应等生理和病理反应过程的调节。目前认为过度的能量摄入和脂肪储存可以增加脂肪组织氧化应激反应,增加氧化应激反应可反过来抑制脂肪细胞分化、增加免疫细胞向脂肪组织浸润等,导致脂肪组织内分泌功能失常和慢性炎症[15]。
肥胖介导的炎症可能与增加脂肪组织炎性细胞浸润密切相关[16-17]。在肥胖状态下,一些炎性细胞因子可能被释放引起巨噬细胞激活,而巨噬细胞在白脂肪组织浸润可引起脂肪组织的慢性炎症并转变成系统性炎症[16,18]。受到巨噬细胞浸润的白脂肪组织可转变成一个具有高度分泌活性的内分泌器官,分泌一系列的脂源性炎性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单核细胞化学趋向因子、白介素-6等。这些炎性细胞因子不仅能在脂肪细胞中诱导慢性炎症,而且可进入血液循环,抑制胰岛素信号传导,导致全身性的胰岛素抵抗[15-17]。因此,慢性炎症被认为是肥胖引起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主要机制[17-19]。
3 从进化生物学观点看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的关联性
适者生存是生物进化的一个最高准则。数百万年来,从低级生物到人类都面临着饥饿和感染的生存压力[10]。多细胞生物的生存能力主要依赖于生物体能够在营养物质不足的状况下储存能源以及满足感染等应激状况下的高能源需求[20]。免疫系统是生物体应对感染等应激状态下最重要的反应体系,需要有足够的能源支持来保证其发挥正常功能。这些能源主要来自从外部摄取能量物质和利用内部储存的能量包括糖原、蛋白质、甘油三酯或游离脂肪酸等。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的紧密合作是生物体适应环境赖以生存的基础[11,21]。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代谢和免疫系统相互依赖,一些调控能量代谢和免疫功能的基因从低级生物到哺乳动物都被良好的保存下来。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一些调节能量代谢信号分子和免疫反应的信号分子之间有相互调控效应[10,22],如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PPAR-γ)是一个促进脂肪细胞分化的主要信号调控分子,也是调节T细胞在脂肪组织聚集和转化的信息分子[23];瘦素是一个重要的调节能量平衡的脂激素,现已证明瘦素可调节胸腺内环境稳定和IL-1和TNF-α等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22]。
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之间的密切合作是维持生物体内环境稳定的重要基础。炎性反应通过诱导胰岛素抵抗增加血糖浓度,维持心、脑等重要器官和免疫细胞的能量代谢抵抗感染。心、脑和白细胞等被认为是胰岛素不敏感组织,主要依靠血糖提供能量[24]。因此,急性炎症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对控制感染可能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可以从机体对急性炎症的时间反应过程来了解自然选择机制在协调免疫系统和能量代谢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5]。急性感染性疾病常常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在感染开始的2~3 d启动先天性免疫反应,随后的3~4周激发获得性适应性免疫反应[25]。由于感染所致的体质虚弱和呕吐可引起能源物质的摄入减少,而急性感染性疾病本身也是一种消耗性疾病,需要动员脂肪、骨骼肌等能量储存组织的能量[10]。感染组织释放到循环血液中的炎性细胞因子可诱导脂肪和肌肉组织的胰岛素抵抗,减少这些组织的能源消耗、代偿性的高胰岛素血症、高血糖和高血脂,有利于机体防御和控制感染[10]。脂肪和肌肉组织中储存的能源通常可维持3~5周,这个时间与获得性免疫反应抵抗外界感染所需要的时间非常吻合。如果获得性免疫反应不能在这个时间段内做出反应,受感染的机体就可能会死于能源耗竭[26]。除了能源消耗,急性炎症还常伴有水的丢失。水的丢失包括受感染组织的局部水的丢失以及皮肤出汗、呼吸道的挥发等全身水的丢失[25]。为了补偿水的丢失,在急性炎症状态下,水潴留系统常被激活,比如激活交感神经系统、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髓质系统等神经体液机制[25]。有趣的是,这些参与调节水潴留的激素如血管紧张素Ⅱ和醛固酮也具有促炎作用,它们在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27]。
水潴留和能量存储的调节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并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被选择性保留下来以抵抗炎症反应和增加生存能力[9]。然而,由于人类还没有进化出一个平衡水潴留和能量储存的调节机制,因此被现代生活所激活的水潴留和能量储存机制可能增加高血压、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9]。
4 钠盐是高血压和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另一个联系?
根据血压对盐反应的不同,高血压可分为盐敏感性高血压和盐抵抗性高血压。动物和临床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和盐敏感性高血压密切相关[5,28]。与盐抵抗性高血压相比,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更易发生胰岛素抵抗,且高盐饮食损害胰岛素敏感性主要发生在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在盐抵抗性高血压患者中没有明显的变化[6],说明高血压、盐敏感性和胰岛素抵抗之间在发病机制上有着密切联系[5,29]。
高血压的易感性与人类进化也存在一定的关联[30-31],这种关联性可以在非洲找到它的起源。在非洲炎热和潮湿的环境下,蒸发散热是生物体适应环境的一个基本生理反应过程[32]。然而,炎热的气候和过度的体力活动引起的大量出汗可导致水分和盐的大量丢失,最终引起低血容量而危及生命。古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在古环境中能获取的盐是很少的,而盐的摄入不足和出汗引起的大量盐丢失可增加其对盐摄入的渴望和肾脏的储钠效应,这对于种族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自然选择使得一些存储钠的基因被保存下来[31],而这些基因在盐过量的现代环境中可能促进高血压的发生。
研究表明高血压的易感性与一些古老的遗传基因有关[33],这些基因可增加易患高血压的风险。黑猩猩和人均拥有血管紧张素原(AGT)和上皮细胞钠离子通道γ亚基(ENaC-γ)两个高血压易感基因,而这两个基因均参与盐和血压的调节。AGT有两个受体,一个在启动子A-6G区,另一个在T235M区,这两个受体均与高血压有关[25]。人类基因库研究也显示,一些慢性疾病的遗传基因可能因适应古环境从而被选择下来,这些遗传基因在古代缺盐、低能量和过度体力活动的环境下可增加人类的生存能力;而在盐和能量过剩的现代环境中,这些遗传基因可能促进肥胖、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发生[33]。
钠离子是决定体液分布的一个主要因素,钠潴留常引起水潴留。上皮细胞钠离子通道(ENaC)和钠离子交换分子3(NHE3)是调节钠离子在肾小管重吸收的主要信号分子。研究表明胰岛素可通过刺激ENaC和NHE3增加肾小管对钠离子的重吸收[34],减少钠离子的排出,在盐摄入过多的环境下可能促进高血压的产生。
5 节俭基因假说
所有生物都需要适应它所生存的大环境或小生态环境,在远古环境条件下,人类为增强抵御炎症反应的能力而保留了一些与能量代谢和盐储存的相关基因(如调节胰岛素信号通路的基因)[33],因为能量储存和保存体液对生物体抵抗饥荒、感染和某些应激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被保留下来的调节钠离子和能量储存的基因被称为节俭基因(Thrifty genes)。节俭基因这一概念首先是由 Neel[35]提出的,Neel[35]把节俭基因定义为能够有效地摄取和利用食物的基因。在节俭基因假说中,他认为一些节俭基因之所以被选择到人类的基因库是因为这些基因比非节俭基因有更多的优越性。古代的食物供给是不稳定的,狩猎者常需经历饱食和饥饿的交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基因被进化为能够更有效地调节能量摄入和储存的基因。因此,在饥饿来临时,拥有节俭基因的生物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因为他们可以依赖大量储存的能源来渡过饥饿难关[24]。根据Neel的假说,糖尿病易感性的遗传基础可能与适应旧石器时代时的饱食和饥饿交替循环有关,因为人类通过在饱食时增加脂肪储存引起肥胖,在饥饿来临时就有更高的生存概率。如果说这些基因在古时代具有其优越性,那么在现代生活环境下,这些节俭基因则可能引起肥胖和2型糖尿病。
节俭基因的假说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些肥胖相关的现象。研究发现,肥胖与身高一样具有多基因遗传特征[36],基因群体遗传变异性主要表现在一些特殊基因表现频率上的差异,而不是总体基因的差异[24,37]。比如机体各部位构建(体格和体型)的种族差异代表着身体各部位不同的承载负荷比例,而这些差异可能影响不同种族人群之间对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易感性的变异。机体的构建包括器官肌肉比例、四肢和脂肪比例、四肢和躯体比例以及脂肪组织的扩展能力等,四肢瘦小和腹部脂肪增加代表着节俭基因的效应,这些均与个体易患代谢综合征有关[37]。
6 小结
大量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与高血压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之间的相互共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和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6]。这可能与慢性低度系统性炎症和增加氧化应激反应有关。在长期的人类进化过程中,调节炎性细胞反应(炎性细胞因子等)、能量代谢(胰岛素信号通路分子)、盐的潴留(钠离子通道)等节俭基因可能被选择和保存下来,这些曾帮助我们祖先在饥饿、感染、外伤和体力应激等状态下生存下来的节俭基因,在现代生活环境下可能被不适当的激活,从而增加了胰岛素抵抗、高血压、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一些现代疾病的发生和流行[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