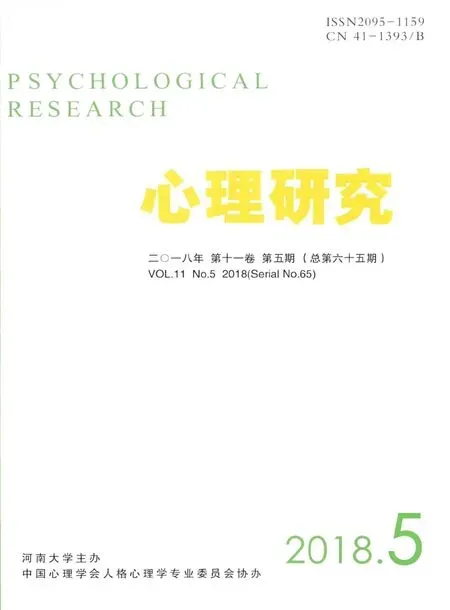父母教育卷入对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感知母亲教育卷入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刘春雷 霍珍珍 梁 鑫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曲阜 273165)
1 引言
学习投入(learning engagement)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和充实的精神状态(Schaufeli,Martinez,& Marques-Pinto,2002; 倪 士光,伍新春,2011)。研究表明,在学生学习成就的影响机制中,学习投入是一个重要因素 (赵明仁,2010)。学习投入与学业表现呈正相关,学习投入越高的学生,其学业成就也越高(张娜,2012)。良好的学习投入不仅体现良好的教育质量,对学校教育改革也有重大影响(蔡敏,刘璐,2014)。因此,要想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培养良好的学习行为,学校应当从“学习投入”抓起,高度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关于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探讨,国内外研究多关注学校因素(如教师支持、同伴关系、课堂学习氛围和环境等)的影响,而对家庭因素的探讨匮乏。家庭中父母教育卷入在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父母教育卷入(parental involvement)指父母对其子女在教育、发展以及家庭和学校中为促使孩子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及心理发展所做出的多种行为(Seginer,2006;罗良,2011)。父母教育卷入可以促进 学 生 在 学 校 的 表 现 (Fan,2001;Christopher,2006)。随着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子女送去参加校外教育培训作为父母教育卷入的主要方式(马克·贝磊,刘钧燕,2015),父母的教育卷入显得相当功利和盲目(陈传锋,王玲凤,陈汉英,俞国良,2014)。
而在父母教育卷入研究中,孩子对父母教育卷入的看法和态度也同样重要,这决定了父母能否有效地影响儿童(Vyverman & Vetten-burg,2009)。研究发现,儿童所感知到的父母教育卷入有时与父母本人做出的教育卷入行为并不一致。例如,Paulson和Sputa(1996)发现,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所报告的在作业和学校方面的卷入水平均高于孩子所感知到的父母卷入水平。而感知父母支持与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正相关(Solberg,Gusavac,Hamann,Felch,Johnson,Lamborn,& Torres,1998),即学生感知父母教育卷入越高,越容易产生对成绩目标定向的支持 (Fridel, Cortina,Turner,& Midgley,2007)。因此,我们在进行父母教育卷入对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时,同时从父母教育卷入与学生感知父母教育卷入两方面入手。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卷入对小学生的学业投入具有影响,但父母教育卷入是怎样作用于学生的学习投入?其中的影响机制如何?这些问题仍需解决。依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并不是简单地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或被环境所左右,个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认知为媒介(Bandura,1996)。自我效能是个体行为的动因。个体对于自我能力表现的预期是个体进行目标设定、行动选择和努力意愿的主要因素。在广泛的研究领域,已有研究证实了自我效能感在人类学习、行为以及动机中的作用(Bandura,1997)。已有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可以引发个体采取积极的行为,如学习投入(Ouweneel,Pascale,Blanca,& Schaufeli,2011)。 班杜拉(1977)在自我效能感理论阐述中表示,随着青少年心理、生理和社会化的发展,自我效能感也会发生变化,即家庭、学校等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 (例如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父母教育卷入越高,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能力水平也会越高(Luo,Aye,Hogan,Kaur,& Chan,2013),学习投入也就越高。而在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上,陆楠和王欲晓(2011)在具体学科中进行了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成绩的研究,发现数学自我效能感高的小学生,其学业成绩也较好。因此,我们认为,父母教育卷入可能并不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而可能是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学习投入,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父母教育卷入与学习投入之间可能存在关系,感知父母卷入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1)父母教育卷入、小学生感知父母卷入与小学生学习投入呈正相关;(2)在父母教育卷入和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关系中,小学生感知父母卷入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取样法,选取山东两所普通小学。在每所学校选取三、四、五、六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共419名学生。其中,男生205人,占48.9%;女生214人,占51.1%。三年级共计107人,男女生分别为43人和64人;四年级共计103人,男女生分别为51人和52人;五年级共计109人,男女生分别为51人和58人;六年级共计101人,男女生分别为54人和47人。分别发放感知父母教育卷入问卷、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和小学生学习投入问卷,最终回收问卷409份,回收率为97.6%。同时,对以上学生家长发放父母教育卷入问卷(家长报告版)419份,最终回收290份,其中父亲填写90人,母亲填写200人,分别占31.0%与 69.0%,问卷回收率为 64.9%。
2.2 测量工具
2.2.1 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
采用吴艺方等(2013)编制的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父母回答版)。该问卷共29个项目,包括家庭监控、学业辅导、亲子沟通、共同活动、家校沟通五个维度。问卷采用五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所有题目的平均分即为父母教育卷入行为得分,分数越高表示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94;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0.87、0.65、0.87 和 0.91;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 指 数 为 :χ2/df=3.86,RMSEA =0.05,CFI=0.94,SRMR=0.05,TLI=0.93。
2.2.2 感知父母教育卷入问卷
采用宋冰(2010)编制的父母教育卷入问卷(学生报告版)测量儿童感知到的父母教育卷入,包括感知母亲卷入和感知父亲卷入两个分量表,共42个题目,包括智力卷入、行为管理卷入和情感卷入三个维度。每个分量表题目的平均分即为感知母亲卷入和感知父亲卷入的得分,分数越高表示儿童感知到的父母教育卷入水平越高。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85,母亲教育卷入三个维度 α系数分别为0.69、0.78 和 0.74;父亲教育卷入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79、0.87 和 0.85。
2.2.3 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采用梁宇颂 (2000)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此问卷共22个题目,分为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每个维度11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所有题目的平均分即为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分数越高表明此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及其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9、0.85 和 0.78; 其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为 :χ2/df=1.86,RMSEA=0.04,CFI=0.92,SRMR=0.05,TLI=0.91。
2.2.4 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Skinner等(2008)编制的学习投入量表,采用回译法将之翻译成中文,共计10个题目,分为行为投入和情感投入两个维度。所有题目的平均分即为学生的学习投入,分数越高表明此学生的学业投入越高。该量表整体采用五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国内一些研究证实该量表能用于测量小学生的学习投入(魏军,刘儒德,何伊丽,唐铭,邸妙词,庄鸿,2014)。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行为投入维度和情感投入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68和 0.72。
2.3 分析方法
应用SPSS20.0软件对各量表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及Hayes(2013)编制的SPSS插件PROCESS宏程序(http://www.afhayes.com/)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该宏程序能便捷有效地进行多重中介模型、调节模型以及它们之间的混合模型分析,在近期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3 研究结果
3.1 相关分析与描述统计
表1列出了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与描述统计结果。相关分析表明: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习投入相关不显著(p>0.05);感知母亲卷入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学习投入相关都显著(p<0.01);感知父亲卷入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相关都显著 (p<0.05);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小学生学习投入相关显著(p<0.01)。 相关样本 t检验表明,父亲教育卷入和母亲教 育 卷入得 分存在 显 著差异 (t=-3.29,p<0.01),感知父亲教育卷入和感知母亲教育卷入得分存在显著差异(t=17.2,p<0.001)。 独立样本 t检验表明,男生和女生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各维度上都有显著差异(p<0.01),女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显著大于男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

表1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3.2 中介效应检验
因为母亲卷入显著大于父亲卷入,感知母亲卷入显著大于感知父亲卷入,因此,在本研究中,将父母教育卷入分为母亲卷入和父亲卷入,将感知父母卷入分为感知母亲卷入和感知父亲卷入进行两组分析。每组分析分别检验三条中介路径,第1组路径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母亲教育卷入→感知母亲卷入→学习投入(路径1);母亲教育卷入→感知母亲卷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路径2);母亲教育卷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 (路径3)。关键要检验的是中介路径2是否显著。

图1 母亲教育卷入、感知母亲卷入、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关系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在第1组分析中,将自变量(母亲教育卷入)、中介变量(感知母亲卷入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因变量(小学生学习投入)以及协变量(性别和年级)依次选入相应的选项框。选择模型6(此模型为链式多重中介模型),设定样本量为5000,Bootstrap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即勾选 “Bias Corrected”,对置信区间的置信度,选择95%。表2列出了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结果。
数据结果表明:母亲教育卷入正向影响感知母亲卷入(β=0.26,t=3.53,p<0.001),感知母亲卷入正向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 (β=0.21,t=2.31,p<0.001),学业自我效能感则对学习投入存在正向影响 (β=0.84,t=14.44,p<0.001)。 此时,母亲教育卷入对学习投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5,t=-1.01,p=0.32)。母亲教育卷入→感知母亲卷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的路径效应值为0.047,其所在置信区间不包括 0(95%CI=0.014,0.096),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母亲教育卷入→感知母亲教育卷入→学习投入的路径效应值为 0.017,其所在置信区间包括0(95%CI=-0.002,0.061),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不显著;母亲教育卷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的中介路径的效应值为 0.055,其所在置信区间包括 0(95%CI=-0.05,0.15),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感知母亲卷入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母亲教育卷入与学习投入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得到证实。

图2 父亲教育卷入、感知父亲卷入、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关系的中介模型

表2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第2组路径分析模型如图2所示,将母亲教育卷入换成父亲教育卷入,将感知母亲卷入换成感知父亲卷入再进行分析。数据结果表明,感知父亲教育卷入正向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 (β=0.11,t=3.26,p=0.001)。学业自我效能感则对学习投入存在正向影响(β=0.86,t=13.62,p<0.001)。 此时, 父亲教育卷入对学习投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β=-0.025,t=-0.48,p=0.63)。父亲教育卷入→感知父亲卷入→学习投入的中介路径效应值为0.002,其所在置信区间包括 0(95%CI =-0.004,0.020), 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不显著;父亲教育卷入→感知父亲卷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的中介路径效应值为0.005,其所在置信区间包括 0(95%CI =0.011,0.030),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不显著;父亲教育卷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的中介路径效应值为0.099,其所在置信区间不包括 0(95%CI =0.001,0.198),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因此,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父亲教育卷入与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得到证实。
4 讨论
4.1 父母教育卷入、感知父母教育卷入对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
过去的研究在父母教育卷入究竟对儿童青少年发展是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上仍然存在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以往对父母教育卷入的测量没有区分父母自身教育卷入和孩子感知父母教育卷入。本研究将父母教育卷入与学生感知父母教育卷入进行了区分,得出了相对清晰的结果。在父母教育卷入、感知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习投入这三个变量间的相关分析中,结果表明: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习投入相关不显著,感知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相关都显著。
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习投入相关不显著,而感知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习投入相关显著说明父母教育卷入多并不必然会导致小学生更多的学习投入,而只有让儿童充分感知到,并让儿童喜欢和接受的教育卷入才能让孩子更多地投入学习。研究发现,儿童所感知到的父母卷入有时与父母本人做出的教育卷入行为并不一致(罗良,2014)。本研究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所报告的教育卷入水平均高于孩子所感知到的父母卷入水平。这种不一致意味着,父母所做出的一些卷入行为,孩子并没有充分感知到。这是导致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习投入相关不显著,感知父母教育卷入与学习投入相关显著的原因。这也与先前的研究一致。乔娜、张景焕、刘桂荣和林崇德(2013)的研究发现,初中生感知父母参与与其学习成绩显著正相关。刘桂荣和滕秀芹(2016)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对父母教育卷入的感知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
最近以中国儿童为被试的实证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卷入与学业成绩呈负向关系 (郭筱琳,2017)。Pomerantz,Moorman 和 Litwaek(2007)与 Silinskas,Niemi,Lerkkanen 和 Nurmi(2013)曾提出,父母教育卷入也许并非越多越好,不恰当的教育卷入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不恰当的父母教育卷入方式,或许正是造成父母教育卷入水平与小学生学习投入水平相关不显著甚至负相关的原因之一。Froiland和Peterson(2012)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父母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对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马虹、姚梅林、吉雪岩(2015)的研究发现,家长的倾力投入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导致子女的学业投入,其成效会受到教养风格的制约。若教养风格不当,不仅家长投入的收效甚微,甚至可能诱发其他不良后果。可见,家长若能与子女良好地互动,采用支持型的教养风格,则家长投入有望取得良好成效。因此,父母教育卷入并不是越多越好,功利主义的父母教育卷入并不一定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而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无论是在父母教育卷入还是感知父母教育卷入方面,父母的关注点更多是在家庭监控和学业辅导方面,父母的行为管理卷入大于情感卷入。因此,不正确的父母教育卷入方式,并没有我们预期的促进学生学习投入,有时反而起到相反作用。
4.2 感知父母教育卷入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父母教育卷入和学习投入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感知母亲卷入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母亲教育卷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感知父母教育卷入水平越高,其学业自我效能水平就越强,学业自我效能的提升又进一步带来更高水平的学习投入,这已被国内外有关学习投入的研究所证实(Ouweneel,Pascale,Blanca,& Schaufeli,2011;石雷山,陈英敏,侯秀,高峰强,2013)。学业自我效能是学生对自我学习能力的评价。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动机因素,如果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能力充满自信,他将更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表现为在学习上愿意付出努力,遇到困难更能坚持不懈,以及对学习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卷入和全身心的参与。因此,学业自我效能通过学业目标的设定、学习的付出与努力,以及在遭遇挫败时的坚持程度,影响学生对学习的投入水平。
本研究的一大创新之处是对父母教育卷入进行了父亲和母亲的区分,结果表明:母亲教育卷入通过影响小学生感知母亲教育卷入,感知母亲卷入又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小学生的学习投入;而父亲教育卷入对感知父亲卷入没有显著影响,只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感知父亲教育卷入也是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起作用。前面的差异检验也证明,父母教育卷入中更多的是母亲的教育卷入,父亲的教育卷入少,以至于小学生没有或很少感知到父亲教育卷入。说明小学生感知母亲对其教育卷入,明显优于父亲,这与Lewis和Lamb(2003)的研究中提到的母亲的卷入方式与父亲的卷入方式是一致的。中国自古讲求“男主外,女主内”,母亲在孩子的教育上一直承担着重要责任。在一个家庭结构中,父亲更多地承担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有时可能会因为工作需要而短期外出或者长期外出,这就会导致不能兼顾到孩子的教育卷入,因此父亲教育卷入对小学生感知父亲卷入没有显著影响。
近些年来研究发现,父亲的卷入行为对儿童的认知、情感和社会化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特别是男孩在成长发展中父亲的陪伴对孩子的学业和人格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父亲教育卷入的缺失可能是男孩在小学阶段发育较晚导致男孩学业成绩总体比女孩差的另一原因。母亲对男孩陪伴可能并不能弥补父亲在男孩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父亲高度参与教育的家庭中,儿童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更有同情心,较少存在性别刻板观念,更为内控 (赵娜,2007;Pleck,1997)。 Lamb(2010)曾总结到,父亲的敏感性教养(如回应、交谈、教导以及鼓励学习等)能预测儿童社会情绪方面的发展,而父亲缺失则会对儿童青少年产生显著的不良影响,如与父亲分开居住的孩子会出现更高的辍学率、更多的抑郁或焦虑问题以及更多的行为问题。因此,加大父亲的教育卷入程度,通过亲子沟通、共同活动等提高小学生感知父亲卷入和学业自我效能感,或许对其学习投入会有帮助。
5 结论
(1)父母教育卷入对小学生学习投入没有显著影响,小学生感知父母教育卷入程度对小学生学习投入有显著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预测学习投入。
(2)小学生感知母亲卷入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母亲教育卷入与学生学习投入关系之间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3)学业自我效能感分别在父亲教育卷入和感知父亲卷入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