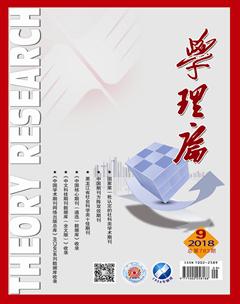文化自信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
谢园园
摘 要:回顾中国文化发展史,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文化“四自”现象(即文化自负、文化自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了探索,其中以张申府、张岱年、方克立、刘仲林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在继承前人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化哲学的独到见解,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借鉴国外先进文化,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自信;综合创新派;文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9-0097-03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慶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学者对文化的认识也在摸索中前进,其中,以综合创新派独辟蹊径的探索为例。
一、文化“四自”
(一)文化自负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给炎黄子孙带来丰富灿烂的文明成果。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下,中国统治者日渐生成不可一世的优越心理,表现之一在于固守华夏中心主义,抱着“天朝上国”的文化自负心态。例如,1793年,乾隆83岁大寿,英国为了建立与中国的通商关系,派马戛尔尼访华。对于英国提出的通商要求,乾隆给英王的敕谕说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二)文化自卑
以“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文化自负观念,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近代国门被迫打开而逐渐被改变。封建主义清王朝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角逐中,开启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百年屈辱近代史,中国人民逐渐由养尊处优的文化自负心态转变为惶惶不可终日的文化自卑心态。
西方国家的侵略来势汹汹,他们并未忘记以往在中国遭遇中“夷”字特有的戏谑与侮辱。于是,他们变本加厉。在中英《南京条约》的谈判中,汉字“夷”首次被英方列入条约谈判议程。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中英天津条约》第50款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在西方国家的不懈“努力”下,到20世纪之交,“夷”字已经在中文出版物中了无踪迹,取而代之“洋”字统指新兴的外国事物。
(三)文化自觉
面对新旧文化的破与立,如何正本清源,是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这期间出现许多观点,如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论”、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鲁迅的“拿来主义”,等等。但是,“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重要。”[1]文化独立,顾名思义即在文化选择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要想做到文化独立,首先要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文化之所由来,对于其发展历程、内在特质、现实状况、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对于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2]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3]“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3]费孝通将文化自觉历程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中,“‘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美人之美就是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地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和发展。”[3]
这里列举中日对待《海国图志》的不同态度,简单说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近代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朝野的震动。“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面对当时中国封闭、僵化、落后的封建思想观念和文化严重禁锢人们思想、极大阻碍社会发展的状况下,心急如焚,忧国忧民,便委托魏源编写了一本全面介绍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书籍——《海国图志》。魏源在书中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纲领。然而遗憾的是,《海国图志》一书并没有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反观日本人却如获至宝,连续翻印多达15次,大大促进了日本人思想的空前解放。
(四)文化自信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予以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传递其文化理念。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4]文化自信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5]。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6]“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
二、综合创新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独辟蹊径地探索综合创新派,主要是指以张申府、张岱年、方克立、刘仲林为代表形成的文化哲学。
(一)张申府:“列宁、孔子、罗素,三流合一”
张申府早年阅读罗素《数学原理》等相关著作,接受了罗素的逻辑解析学说,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此外,他还被认为是把逻辑主义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的中国第一人[8]。在文化哲学上,张申府主张“辩证综合”,即“列宁、孔子、罗素,三流合一”。
逻辑一词是张申府从章士钊1912年发表在《民立报》上的文章中得知,当时罗素的逻辑解析学说风行一时。张申府在《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一书中曾提及他与罗素之间的“缘分”。张申府刚进北京大学读书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申府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籍,1914年美国出版,英國罗素著的《我们的外界知识》。翻看一遍后,他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简直爱不释手。由此,张申府发现并对罗素产生兴趣。
(二)张岱年:从“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到“综合创新”论
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提出“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观点,即主张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解析哲学综合的文化哲学观。他的有关思想集中表述于1933年发表的《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和1935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三篇文章中。
张岱年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又明确提出“综合创新”论的文化哲学观。他在《文化与哲学》一书的自序中说道:“30年代曾经参加当时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我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这种主张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9]80年代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在内容上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不仅讲中西文化之综合,而且也讲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三是明确指出‘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综合。”[10]
(三)方克立:“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
方克立在张岱年等的影响下,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哲学观。说起文化体用问题,难免会使人想起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为摆脱疑虑,方克立曾专门发表文章予以阐述。他指出,晚清的“中体西用”论是以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船坚炮利为用,企图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封建的旧文化、旧制度的保守主义理论。而“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哲学观,“力图突破体用二元思维模式的局限性,把主导性之‘体(魂)与主体性之‘体、‘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区分开来”[10]。方克立用“体、用、魂”三元模式更加准确地说明了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民族文化主体性和对外开放方针有机统一起来。
(四)刘仲林:“从‘仁学到‘创学”
刘仲林在继承张岱年“综合创新”论和“广义创造观”的基础上,提出“从‘仁学到‘创学”的文化哲学观。他把中国文化与科学视为创造过程的产物,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重点,通过从“仁学”到“创学”的转型,探索中国文化与现代科学会通的新途径[11]。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创造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创新精神,只是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由于统治阶级和历史的需要,逐渐忽视了人的创造性,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更多地被束缚、禁锢和压制[12]。
刘仲林从中国传统文化着眼,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交,君子以辅相天地之宜”是中国文化的总追求和基本精神。他认为“天行健”“地势坤”“天地交”三位一体,以及由此形成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辅相天地之宜”,代表了积极进取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哲学与文化创新思想的重要源泉[13]。在此基础上,刘仲林提出自己对现代创造的理解,他认为创造是赋予新而和的存在;是对已知要素进行组合和选择的过程;是只可在实践中体会的一,是不可言说的道[14]。
三、结语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既有古今之分,又有中外之别。“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无论是文化复古主义还是全盘西化论,都只看到文化的一个方面。我们应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16]。正如习近平所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7]一言以蔽之,处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我们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实现文化上的“和而不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1][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哲学家对80年前的中国印象[M].秦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192.
[2]李宗桂.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J].社会科学战线,2017(8).
[3]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88.
[4]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J].红旗文稿,2010(16):4.
[5]习近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N].人民日报,2016-07-02(2).
[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2).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8]郭一曲.从“辩证综合”到“综合创新”——张申府对张岱年的影响[J].现代哲学,2001(2).
[9]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
[10]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71,3.
[11]刘仲林.儒学与科学会通三家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8).
[12]刘仲林.中国文化与中国创造学[J].天津师大学报,1998(5).
[13]刘仲林.“创新”的中国文化渊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4-5.
[14]刘仲林.论创造与创造观[J].东方论坛,2002(1).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6]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1).
[1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