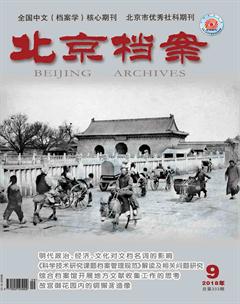档案职业概念界定的困境及其消解
杨光 奚朝辉
摘要:我国档案职业至今缺乏统一的界定。文章剖析了档案职业界定陷入困境的原因,即源于档案职业的日常概念与其科学概念之间的矛盾、档案职业概念的稳定性与社会现实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档案职业的“行政性”与“管理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档案职业的国别差异性与其国际性之间的矛盾,并针对上述矛盾提出了相应的消解之策。
关键词:档案职业核心概念概念界定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rchival occupation in our country still lacks unified definition till no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light of archival occupation definition, namely the contradiction be? tween the daily concept and the scientific concept ,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tability of the con? cept of archival occupation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reali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functionand“archivesmanage? ment”function of archival occupation, and the con? 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untry differences and in? ternationality of archival occup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Keywords: archival occupation; core concep? tion; concept definition
核心概念的界定是开展一切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它既决定了研究开始的起点,也划定了研究所涉的边界。但在档案职业研究领域,“档案职业”这一核心概念缺乏统一的界定,且鲜有文献专门探讨该问题。[1]鉴于此,笔者曾在《社会分工视野下档案职业主体概念的界定》一文中,沿循“溯源追本”的研究思路,基于职业的“逻辑起点”——社会分工视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进行了解读,并认为在我国档案职业主体有且仅指中央和县级以上综合档案馆中的档案管理人员。[2]而作为后续研究,本文旨在剖析造成档案职业界定混乱的原因,并试图改观人们对档案职业的认识。
一、陷入困境:档案职业界定中的分歧
档案职业至今缺乏清晰统一的界定。一方面,档案学界的代表性观点并未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学界的这些代表性观点与档案职业的官方界定存在出入。
(一)档案职业的官方界定与学界界定
我国在1999年和2015年分别颁布了两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大典》)。[3]新旧两版《大典》对于档案职业的界定基本一致,即档案职业主体是指:从事档案接收、征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保护、利用、编研的专业人员。[3-4]特指综合档案馆中的档案管理人员。而在相关文献中,诸多研究者却未参考该官方界定,或将档案职业主体外延扩展至各组织内部的档案管理人员,[5-6]或扩展至档案中介机构中的档案服务人员,[7]或扩展至档案行政人员,[8-9]或扩展至档案教学人员,[10]等等。
(二)档案职业界定中的分歧
纷呈的观点折射出人们对于档案职业的认识存在三方面分歧:
第一是业务范围上的分歧,体现为“社会与组织之争”,即档案职业是面向社会还是面向组织提供服务。
第二是工作职能上的分歧,体现为“行政与管理之争”,即档案职业是从事行政活动还是档案管理活动。
第三是工作目的上的分歧,体现为“公益性和营利性之争”,即档案职业活动是以服务社会为目的还是以获取利益为目的。档案人员的工作目的由其所属单位的性质决定。若在非营利性组织,如在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档案人员,其旨在为公众谋取利益。若在营利性组织,如在商业性档案机构、各企业中工作的档案人员,其职业活动则属于经营性活动,本质上以获得“私利”为目的。
二、解读困境:档案职业界定的矛盾
无论与官方界定相较而言,还是从学界内部来看,我国档案职业的界定都有失准确性和同一性。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档案职业界定的混乱:
(一)档案职业的日常概念与其科学概念之间的矛盾
“‘职业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概念的特性之一就是其内涵的模糊性。”[11]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对“职业”的模糊性特征进行了精辟的解释:“一方面,职业被社会科学家们当做一个审慎界定的科学概念来使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职业描绘了一种在道德上可欲的工作。”[12]可见,“职业”内涵的模糊源于其日常概念和科学概念之间的矛盾,两者既相关又相异:前者通常是对感性認识的直接抽象和概括,往往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抽象和概括,它摆脱了前者模糊的性质,具有精确性和严格的形式。
人们对于“档案职业”的理解也无法摆脱思维的固有局限与自然惯性。于大部分人而言,其对档案职业的认识首先建立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与“档案”相关的活动都是档案职业的范畴。然而,每个人受制于知识经验的局限往往会对档案职业的本质有着不同程度的把握。诸多研究者跳过了概念界定这一必要的研究环节,而仅凭借粗线条的日常认识直接开展研究,无疑会混淆档案职业的日常概念和科学概念。
(二)档案职业概念的稳定性和社会现实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
社会现象不断发展,与之对应的概念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更新常常滞后于社会变动。由于先前的档案职业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使得许多人对于现代档案职业的认识仍无法摆脱先前认知。
我国古代的档案管理活动一直是文书、档案,乃至图书工作的混合体,由此派生的“档案”管理者也非独立主体,而是兼有文书、档案、图书等执掌的史官或书吏[13]。至民国时,档案及其管理活动开始明晰化,但仍囿于政府机构的框架内,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直至1999版的《大典》将档案职业收录其中,这才标志着我国档案管理活动正式成为一种社会职业而独立存在。然而,由于此前档案管理活动一直和行政、文书活动密切相关,由此形成的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文书情结的“档案职业”概念已根植于社会认知中,它们成为人们重新界定档案职业的范本和参照。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了人们对于档案职业现状的判断,使一些人仍将档案职业主体和文书人员及档案行政人员混为一谈。
(三)档案职业的“行政性”和“管理性”之间的矛盾
我国档案局和同级档案馆“合署办公”的模式决定了综合档案机构的人员主要包括档案行政人员和档案管理人员,按照2015版《大典》的分类,前者属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3]或者“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如各档案局的领导班子,他们属于“事业单位负责人”),[13]后者属于“专业技术人员”。[13]但两者界限的模糊使得档案职业的角色定位在“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摇摆不定。
1.人员编制混乱:按照我国的编制制度,履行档案事业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应属于行政编制,履行档案保管和利用职能的人员应归入事业编制,而后者才是官方界定的档案职业主体。换言之,事业编制理应是判断档案职业的标准之一。但“有的局、馆全部是行政编制;有的局、馆全部是事业编制;也有的局、馆既有行政编制,也有事业编制,并开始出现事业编制‘参照公务员标准的趋势。”[14]人员编制规划和设置的混乱影响了人们对档案职业的判断。
2.职能相互交叉:“局馆合一”的管理体制要求档案机构既要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又要满足社会文化需求。从工作性质来看,档案行政人员应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档案管理人员应履行档案管理职能。但由于人员编制的混乱,导致两者的职能划分并不清晰,即档案行政人员会从事档案接收利用工作,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也会指导档案业务。
3.职业流动灵活:我国档案局(馆)为适应“局馆合一”的管理模式,设置了专业技术职务阶梯和综合管理职务阶梯的双通道模式,[8]为档案人员提供了一条从专业技术角色转换为行政管理角色的职业流动通道。加上我国的人才管理制度与职称、工资挂钩,行政人员的地位和待遇常优于技术人员,这变相地“鼓励”了人们频繁地流向档案行政岗,模糊了档案行政和档案管理工作间的界限。
(四)档案职业的国别差异性与其国际性之间的矛盾
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概念是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15]我国当前的职业分类体系也是参照“《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基本原则和描述结构,借鉴发达国家的职业分类经验而建立的”。[3]可以说,我国的“档案职业”是西方传入的“舶来品”。但源出西方的“档案职业”已在中国语境中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内涵。然而,学界在引介西方成果时,却常常忽略两者的差异,以致我国“档案职业”概念的混乱。
1.档案职业编制不同: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务员被称为government employee,即政府雇员,是指是在美国联邦政府中工作的所有人员。[16]因此,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及其管辖下的国家档案馆工作的档案职业主体都属于公务员编制,都在政府领取工资。而我国的档案职业主体可能属事业编制,也有可能属行政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17]也就是说,在我国综合档案馆工作的档案职业主体不一定属于公务员,但档案行政人员却一定是公务员。如果有人误读了中西档案职业编制规划,很可能以“是否是公务员”的标准来界定我国档案职业,误将档案行政人员纳入我国档案职业的范畴。
2.档案职业管理对象不同:美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SOC)系统将美国的档案职业主体界定为从事“鉴定、编目、直接保管永久records[18]以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并基于档案资料参与研究活动”[19]的人员。可见,美国档案职业的管理对象包括档案、records和历史文件。而新旧两版《大典》明确规定我国档案职业客体仅指“档案”。学界在引介西方成果时,若忽略了这一国别差异性,可能使人们误以为我国档案职业主体除了管理档案,也管理records和文件,从而将其外延扩展至组织内部的档案人员,甚至是文秘、信息资源管理人员。
三、走出困境:档案职业界定分歧的消解
档案职业是整个档案学的“出口”,对档案职业主体是否具有准确、清醒的认识,影响着学科与职业之间关系的建构。研究者在界定档案职业主体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区分档案职业的日常概念和科学概念
在不同情境中我们应区分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赋予“档案职业”多义的理解。但“至少在一个学科领域内,一个术语只表达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只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达,不能有歧义”[20]。“职業”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社会学的奠基人涂尔干明确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21]。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而形成,不能用常识来解释,科学的观念只能来自科学的实践。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22]对档案职业的界定必须与客观的社会实践相联系,而非按照个人主观常识的指引进行自定义。即使不认同官方界定,也应讲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仅凭日常概念代替科学概念。
(二)根据社会现实重新界定档案职业
档案职业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档案界需要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及时且客观地对其进行界定。档案管理活动虽最初与文书、图书、行政活动“不分你我”,但2015版《大典》已明确规定,上述活动分属于不同的职业类别。但一些研究者仍未将档案管理活动当作一种独立的职业来看待,总要或多或少地牵扯到其他工作。面对档案职业遭受的误解,研究者应自觉地为档案职业正名,而非拘泥于陈旧的档案职业观而忽视其发展的客观现实。
(三)明确档案职业主体的角色定位
我国档案管理和档案行政工作界限的模糊让人们误以为档案职业具有行政职能,要改观这种认识须对其角色定位进行“去行政化”处理。首先,坚决贯彻履行我国的编制制度。各局(馆)内行使档案管理职能的人员,即档案职业主体只能纳入事业编制。其次,明确档案管理人员和档案行政人员的职能分工。在实际工作中,档案局(馆)应该按照《大典》等官方文件安排各自的工作,如档案管理人员只负责管理档案和提供利用而不涉及其他工作,档案行政人员亦然。最后,改善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维护档案职业群体的稳定性。
(四)处理好档案职业学术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Archival profession”与“档案职业”虽常被画上等号,但在看似一致的词语背后实际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国别差异。这些差异既是各国档案职业的立足所在,也是世界档案职业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西方档案学主导著全球档案学研究,学习西方理论已成为中国学界走向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但西方档案学在全球范围内的散播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同化世界文化的一种隐蔽形式。若研究者毫无批判性地盲目推崇西学,不仅会造成如“档案职业”等术语交流的误解,且中国档案职业与生俱来的特质极有可能被淹没。因此,在译介国外成果时,必须考察其产生的现实背景,重视中西“档案职业”的差异。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笔者以检索式:1.TI=(档案*职业) AND (TI=概念 OR TI=界定);2.TI=(档案*职业) AND KY=概念界定在CNKI全库进行搜索,共计输出文献两篇(检索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除笔者的《社会分工视野下档案职业主体概念的界定》外,即是《重新界定当代档案职业社会功能》,但该文主题并非档案职业界定,故剔除。当然,不排除因笔者检索策略存在缺陷而导致漏检相关文献.
[2]杨光.社会分工视野下档案职业主体概念的界定[J].档案管理,2017,(5):16-19.
[3]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5:1.
[4]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999:393.
[5]王新才,谭必勇.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与中国档案教育的发展前途[J].图书情报知识,2005(6):18-22.
[6]王小丽.关于建立我国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探讨[J].档案管理,2006(2):42.
[7]徐拥军,闫静.中国新上岗专职档案人员职业认同和职业满意度调查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7(1):84-92.
[8]范世清.困境与路径——试论档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内涵与意义[J].浙江档案,2008(4):20-22.
[9]杨艳.论档案职业资格评价体系的构建[J].档案学研究,2013(3):64-69.
[10]李财富,童兰玲.档案职业与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研究[J].浙江档案,2009(3):22.
[11]张英丽,沈红.学术职业:概念界定中的困境[J].江苏高教,2007,(5):27.
[12]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06,(1):199.
[13]胡鸿杰.中国档案职业的形成与确立[J].档案学通讯,2006(1):17.
[14]罗军.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49.
[15]孟景舟.职业教育基础概念的历史溯源[D].天津:天津大学,2012:15.
[16]解舒晴.中美两国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9.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EB/OL].(2011-10-13)[2017- 03- 22].http://www.gov.cn/2012gwy/content_ 1968390.htm.
[18]Records在本文中以英文原文形式出现是因为在中文相关领域中暂无与之完全对应的概念,相关结论可参见谢丽、王健的《中美档案法律法规中核心概念对应关系研究》.
[1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DB/OL].(2011- 03- 11) [2017- 03- 22]. https://www.bls.gov/soc/2010/soc254011.htm.
[20]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35.
[21]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5.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2.安徽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