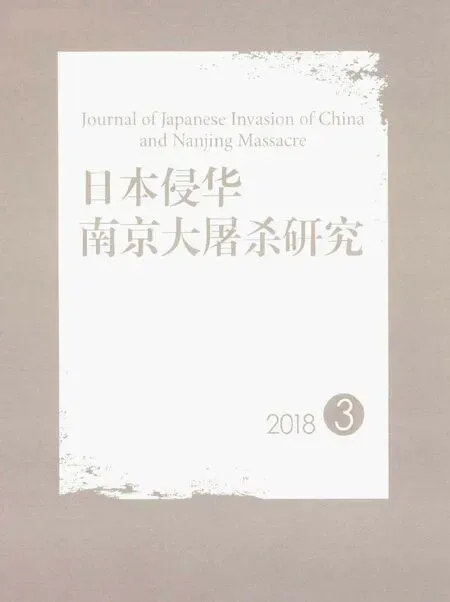民国出版物中的日军“慰安妇”制度
刘广建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期间实施的罪恶制度,是日本的战争罪行之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特别是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开始在侵华日军中全面实施“慰安妇”制度。当时在中国的日军“慰安妇”主要来源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国内。这些女性被以欺骗、诱拐、强征等方式送进日军慰安所,①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初期,有少数日本女性在日军的蛊惑下自愿充当“慰安妇”。被迫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据中国学者估计,仅中国的受害女性就达20万人。对于这种侵犯人权、违反伦理的国家犯罪行为,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就已开始详细报道并加以批判了。许多报刊报道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罪恶,一些亲眼目睹日军暴行者的叙述更可看出这一制度的残忍性。
一、记录“慰安妇”制度的民国出版物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大屠杀过程中,南京发生了近两万起强奸事件。在面临大规模性病威胁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当局在南京确立了“慰安妇”制度。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在1937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军队的非法违纪事件越来越多,参谋部第二课召集各队将校会议,参谋长强调军纪,并审议通过了第二课提出的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提案。”②《上村利道阵中日记》,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此后,“慰安妇”制度迅速在日军占领区推广。
当时中国的出版物关注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多的是报纸。③本文所考察的报纸以1937年至1947年的《申报》和《大公报》为主,也有少量涉及“慰安妇”内容的其他报纸。从日军大规模实施“慰安妇”制度开始,到日本投降后追究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中国报纸对其持续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7年的《申报》报道中,直接出现“慰安妇”和“慰安所”的报道近40篇。以“军妓”“营妓”①由于当时对日军“慰安妇”制度没有深刻认识,所以当时报刊有时称“慰安妇”为“军妓”“营妓”、“妓女”等。等为报道内容的有20多篇。同一时期,《大公报》直接出现“慰安妇”和“慰安所”的报道近50篇;以“军妓”“营妓”等为报道内容的有90多篇,是同时期《申报》的四倍多。其他报纸如《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也有数篇关于日军强掳中国女性充当“慰安妇”的报道。伪政权的报纸如《南京新报》甚至还公开刊登慰安所的广告。
《申报》和《大公报》刊载的有关“慰安妇”制度的内容以新闻报道为主,仅有少数几篇社论。这些报道除极少数与“慰安妇”制度无直接关联外,其余均涉及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慰安妇”制度、建立慰安所、强征中国女性充当性奴隶等内容。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1938年12月25日在《申报》发表文章指出:“我常常听见在华的日军,有找到中国妇女,拘禁中国妇女于所谓‘舒适所’内。可是,虽然这种暴行在上海、南京、芜湖,以及其他一切被日军占据的城镇里,已经发生了无数次。然而日军的暴行,还不止对中国妇女如此,对日本妇女也赐予这种同样的‘恩惠’。他(指日军当局——引者)为了要使日军‘舒适’,于是把日本的妇女一千千的送到中国来设立‘特别妓院’(又名‘安心园’)以供日军取乐。”②史沫特莱:《扬子江上日军的危机》,《申报》(上海版)1938年12月25日,第7版。从这些报道中不仅能看到中国女性受到迫害,也有朝鲜半岛和日本女性沦为性奴隶者,更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日军官兵和“慰安妇”的关系,即日军在慰安所中遇到自己的妻子等及由此引发的悲惨故事。
当时的期刊也有一些文章涉及日军“慰安妇”制度,但数量不多。笔者目前所能找到的民国期刊相关文章约30篇,时间跨度从1937年到1946年,几乎每一篇都记述得非常详细,从不同角度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涉及慰安所开办者的信息、慰安所详细地址、“慰安妇”人数、慰安所内发生的事情等等。通过这些文章,使人们对日军“慰安妇”制度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如《浙江妇女》1939年第4期刊发的任重的《南京慰安所里》一文,详细介绍了作者亲眼所见南京人民慰安所内的情况;再如徐妫在《文化批判》1939年第6卷第1期上发表的《战时下的日本妇女》一文,系统介绍了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本女性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遭遇,其中就包括充当日军“慰安妇”。
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部分图书也涉及到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伪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新闻训练所编写的《南京指南》。这本南京旅游指南有一章节专门介绍南京的娱乐场所,其中有9家以慰安所冠名,详见下表:

《南京指南》所载日军慰安所名称和地址一览表
此外还有《今日之南京》《敌寇暴行录》《陷京五月记》等书籍,部分内容也涉及“慰安妇”制度。这些图书或多或少记述了“慰安妇”制度的实施情况,人们能从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如《南京指南》记载的人民慰安所与前述《浙江妇女》刊发的文章都指向同一个慰安所,从而可以进一步弄清人民慰安所的情况。
还有一类出版物比较特殊,即由日本人在中国出版的日文书刊,其中也有部分涉及到了日军“慰安妇”制度。有两本日本人的出版物较为典型,一是《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记录了在中国各地日本侨民①该书将朝鲜半岛人和台湾人也归类为日本侨民。的信息,其中有很多人涉及慰安所。《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就开始编辑出版,每年一版。从1937年起,该书大量出现慰安所的内容,包括慰安所的名称、地址、电话、经营者姓名和籍贯等,直到1944年最后一版。如东幸升楼慰安所位于南京下关大马路德安里14号,开办者为日本人川尻金藏;②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中支版·南京)、金風社、1939年9月、8頁。清江会馆慰安所经营者为日本人反町龟十郎;③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中支版·無錫)、金風社、1942年8月、9頁。芜湖下二街37号的不知火馆慰安所经营者为日本兵库县人坂田小一郎;④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中支版·蕪湖)、金風社、1942年8月、6頁。广东的慰安所有“高雄亭”“玉之屋”“竹之屋”“文明村”“福冈亭”“吾妻楼”“天桥”“青山”“银猫”“三浦家”等。⑤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中支版·廣東)、金風社、1939年9月、15、19、22、24、25頁。
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类似的另一本日本人的出版物是《在支半岛人名录》,该书只记载了朝鲜半岛人在中国从事各种行业的情况,其中包括慰安所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书中的部分信息能够相互印证,也有部分信息可以和《南京指南》中的慰安所相互印证。
二、民国出版物对“慰安妇”制度的记述
民国出版物中记录了很多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内容,包括日军在各占领地筹建慰安所,强征当地女性充当“慰安妇”,以及“慰安妇”所经历的悲惨故事等。从这些记述中人们不难看出,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不仅给被占领区的中国女性造成了严重伤害,朝鲜半岛、台湾地区甚至日本女性亦不能幸免。
日军为了实施“慰安妇”制度,几乎在每个占领区都设立了慰安所,甚至在前线阵地上也设立临时慰安所。日军慰安所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军队直接经营的专供日军使用的慰安所;二是形式上为日侨民营,但军方也插手,供军人、“军属”玩乐的“军督民办”慰安所;三是由日军指定专供日军使用的民间妓院形式的慰安所;四是军方或民间经营的流动式慰安所;五是日军指使伪政权或胁迫中国娼业老鸨开设的慰安所。⑥苏智良:《日军“慰安妇”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209页。从侵华日军各部队自发设立流动慰安所,到“慰安妇”制度确立后的大规模推广,各种形式的慰安所通过不同途径、利用各种场所建立起来。
以南京为例,一位亲眼目睹日军暴行的市民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汉奸为要买好日本人,一面尽量压迫民众,一面在城中设立十七个慰安所,到外面强迫美丽的女同胞,作日人的牺牲品。这十七个所谓‘慰安所’中,不知有几万女同胞被蹂躏牺牲了。”⑦林娜:《血泪话金陵》,《宇宙风》第71期,1938年7月16日,第257—258页。一名被日军俘获的中国军人目睹了日军建立的慰安所:“被俘的那天下午,整整挑了半天水。第二天早晨我又被迫去担脸水,一名敌兵让我担水到后院里,又让我往屋子里送。我不明白,他就又踢我又打我。等我明白了,只好往屋里送。刚走进去,便一眼看见两个女同胞掩在一条毯子下,躺在那里。两个满脸横肉的日军官佐,一人穿了件女衣在狞笑……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们,就是在大白天也不能穿衣服……又有一天,一批女人被赶了进去……黄昏时分,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总好似听到哀号和嬉笑。”①佚名:《一笔血债,京敌兽行目击记》,《大公报》(汉口)1938年2月7日,第2版。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白芜回忆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时说:“慰安所是非常多的,汉奸利用流民之多,无依的女孩子之多,强迫收容了来卖淫。有一个流氓汉奸乔月琴主办了几个慰安所,自任总主任,另以一唐少霖任副主任,在铁管巷四达里设有‘上军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设有‘上军北部慰安所’。在夫子庙海洞春内设有人民慰安所。这些女同胞逐日受到无数次的凌辱”。②白芜:《今日之南京》,南京晚报社1938年11月版,第(A)9页。1938年初,南京的社会秩序开始渐趋稳定后,日军在南京城内以各种方式陆续开办了多家慰安所。“在京日军是以各战场调回整理的居多,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军部以极大的化妆费和服装费去创办‘慰安所’。每个礼拜一次的机会给士兵去自由选择。”③任重:《南京慰安所里》,《浙江妇女》1939年第4期。据调查显示,战时南京的日军慰安所至少有60家。④苏智良、张建军主编:《南京日军慰安所实录》,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民国时期的报纸也大量报道了不同类型的慰安所。如苏州昆山于1937年11月被日军侵占,昆山“昔为文物之邦,民风古朴,向无妓寮之设,自日军铁蹄蹂躏后,日宣抚班即有慰安所之设立,以供日军之需要”。⑤《昆山之烟赌娼》,《申报》1938年12月18日,第7版。日军占领苏州的甪直镇后,“镇民不敢出外,年青妇女,更是深深地藏匿,后来因为有了慰安所,伪居留民办事处又‘先意本旨’地供应他们,使他们事事满足,骚扰也就好些了。”⑥《一年來之角直鎮——日军驻屯下烟赌极盛潘志铨奉伪令作威福》,《申报》1938年10月18日,第7版。苏州的这些慰安所很明显是日军授意当地汉奸建立的,在防止日军骚扰当地女性的借口下,慰安所成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地方。在镇江,“日军来镇驻防荼毒民众,无所不至,汉奸亦出而活跃,组织伪维持会,以事供应,并设慰安所,以便日军之性欲冲动,得有所解决也。”⑦《顾亭林故里沦陷后惨遭蹂躏顾墓之前曾被日机投弹二枚日军与汉奸等极力荼毒民众》,《申报》1938年11月17日,第7版。在华南,日军进犯广东三水县时,对县城进行狂轰滥炸,“县府前座及河口大码头各大建筑物,多被弹炸,而日军且据县府以作大本营,辟救济院为日军慰安所。”⑧《粤省各属被日机轰炸之灾况汕头及西江一带均极惨重》,《申报》1939年5月29日,第7版。三水县的慰安所是日军直接建立的、专供日军享乐的直营慰安所。由此可以看出日军利用一切可能的场所来设立慰安所。
在各地慰安所中,日军在扬州开办的慰安所颇具代表性,《申报》对此有详细介绍:
日军初占扬州,留城妇女被其蹂躏,性情激烈者,跳井投河,懦弱者,忍辱偷生。虽有卧床装病,女扮男装,亦难幸免。后经傀儡方小亭与日军司令天谷商定,准设慰安所,在新胜街大陆旅社,由著名龟奴沈家庆办理,召集原有妓女八十名,惜求过于供,言语不通,致发生妓女被殴伤,衣袴被撕破等情事。日军自由在民家强暴者,仍占多数,以致妇女居城者,纷纷远避。大陆慰安所开幕后,风波迭起,沈家庆屡遭被打。而生涯甚好,继起者,有绿杨慰安所,并有通译招待,日方在亨得利钟表店,设立“扬州野战润保”,有日鲜艺妓。新胜街特别热闹,旋经另一方日人觊觎,遂将掠来妇女百余名,在城外汽车站设立慰安所,代价比城内减半,(每小时五角,城内一元)以为竞争。自华南战起,湘鄂军兴,日军纷调他处,扬城日军仅百余名,并且数月无饷,穷困已极,各慰安所生涯冷落相继停止,现在只有特别慰安所一处,在左卫街盐商周扶九住宅与伪警局遥遥相对,此慰安所系日军官纵欲处,代价较昂,日军兵士之慰安所,则在背街小巷中。⑨《扬州烟赌娼鼎盛 日方实施毒化政策之一斑》,《申报》1938年12月16日,第7版。
这则报道中出现了日军直营的慰安所、日侨开办的慰安所和伪政权开办的慰安所,还有日军军官专用慰安所和士兵专用慰安所。“慰安妇”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日本和朝鲜半岛女性。可以说,日军在扬州设立的慰安所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一个缩影。
在强征“慰安妇”方面,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各部队全面推行后,大量女性被以各种方式送进慰安所,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在中国大陆战场,不仅有中国当地的女性被强迫沦为“慰安妇”,更有日本国内、朝鲜半岛的女性也被日军蹂躏。日军征召“慰安妇”的方式主要有强征、欺骗、诱拐等,这些被送进慰安所的女性每天遭受人数不等的日军蹂躏,身心备受摧残。在江苏如皋,“为了要满足日军的性欲,所以被占领了的市镇里都设有慰安所,在那里面有许多年轻的花姑娘,相同妓女似的,过着下贱的苦痛的日子,她们原来都是良家的妇女。”①《如皐沦陷后概况伪自治会严厉压迫民众武力大增坚决抗敌》,《申报》1938年10月25日,第7版。在南通,日军慰安所内不仅有中国“慰安妇”,还有日籍“慰安妇”。据报道,“伪自治会之第一大建设为慰安所,起先设于广雅楼旅社,搜罗难民妇女数十人,供给日军泄欲,取费分五角、一元两种,最近因日军尽驻城南,则又迁至关帝庙东某姓屋内,并有日妓八名,招待周至,甚博日军欢心。”②《如皐伪组织闹饥荒努力罗掘用以媚日富户贫民均遭剥削》,《申报》1938年11月7日,第7版。在杭州,“妓女变相之慰安所,以前散居各处,现在均集中新市场之泗水劳桥桥畔之泗水新村,中有日本、朝鲜、中国三种妓女,每日喧扰万分,泗水新村本为极幽静之住宅区,今则歌舞终天,已非干净土矣。”③《杭伪市府搜括方法各城门口增设厘卡并举办变相人头税》,《申报》1938年10月22日,第8版。在云南腾冲,日军“利用城乡流痞组伪维持会,勒令三日内交足妇女百名,设慰安所,供敌泄兽欲。”④《滇西之敌无恶不做 沦陷区青年纷纷投军杀敌》,《大公报》(桂林版)1942年8月7日,第2版。
1939年8月,伪维新政府的官方报纸《南京新报》创刊,人民慰安所在《南京新报》连续登了一个月的广告,广告词称:“特选择美丽女子数十人在海洞春创办人民慰安所”,⑤《南京新报》1938年8月1日,第6版。并将这些女子的名字全部罗列出来。从姓名即可看出,人民慰安所中的“慰安妇”全是中国女性。任重在《南京慰安所里》一文中提到一个在人民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据她描述,“这儿大部分是苏州人,军部慰安所也有四五个,那边中国人占到十分之七,东洋的女子有十分之三。中国的女子大部分是从难民收容所来的。”⑥任重:《南京慰安所里》,《浙江妇女》1939年第4期。军部慰安所很明显是日军直营的慰安所,专门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军部慰安所里的“慰安妇”有30%来自日本,这个比例相当大。由于日籍“慰安妇”相对较少,因此备受日军官兵的欢迎,一般都是军官才能享受的待遇。在各慰安所中,日籍“慰安妇”都是绝对少数,南京的日军军部慰安所中的日籍“慰安妇”占30%,可见军部慰安所服务对象非同一般。
“慰安妇”是有严格等级区分的。据王璧珍的《慰安所里的女同胞》一文记载:“第一级,是从敌国调来作战而死亡者的妻女,她们的丈夫或父兄因侵华致死了,死耗不让她们知道的,而以欺骗的方式引诱她们来华,说是和丈夫或父兄会面,来华后,却分派到各军营充当泄欲器了。第二级是朝鲜或台湾人,她们在魔掌宰割之下,是要如何便如何的,她们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一被征发是无法避免的。第三级就是遭受蹂躏的我们的女同胞。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享受者是军官,而我们的女同胞呢,所承受的只是那些战兵的践踏。”⑦王璧珍:《慰安所里的女同胞》,《广西妇女》第17—18期,1941年。白芜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女人,当然也分等级,第一等,日本女人,然而很少,只有艺妓与慰安所的‘慰安员’;第二等是韩娼与买海洛因的高丽妇;第三等,东三省籍的女汉奸,受过敌人训练的女子,能说很流利的日语,如在公共汽车上买票的,在广播电台报告的,在小学校当指导员。此外的中国女人只有随时受凌辱,到处受蹂躏了。”⑧白芜:《今日之南京》,第(F)4—(F)5页。
在日军“慰安妇”制度下最悲惨的是沦为性奴隶的“慰安妇”,她们被迫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遭受非人的虐待,有时一天要遭受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日军的蹂躏。王璧珍在《慰安所里的女同胞》中这样描写“慰安妇”的生活:“在值班的那一天,是要承受六十名战兵践踏的,而在践踏时,尚须强作笑容,不能有不愿意的表现,否则,亦会赤裸裸的遭受鞭挞……”①王璧珍:《慰安所里的女同胞》,《广西妇女》第17、18期,1941年。1938年出版的《敌寇暴行录》中有一篇文章记载了一位中国牧师亲眼目睹日军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行乐所”内的场景:
盖该屋各层设有极暖之水汀,其最低一层,有日兵在苏锡昆山浦东各地所掳之我国良家妇女,自十七八岁至三十岁者,约数百人,皆一丝不挂,面有愁容,而日兵则川流不息期间,任竟选择性的满足。如任何女子有不从者,皮鞭立至。此妇告人,自被掳入内,每日至少遭十次以上蹂躏……此所谓行乐宫之二层,有同样命运之妇女,为自三十岁至四十岁数百。②《敌寇的行乐所》,秋江等編:《敌寇暴行录》,文艺社1938年版,第48页。
由上可见这个慰安所规模颇大,“慰安妇”全部为中国女性。日军在慰安所恣意妄为,女性在提供性服务时不能有愁容和不情愿的表情。这是对女性人格的极大侮辱和女性人权的极大侵害。
日军的性暴力不仅针对中国女性,对日本女性也同样表现出罪恶的一面。在慰安所,部分日本“慰安妇”是被日军欺骗而来的。如《大公报》曾在一篇报道中记述了一个日本“慰安妇”讲述自己是如何来到慰安所的:“我们是受了骗。在东京多少和我一样遭遇的女人都有和我一致的要求:亲自来支那看一次我们心爱的人……我们组织了‘索夫团’。我们向军部要求了好多次。但是,谁知道军部骗了我们,强迫我们参加慰安队”。③《手的故事》,《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4月10日,第8版。徐妫在《战时下的日本妇女》一文中写到,在战争中的日本妇女生活十分悲惨,许多年幼的女儿被卖做娼妓,有些才十三四岁。这些年轻的被贩卖的日本女性“其中有许多名组成‘慰安队’,送至中国女人较少的占领区域,做着‘皇军’发泄性欲的对象。”徐妫在文章中还记述了日军大量招募日本女性到中国战场,职业有“医务上需要的看护妇,桃色的‘花嫁’妇女,‘慰安所’中的少女和娼妓。”④徐妫:《战时下的日本妇女》,《文化批判》第6卷第1期,1939年。这些被招募的日本女性的命运如何呢?文章举了一个例子颇具代表性:“有一个日本女学生,激发爱国心,投身野战医院为看护,三天之内被医生与军官轮奸二十九次之多。”⑤徐妫:《战时下的日本妇女》,《文化批判》第6卷第1期,1939年。这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典型罪行。许多女性都是被日军以招募看护妇、洗衣工、做饭工等所欺骗,最终沦为日军性奴隶的,可见在“慰安妇”制度下,即使日本女性也不能幸免。
据不完全统计,战时约有40万女性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各国及少量白人女性。在日军“慰安妇”当中,中国受害女性无疑是最多的。这是因为日军在中国的驻军最多、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估算,中国大陆约有20万女性沦为日军的“慰安妇”。
慰安所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地方,日军官兵常常到慰安所来取乐。在慰安所里,也常常发生悲惨的故事。
任重在《南京慰安所里》一文中记述了一个叫田中横一的日本军人,因为长时间接不到家人的来信而心情郁闷,于是决定去南京的慰安所“放松”一下。慰安所来了一批大阪和横滨的“慰安妇”,因田中的家乡在横滨,所以他想要一个横滨的“慰安妇”。令田中没想到的是,接待他的“慰安妇”是他的妹妹芳子,而更令田中无法接受的是,他的妻子菊子也来到了南京,成为一名“慰安妇”。兄妹姑嫂在南京慰安所的意外相逢使田中横一精神崩溃,不久便上吊自杀了。
田中横一的悲剧绝非个案。小蜂的《湖州城——慰安所里》一文也记载了两个日本军人在慰安所内分别遇到自己妻子的故事,因为不愿接受自己爱妻成为他人“玩物”的事实,这两个日本军人都选择了自缢。文章最后一段文字令人十分感慨:“慰安所里,有着一片清淅的惨哭声,隐隐地在她们的心头浮起。但还是有不少的皇军,正向着这慰安所里,找寻他们的爱人妻子……”⑥小峰:《湖州城——慰安所里》,《世轮》第1卷第3期,1939年。对这一发生在慰安所里的悲剧,《申报》也有详细报道:
据住于油东某处之来人谈,日前白莲迳港南附近某草房内,有两日兵自缢身死,其致死之物为足上之绑腿布。自杀之原因,系发觉渠等二人之妻,在虹口为妓,因二人赴虹口狎游时,适乃妻等油头粉面,含笑逢迎,相见之下,转喜为悲,互相饮泣,一阵伤心之后归而出此下策。死者一名‘知非幸造’,系军特务部南涎警备队长,一名‘森治丸三’系警备队士兵。皮带上扎有遣书数纸,略述彼二人因赴虹口帝国妇女慰安所,撞见离别已久之爱妻,在内为妓,操皮肉生涯,遭遇生平未有之耻辱,无颜再见世人等语,嗣由日军将二尸密运虹口收脸。①《两日兵自杀虹口狎游巧遇妻室事后思量认为耻辱绑腿带结束了生命》,《申报》1938年10月19日,第11版。
最具悲剧色彩的故事发生在扬州的日军慰安所。据鲍雨的《扬州的日兵在自杀》一文记述,一个名叫宫毅一郎的日军军官在扬州大陆旅社慰安所遇到了自己的妻子秋子。不久,宫毅和秋子双双自杀。后来人们发现了宫毅的记事本,得知他们自杀的原因。原来,宫毅一郎是日本长崎人,新婚不久即应征入伍派往中国已经有五个月了。前三个月都能收到妻子秋子的来信,后两个月却收不到了,这使他非常郁闷。后来有人告诉他在扬州的大陆旅社慰安所看到一个“慰安妇”很像他妻子,他便去查证,没想到真的是他的新婚妻子秋子。经询问,宫毅得知秋子是“被征来‘慰劳’皇军的。同时她还告诉他,妹妹因反对出征,被关在牢里,母亲已经急死了。他愤恨,他羞愧,他没有路走了,除了自杀之外。”②鲍雨:《扬州的日兵在自杀》,《抗战文艺》第1卷第9期,1938年6月。因为对战争的痛恨,宫毅和秋子双双自杀了。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被当成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一个典型事例。《扬州的日兵在自杀》发表后,宫毅和秋子的故事迅速被国内多家报刊转载或转述。《解放》杂志第67期刊登了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文彬,于1938年11月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国青年运动的新方向》一文,文中引用了宫毅和秋子自杀的故事,表示:“宫毅和秋子正如许多日本青年一样,还没有能够走上积极和中国青年联合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终于可怜地牺牲了,这正是我们的责任所在。”③冯文彬:《中国青年运动的新方向》,《解放》第67期,1939年3月。后来,宫毅和秋子的故事被改编成了话剧《秋子》,于1942年2月在重庆公演,轰动了大后方。
三、记录“慰安妇”制度的民国出版物的价值和意义
民国出版物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记载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有意识的记述和无意识的记述。所谓有意识的记述,指的是主动去报道、评论“慰安妇”制度的内容,如当时国内出版的报纸、期刊和书籍的相关内容等;而无意识的记述是指本来并不是为了记述“慰安妇”制度,但客观上记录了“慰安妇”制度,如慰安所的广告、日本人在中国出版的涉及“慰安妇”的书籍等。这两种形式的记述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当时国内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记述、报道和评论等,基本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性出发,目的是激发全国民众的抗日斗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时环境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尤其是看到中国女性在慰安所内被蹂躏及被迫提供性服务的报道,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姐妹被日军伤害,更能坚定人们的抗战意志。另一方面,民国出版物对“慰安妇”制度的记录,为今天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从这些记录中人们可以了解日军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于何时何地实施了“慰安妇”制度,有多少女性遭到日军的奴役等等。根据这些记录,再配合“慰安妇”的调查,人们可以了解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真相。
民国出版物对日军“慰安妇”的记录也表达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扬州的日兵在自杀》描述了日军年轻军官宫毅和他的妻子秋子在扬州慰安所相遇的故事,虽然宫毅和秋子双双自杀身亡,但宫毅在最后发出了有力的呼声:“支那人民应该和日本人民联合起来打到日本军阀!”①鲍雨:《扬州的日兵在自杀》,《抗战文艺》第1卷第9期,1938年6月。从这一呼声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宫毅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痛恨。王沣泉所写的独幕剧《慰安所》,通过戏剧的形式展现了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内的享乐和“慰安妇”遭到残酷对待的情形。在独幕剧行将结束时,一名日本士兵在慰安所中对另一名玩弄自己妻子(“慰安妇”)的日本士兵说:“你这种死绝良心的东西,甘心做军阀的走狗,在这儿作威作福,欺负支那人还不算,还来欺负自己人,我今天非干掉你不可!”②王沣泉:《慰安所》,《抗战周刊》第38期,1940年。最后双双毙命于慰安所。这一独幕剧也是在痛斥日军“慰安妇”制度对中日两国女性乃至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使人们无形中感受到和平的珍贵。类似这样发人深省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反映出的共同主题是痛斥战争、呼唤和平。
虽然民国出版物有关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记载使人们对这一罪恶制度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其并没未充分揭示日军奴役女性的战争罪行。究其原因,主要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当时未能充分认识其本质。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慰安所的建立和“慰安妇”的招募。当年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很少由军队直接参与,一般是日军占领某一地区后,指使汉奸或当地伪政权(维持会)具体操作。这些人熟悉当地情况,威逼利诱当地女性为日军“服务”。如战后审判汉奸王士海时指控其在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任敌天津防卫司令慰安所办事处主任,强征妓女供敌兽欲。”③《王逆士海将公审法院已提起公诉》,《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7月9日,第3版。一些不明真相的女性以为只是从事给日军洗衣服、做饭等简单的工作,没想到却沦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还利用日本侨民,将日本国内、朝鲜半岛和台湾的女性带到中国,开设慰安所。《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和《在支半岛人名录》中记录的慰安所即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对“慰安妇”的称谓。一般来说,在慰安所内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可以称之为“慰安妇”。民国出版物中直接出现“慰安妇”称谓者很少,但是将慰安所内的女性称为“妓女”“营妓”等却非常普遍。“妓女”“营妓”是指为了赚钱而自愿出卖身体的女性。而“慰安妇”则是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对“慰安妇”制度不够了解,未能认识其本质,所以在出版物中使用一些传统名词来表述“慰安妇”也就在所难免了。正是由于认识不足,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与遭日军强奸的普通女性并无区别。因此,民国出版物中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描述有一些模糊与混乱之处。
第三,对“慰安妇”制度的记述。民国出版物中记录的“慰安妇”制度往往浮于表面,很多就是单纯描述一件事情,很少对其本质进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从另一个层面说,正因为民国出版物对“慰安妇”制度的记述是质朴的、感性的,没有过多的修饰,所以也最接近事实真相,最能反映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