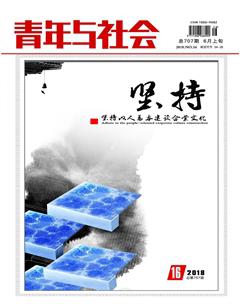巴山作家:刘林微型小说——老杨
刘林
我幼年时曾结识一位朋友,百家姓中常见,姓杨。因为大我很多,打初识我便喊他老杨。他和我是忘年之交,以至于忘年到我们是如何相识。
我刚满十九岁那年的暑假,接到了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电话接通,那头是老杨陌生而又熟悉的口音。老杨自我搬走故乡已些许年头,我甚至快忘记他,他并未多说,只让我抽空回去看他一眼,我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满头疑惑地应了他。放下电话,老杨那副老瘦的面孔时隔多年后又在我脑中映现出来。
我印象中老杨是个实诚人,他说有事便一定有事,藏不住心事却也不多话,三两句说完便休,性格似及了我,不惹人厌,不讨人喜。在我很小我便认识了老杨,怎么认识的早已模糊不清,似乎是因为小时候的某个夏天,在公所的院子里和伙伴们下棋,两小儿操着稚嫩的棋技斗得个你来我往,一筹莫展之时隐约觉得身边有人观瞧,回头一看站着个人,一张略带皱纹的沧桑脸,像老树皮一样。我并没在意他,可他却饶有兴致地自顾在一旁指点棋路,为我谋局。小孩儿玩耍,哪儿管什么规矩,既然有了外援,他如何说我就如何下,一来二去我的棋艺已是超过同龄人许多,看着公所大院里的同龄人甚至大人败我面前,这种成功的满足感和虚荣心让我享受了很久。那后来,老杨便天天在院里陪我下棋,一来二去,我“业务精进”,和老杨也日渐熟络,先是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到后来他干脆主动提出认我做个小兄弟,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深了起来。
说起老杨的年龄虽大,可我从未见过他家人,每次一到下棋玩耍的时候,我在他便陪我,我回家他也就与我道别,他似乎从没逗过其他小孩,我也从没见他上班工作,年幼的我甚至还异想天开怀疑他不是正常人。我去过他家,离我们这不远,只需穿过三条巷子和一条街,在一个土坡旁边,是一户独家独院的木头房,我虽然只去过一次,但却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屋门口有棵大树让我记忆深刻,小时候的我看着这棵树,觉得无比巨大,我问过老杨,老杨说,这树年龄和他一样,他小的时候就有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看着树皮,再看看老杨树皮一样的脸,还真有那么一点相似的沧桑。
我便坐车去了老杨家,仍是那条路熟悉的路,门前那棵树已没当年挺拔,如同十几年风雨经历过来的老杨,也渐渐显出疲态。顺着路走过去,远远看见老杨端个茶盅倚在树下等我,仍旧那个老房子,仍旧是一个人。我快步走到跟前,终于又听见了老杨那枯木般独特,令我打小就熟悉的嗓音“哈哈,来挺早啊”,我听得出他言语中老迈的疲惫,接过了话“是啊,今天车少,昨天下了雨路上没人…别站着了,快进来坐,茶泡了,酒倒了,菜好了”说着便领我进屋。老杨的家里仍是十几年前不变的摆设,破落的小屋子,苍痕的木板,我落座在一个树墩子改造的凳子上,眼前满桌酒菜,菜是老杨亲手做的,我甚至才发现桌子凳子都是老杨亲手做的。他跟我说早年他是一个木匠,如今老了,就没再弄这些玩意儿。我无心留意这些变化,只想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老杨并不慌忙,给自己斟了一杯茶水,在我面前坐下满脸是惆悵,却也不直接回答我,随便扯了个话题,同我聊了许久的家长里短。我看他这副模样想必没有什么大事,也随着他长吁短叹时光不易起来,那年我搬家进县城,临走的时候老杨还来过看我,我曾许诺会年年回来拜访他,却年年亏欠,这个时候才想起,我是真的是很久没来这儿了。
桌上老杨和我交杯换盏,他举一杯我便陪一杯,如同当年下棋,他说一句,我便走一步。饭过五味,他起身在床枕下摸出来一张照片给我看,接过照片来,一股年代的沧桑从我指尖传遍全身,不由得打了个激灵,照片里老杨站的位置似乎就是这个地方,我一眼就认出他倚靠的大树,不过当年那个树还没现在这么大,也没这么老,看起来一副破落荒凉的景色,现在城市处处都在发展,似乎连这点破落地儿也跟着沾光变得亮丽不少。老杨说道“这是刚在这里的时候留的影。最近来了一群人,说要把这里改造,让我去另一个地儿住,下个月的今天听说就动工了。我的老房子要没有咯,这不,抓紧喊你来吃顿饭,一是叙叙旧,二是以后啊说不定已经见不到我了……”老杨如鲠在喉一般,把他后面想说的话硬咽了下去,转而苦笑地说了句“算了吧,不说了”。我当时并未理解,为什么老杨给我要讲这些话,只觉得也许他只是无处诉苦,似乎只有我是他的亲人,从未想过他是否有妻儿老小亲戚朋友。看着老杨脸上的疲惫和恐惧,只感觉酸甜苦辣的菜陪着酸甜苦辣的人,渐渐被时间这个胃消磨殆尽。这一顿饭不知道吃了多久,谁都心照不宣地不忍道别,老杨醉醺醺地送我到车站,我已经上车,汽车发动没多远,老杨打来了电话,仅仅对我讲了句“这些年来谢谢了。”不及我追问,便挂掉了电话,剩下那头的一阵忙音。我想也许他只是喝醉了。可坐在回程的车上我仍旧一路回想,好好的为什么要说谢谢。
转眼一个月过去,我想起老杨说他家里那片地要被开发,就是前几日动工,我抽了个日子想回去看望。到了地方发现木屋旁的那棵大树已经不存在,似乎已经开始施工前的清场。我发现木屋还在,上前敲开了门,看见的却只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透过缝隙间打量了一下屋子,老杨并没在屋,唯独剩下那套桌椅板凳,和一堆木匠工具。我看着眼前的男人,极力想掩盖住焦虑地心“劳驾,我是来找老杨的。”他却突然一愣“老杨?谁啊?”他这一愣把我弄得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接话,“你不知道住这的老杨么?”“什么老杨,这是我家,我住几十年了现在这片都要拆了,我都不记得还有个老杨”我眉头一蹙“哦哦哦,不好意思可能我记错地方了。但是这屋子我好像记得旁边有很大一棵树”中年男人挺直腰杆提高了调门“哦,这个啊!上次开发这的老板说,这树几十年树龄都没成材,不直又不好看没啥用,给推了,后面要补偿,还要……”我不记得这个男人后面说了哪些话,只觉脑子一嗡空白一片,想掏出手机打给老杨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号码中拼命寻找,却始终翻不到他的电话。我抬起头打断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中年男人“哥,劳驾我问一句,这棵几十年的树是啥品种?”他瞳孔中倒映出满脸呆滞和惶恐的我,紧接着耳边回荡起了他的回答。“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