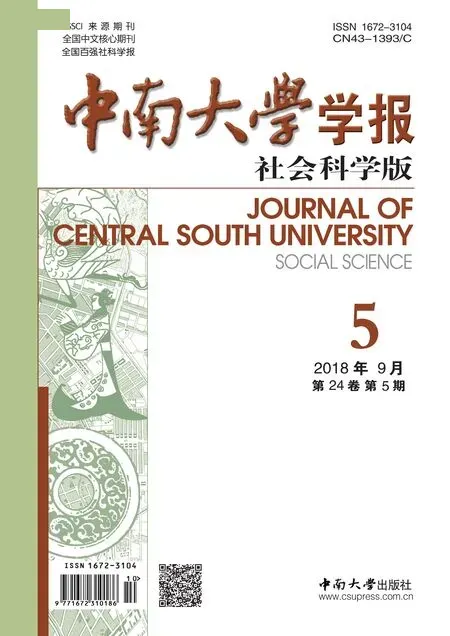特别行政区宪法解释提请权的法理依据与实践动因
朱福惠,张晋邦
特别行政区宪法解释提请权的法理依据与实践动因
朱福惠,张晋邦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实践证明,如果不能将宪法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治理,基本法难以独自支撑。所以,特别行政区应从基本法治理向宪法和基本法治理转型。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主要是宪法适用和宪法解释问题。宪法和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在何种条件下有提请解释宪法的权力,立法法也没有对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的违宪审查要求权作出规定,实质上未能正确地对待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不利于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和解释,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适用宪法实现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所以,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宪法解释提请权的运用虽然是宪法适用和宪法解释的程序性权力,但符合我国的宪法体制和宪法解释原理。通过宪法解释提请权的行使,可以解决特别行政区法制实践中的紧迫问题,从而维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权威。
宪法治理;宪法解释;提请权;特别行政区
一、基本法治理模式的局限①
我国特别行政区的治理遵循“一国两制”原则,通过宪法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基本法并确认高度自治而实现。特别行政区大体经历了从政治构想和外交承诺到建构宪法制度,从宪法制度到法律实施,再从法制到法治三个发展阶段[1]。具体来说,这三个阶段是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一国两制”构想形成时期的战略治理阶段,特别行政区制度入宪至两个基本法颁布之前的政治治理阶段,两个基本法正式颁布施行至今的法律治理阶段。作为“一国两制”理论的主要制度载体,依托于基本法施行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一国两制”实践逐渐遭遇治理难题,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凸显[2]。尤其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伴随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行政区内部社会政治对抗氛围趋浓,主要政治力量对立加剧,政治共识难以达成;行政主导体制不彰,立法会反对派掣肘施政,法院司法能动意识强烈;部分港人存在国民认同危机,导致极端势力浮出水面。从七一大游行到国民教育事件,从占领中环到立法会选举呈请风波。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之后,香港政争仍然难止,2017政改方案再度折戟,重启艰难。当下的特别行政区治理以及基本法的实施面临严峻挑战。
基本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宪法性法律[3],是特别行政区内部各项制度、政策和本地立法的依据与基础,在特别行政区具有凌驾地位[4]和主导地位[5]。基本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其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主要法律载体与生俱来地承载了“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具有的内在张力。作为“活的文件”(living document),基本法发挥包容、妥协以及平衡和再平衡的制度改造能力[6],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而发挥其宪制整合功能。“一国两制”的核心诉求在于舍弃意识形态争议,以国家体制的高度包容完成国家统一,是主权者的自我设限。回归以来在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具体方式选择中,主流观念寄望于创设基本法治理模式完成特别行政区管治。这主要表现为“一国两制”之下内地与特别行政区各自保持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变,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由基本法予以确认和保障,制度差异和制度竞争被寄望于在一国之内相互融合并逐渐消解,国家主权权力与主权行使以及宪法的效力则主要通过发挥基本法的纽带作用予以转化和传导。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区一国共存、各行其是、同台竞争、共同发展。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中,基本法的主导作用和基础作用也历来不断受到学界主流观点的共同肯认和强调。认为香港基本法可以保障香港的法治[7],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法律化,关于香港治理方式的种种设想都是为了保持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繁荣稳定,基本法是这种治理设想的治理依 据[8]。
但事实上,特别行政区的这种基本法治理模式不仅容易造成实践中对国家宪制理解的偏差,而且滋生特别行政区治理的政治隐患。首先,基本法是一部宪法性法律,但不是宪法。对基本法地位和作用的过分依赖与强调,容易造成宪法与基本法关系失衡。基本法不仅被视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基石,更被看作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划分政治权力的宪法文件,将基本法视为“小宪法”“宪法特别法”“特别行政区宪法”。这实际上违背了宪法是最高法、根本法的基本原理。由此在法理上割裂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基本法成为排除宪法充分适用的制度因素,从而导致宪法在特别行政区效力和适用受到长期困扰②。其次,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来说是一部授权法,对基本法地位和作用的过分依赖,容易产生特别行政区管治实践中的政治隐患。对于授权法独立性的过分强调,消解了中央作为授权者的主权决断地位,遮蔽了中央管治权的最终性和合宪性,催生了特别行政区不受中央干预的泛自治要求和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护倾向,纵容了特别行政区的“挣脱情绪”[9],弱化了特别行政区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宪法义务。以致多年来所谓国家与特别行政区“井水不犯河水”的口语化表述从确保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的政治决心被异化为一种相互区隔的政治口实,“一国两制”的内涵被误解为“一国”与“两制”同位、“一国”与“两制”同等的宪制立场。
我们应该看到,首先,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10],本应通过宪法详细规定。基本法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以普通法律承载宪法功能的制度,其自足性③只宜在基本法这一次级规范体系中认识,基本法作为单一的宪法性法律并不能解释自治权的来源及其程度,因此,基本法具体条款的效力和内涵只能置于国家整体的宪制秩序中去理解。其次,授权关系不同于分权关系[11](124)。在授权框架下,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予并且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授权的结果既不应产生分权模式下的灰色区域,也不应产生人权语境下的对抗权[12]。港澳回归后,虽然港澳法律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予以保留,但其制度体系背后的根本规范以及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为核心的新宪法秩序取代了原有宪制,中央针对特别行政区获得了一系列宪制权 力[13]。事实上,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权不仅包括基本法管治权,更包括宪法管治权,宪法的空间效力决定了其整体适用于特别行政区,宪法的部分条文可以在香港直接实施,无须通过基本法转化适用。再次,就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而言,基本法并非仅以宪法第31条为依据制定。宪法第31条虽授权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且基本法有权规定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但基本法的制定是以整部宪法为依据,基本法在全国发生法律效力,并非只适用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亦在序言中明确规定是根据宪法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以,宪法是在特别行政区具有效力的根本法,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了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基本法体现了宪法的制度构造和基本精神。
综上所述,基本法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基础性法律,虽然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构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将之与宪法割裂,则扩大了主权与特别行政区治权之间的逻辑裂隙,隐含着香港高度自治与宪法和主权的普遍性、统一性之间的逻辑裂隙④。若将宪法排除于特别行政区治理之外,基本法本身蕴含的政治张力和根本规范的非自足性使其难以承担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宪制任务。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既是地方治理,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4]。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现代法治并非一般的规则之治,而是宪法至上的宪法之治。宪法不仅为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正当性渊源,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制度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宪法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15]。宪法本身内蕴了正义、自由和秩序的价值意涵,其通过分配政治权力、规范国家权力、预防社会混乱和调节利益关系,能够达成民主、平等和人权等宪法价值实现的积极效果。概言之,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法,其人权保障作用有利于接纳并吸收特别行政区的人权政治语境中的权利保护倾向,其规范和控制国家权力运作的功能则有利于整合中央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行政区宪制的完整含义应该在规范相互关联的整体结构中予以理解,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共同基础论”有利于夯实“一国两制”的宪法保障⑤。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充分适用也有利于国家统合的达成[16]。特别行政区治理应该完成从基本法主导型治理模式向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治理模式的时代转型。
二、特别行政区宪法解释程序的缺失
宪法治理需要国家机关运用宪法思维、适用宪法规范来处理国家或者地方事务,而宪法治理的基本形式是宪法适用与宪法解释,如果没有宪法解释制度,宪法治理模式即不能有效运作。在特别行政区的治理过程中,特别行政区法院多次适用宪法裁决案件⑥,并且通过判例确立违反基本法之审查权对国家宪制进行具有争议的司法审查作业,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发布具有宪法解释性质的决定和决议,其目的在于通过宪法之适用与解释维护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秩序。这表明特别行政区治理中也存在宪法适用的实际需要。然而,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治理观念的影响下,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和解释并没有构成其宪制构架的组成部分。相反,以基本法适用排斥宪法适用的观念较为流行,严重矮化宪法的根本法和最高法地位。国家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常常较少考虑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关系,认为特别行政区的治理以基本法为限。因此,无论是特别行政区还是国家立法,都将“一国两制”视为僵化的基本法体系,从而构成法律体系的双向封闭。由于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不能解释宪法,同时也没有提请宪法解释的权力,导致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缺乏制度基础。
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而且从宪法文本的表述以及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和法律解释权为排他性权力,除非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或者制定法律明确授权其他国家机关解释。宪法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体制,此种体制称之为抽象的宪法解释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审理案件,因此不能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解释宪法。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依职权主动解释宪法,但是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法院提出解释宪法的要求或者建议,具有重要的作用。立法法第46条规定国家机关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法律的要求,而第99条规定,国家机关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和条例抵触宪法与法律的审查要求和建议,此种要求权和建议权可以统称为请求权。所以,宪法解释的提请权是指不具有宪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在适用宪法和法律,或者在履行职权过程中产生宪法争议和疑义时,依照法律的规定向宪法解释机关提出解释请求的权力。凡实行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解释体制的国家,均在宪法和法律中确认宪法解释提请权,并且将社会团体和公民纳入提请主体的范围。宪法解释提请权是宪法解释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程序性权力。宪法之所以确认宪法解释的提请权,其目标主要在于:其一,通过国家机关的宪法解释提请权,拓展宪法的实施与适用领域,避免宪法解释机关垄断宪法适用,真正实现宪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其二,通过国家机关的解释提请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赋予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监督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的责任,从而弥补宪法司法适用机制的形式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之不足。
从实践层面来考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在多数情况下均由其他国家机关提出解释请求而启动,所以,抽象的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一样都需要其他国家机关的提请才能有效运作。赋予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宪法解释提请权,是推动特别行政区宪法治理转型的重要制度架构。国家机关在实施和适用宪法与法律的过程中,如果遇到需要明确宪法条文的具体含义或者对法律的合宪性产生疑义时,需有权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基本法的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别行政区法院行使,但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依照职权进行解释或者根据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提请进行解释,所以基本法的解释不仅在体制上较为完善,而且符合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解释体制。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解释体制,应与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解释体制具有同构性。
特别行政区的宪法适用和解释缺乏制度支持,表现在特别行政区法院适用宪法裁决案件以及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的宪法解释和合宪性审查提请权没有直接而明确的法律依据,基本法和立法法均没有在具体操作层面涉及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解释问题⑦。可见,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治理观遮蔽了宪法治理观。因为在特别行政区治理观上,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被视为只能透过基本法间接适用,所以,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实施过程中的解释问题被不合理地转换为基本法解释问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构成国家基本制度的宪法基础。“一国两制”是八二宪法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肯认,基本法是宪法“一国两制”架构的具体化,因此,基本法不仅在“一国两制”层面不能替代宪法,而且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和法律解释制度等方面更不能替代宪法,基本法解释同样不能替代宪法解释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本法没有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享有宪法解释权或者宪法解释提请权,但基本法的自足性并不意味着其授权模式的封闭性,简单地从基本法缺乏显性授权条款便否认特别行政区拥有宪法解释提请权,是对宪法与基本法关系的误解。根据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特别行政区有权享有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但是,出于对基本法治理的固有认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在规定地方权力时常常忽视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的职权,从宪法审查和解释的权限来看,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特别行政区宪法解释提案权阙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虽然为抽象解释,但其解释具有法规范的效力,是一种造法活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工作程序,宪法和法律解释的启动程序与立法程序同构。据此,我国现行宪法解释体制和运行程序应该根据宪法,结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法律予以理解,从中推论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解释提请权及其行使之必要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立法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2条明确了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议案的主体是中央国家机关和一定数量的代表委员。立法法第26条、第27条明确了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法律案的主体是中央国家机关和一定数量的代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11条也将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提请权主体确认为委员长会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十人以上联名常委等中央国家机关及团体。可见,我国的国家立法权主要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其他中央国家机关在程序上具有法案提请权,而包括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内的地方政府均没有国家立法的法案提请权。所以,从立法权层面,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无权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的议案。
第二,立法法对审查和解释提请主体的限缩。宪法审查的本质是宪法判断,宪法解释的本质是宪法理解,宪法审查以宪法解释为前提,宪法解释必然形成宪法审查。一般而言,有权提起宪法审查的国家机关必然有权启动宪法解释。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审查权⑧。目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审查程序作出明确规定的是立法法。根据立法法第99条第1款之规定,只有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才能针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提出违宪审查的请求,立法法没有规定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的违宪审查要求权。根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之规定,除该条第1款列举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如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可见,立法法并没有明确排除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违宪审查的建议权。
虽然立法法并不是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全国性法律,但该法第8条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属于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表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有关特别行政区方面的法律均受该法之拘束,因此特别行政区虽然不能直接适用该法,但对依据该法制定的有关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以及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应当拥有宪法审查和宪法解释的提请权。这不仅是治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适用的需要,更是确保宪法第31条所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稳固的需要。立法法只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抵触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法律是否抵触宪法的问题。但从宪法至上的原理出发,法律仍然有抵触宪法之可能。根据宪法确立的解释体制,如果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发生抵触宪法之争议,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之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解释。特别行政区在适用基本法和其他全国性法律的过程中,遇到需要解释法律合宪性的情形,如果不能扩大适用立法法第99条第2款之规定,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高度来对待宪法解释提请权,则宪法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中的作用将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解释提请义务
(一) 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有实施宪法的职责
宪法解释提请权是宪法适用和解释的程序性权力,要实现特别行政区的宪法治理,必须要实现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与解释。否则,基本法治理模式之观念仍然难以实现转型。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在现行宪制下的宪法解释提请权,可以由特别行政区法院在适用基本法和全国性法律时提出,也可以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或者立法会一定数量的议员提出,同时也可以由行政长官提出。特别行政区法院和立法会的请求权在法理上之正当性自不待言,然而,行政长官的提请权则需要从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的角度出发予以特别说明,由于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首长,其法律地位不能与内地省级行政机关之行政首长相提并论。特别行政区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实行行政长官主导下的分权体制。鉴于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主导体制,根据基本法的相关规定,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首长,代表特别行政区对中央负责,负责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执行基本法和其他法律,拥有包括行政权、人事任免权、立法权在内的广泛权力。因此,赋予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违宪审查和宪法解释提请权比较符合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从宪法原理出发,宪法解释之提请权的主体资格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享有宪法职权并对其管辖的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二是享有宪法职权的国家机关具有适用和执行宪法的权力,其适用和执行宪法的行为直接发生法律效果。
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行政长官应当具有解释宪法的提请权。根据宪法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宪法这一条款体现了国家在设立特别行政区制度时需要遵循必要性原则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原则。不同于内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行政区政制是权力制衡基础上的行政主导体制。第一,在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上。根据基本法相关规定,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首长,代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基本法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负责。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拥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法律地位。第二,在行政长官的产生上。根据基本法的相关规定,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较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而言,具有较为广泛的认受性和民意代表性。第三,在行政长官的任命上。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批准任命,对中央负责,与中央政府具有较为紧密的宪法和法律联系。第四,在行政长官的职权上。基本法赋予了行政长官包括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执行特别行政区法律、法律签署权、法律公布权、财政预算案签署权、行政决策权、行政命令权、人事任命权和提案权在内的广泛职权。可见,特别行政区政治架构主要是围绕行政长官设计的。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既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的宪法职权,其决定权也直接发生法律效果。因此,特别行政区宪法解释提请权作为非常重要的宪法权力,也应当赋予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使,以此进一步巩固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主导体制。
(二) 特别行政区可以行使法律赋予省级行政区的部分权力
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为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域,因此,在行政区划上,特别行政区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行政区。根据主权原则,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发生直接拘束力,特别行政区的设置及其高度自治权的授予,均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法律而实现。特别行政区不仅需对宪法规定的外交、国防等中央政府权力予以尊重,而且还需要受宪法和法律解释体制、立法制度之约束。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基本法没有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宪法解释权,表明全国人大并没有将宪法的解释权授予特别行政区行使。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虽然没有宪法解释权,但是,宪法确立的解释制度在特别行政区具有效力。基本法颁布施行之初,全国人大以决议的形式确认港澳基本法合宪,但全国人大对合宪性的理解止步于合宪性宣告,未能进一步阐明基本法为什么合宪,导致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定位以及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如何适用宪法和法律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学界先后出现了特别行政区宪法论、基本法律论、宪法特别法论、八二宪法变迁论等几种基本法合宪性推定理论[17]。特别行政区宪法论试图化解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基本制度与现行宪法相抵触的事实违宪争议,将基本法上升为特别行政区宪法典,以期与八二宪法比肩而立。其认为特别行政区制度以基本法为准即可,无须与内地宪法产生联系,以此解释八二宪法部分条款难以在特别行政区直接实施的现状和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所具有的最高宪制地位。但由于基本法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授权,因此基本法宪法论违背了宪法一般原理和我国单一制的结构形式。基本法律论借助于全国人大国家权力机关天然合宪的宪制地位⑨,认为宪法第31条明确了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确立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权力,因此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属于基本法律,基本法律并不违宪。但基本法律论难以回答的是作为下位法何以能够修改上位法,基本法何以能够作出与宪法不一致的规定。宪法特别法论试图以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化解基本法违宪争议[18],但其有将八二宪法弱化为普通法之嫌,与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殊难匹配。八二宪法根本规范变迁论[17]则直陈我国现行宪法已经由过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变为了一部多元共和制宪法,宪法第31条是对五四宪法以来的共和国体制的重塑,八二修宪与七五修宪和七八修宪的显著区别在于宪法的根本规范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般行政区和民族自治区实行社会主义共和制,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共和制”。但八二宪法根本规范变迁论难以有效解释基本法第5条明确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时间期限,此外,其关于八二宪法修改性质的认定,关于宪法根本规范的界定,都存在可进一步研究之处。
从宪法史的角度观察,八二宪法确立的央地关系在发展进程中的变迁可以有效理解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八二宪法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规定是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重大变迁和实验。五四宪法以来,我国的央地关系经历了数次调整,但都是在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局部调整。如果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经济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单一制结构形式的初步改革,那么八二宪法确立特别行政区制度,则意味着特别行政区地方国家权力的自治范围从行政权、立法权进一步扩大到了司法权,国家权力下放的考量因素则逐步从民族因素发展到了经济因素乃至领土与主权因素。我国已经由传统的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单一制国家逐步发展为一个传统型单一制与地方自治型单一制并存的国家。因此,宪法第30条和第31条共同完成了这种国家结构形式的转型与建构。宪法第31条不应当被看作是第30条的特别规定,其与宪法第30条的规范关系应该被解读为一种并列关系,一般国家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以及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具有对等的宪法地位,共享国家机关所应享有的共性和基础性宪法权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以及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都来源于中央授权,虽然授权的内容和形式存在差异,但不影响宪法在这些自治区域的整体效力。
立法法第46条明确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权,立法法第99条明确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要求权以及其他国家机关提出违宪审查的建议权。由于我国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的同构性,以及“无解释即无审查”的违宪审查与宪法解释的关联性原 理[19],一般地方国家机关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拥有宪法解释提请权的规范空间。因此,将宪法第30条和第31条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其他省级行政区均属于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如果法律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内地省级国家机关拥有宪法解释提请权,则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也相应拥有宪法解释提请权。同理,基本法与地方政府组织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具有同等法律位阶,均属于对宪法第30条和第31条的实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因此特别行政区制度虽然一再被强调并非权宜之计,但特别行政区制度具有的实验性质也非常明显。如果特别行政区制度被证明是五十年之后也无须变化,则现行宪法必须进一步修改,对应宪法第三章第五、六节的安排,在其第三章第七节中对特别行政区制度予以明确。
(三) 特别行政区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义务
普通法院解释宪法和法律的国家奉行司法中心主义,而宪法法院或专门机关解释宪法的国家既将宪法解释作为监督宪法实施的司法过程,又将之视为政治过程,一切法律、法规、命令和行为均不得违反宪法,所有国家机关均具有遵守宪法、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及宪法第5条的规定体现了这种宪法观念。在此种宪法观念下,所有国家机关均非消极被动的中立者,而均属于宪法守护者。国家机关提请宪法解释意味着对宪法规范效力的维护,是遵守宪法和实施宪法的行为,由于其具有纠正违反宪法和法律行为的功用,更应被理解为履行一种能动积极的护宪行为。因此,从宪法文本的角度来观察,国家机关的宪法解释提请权已经成为宪法解释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解释的提请主体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和公民⑩。
但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根据具体情况实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因此,宪法第31条的特别规定与宪法第5条的法制统一原则从内容上看似乎存在冲突。但是,宪法第31条和基本法的规定,仅仅在于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应当主要适用基本法处理特别行政区事务,并不是在全国性法律与基本法之间截然分割,即并没有也不可能切断全国性法律与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事务之间的联系。部分全国性法律可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其他有关特别行政区的全国性法律虽不直接在特别行政区实施,但也不得抵触宪法第31条及其所确保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对此应有权提请宪法审查和宪法解释予以监督,以落实宪法第5条和宪法第31条的共同要求。应当认为,特别行政区制度写入宪法第31条后,宪法第5条中原有的“法律”“法制”“法治”等表述的规范含义得到了更新和扩张,特别行政区法制成为国家整体法制的一部分,国家法律体系包含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香港回归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别行政区原有法律进行的审查和采用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宪法第31条是对包括宪法第5条在内的原有宪制的更新,宪法第5条同样主张保障宪法第31条所确立的特别行政区法制。宪法第31条与宪法第5条同处于宪法第一章总纲之内。一般认为,宪法总纲的内容是国家基本原则的概括性规定,总纲在整个宪法结构中起着指导性、原则性和统一性的作用,是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设定之法律依据,是宪政体制形成和运作的基础。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仅以宪法第31条为立法依据,也是宪法第5条的体现,在宪制层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至上和法制统一原则的立法适用。基本法第20条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这是宪法第31条的开放性解释。所以,立法法第46条和第99条有关地方政府权力的规定完全可以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拥有赋予的宪法解释提请权,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法制统一、确保宪法实施的义务所在。
四、特别行政区宪法解释提请权的实践动因
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法规范体系来看,宪法、基本法、全国性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和决定、特别行政区本地立法等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均有产生宪法疑义或者合宪性争议的可能性。由于基本法并未对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适用宪法的程序作出规定,在特别行政区法院没有获得宪法解释授权的背景下,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或者建议解释宪法的权力显得必要而迫切。
(一) 宪法在特别行政区适用引发争议
依据主权原则,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效力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宪法规范在针对主体、事项或者空间上有不同的效力指向和特点。有的条款具有直接拘束力,如宪法序言第9、13自然段,宪法第2、4、29、31、57、62、67、85条等,这些条款涉及国家主权、基本法律制度、中央国家机关之职权,不仅是特别行政区制度建立的宪制基础,也是特别行政区处理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由于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宪法的部分条款在特别行政区只具有间接整体拘束力。这些规范是“一国”的根本制度,是界定“两制”的规范依据,不承认这一类宪法规范在特别行政区的效力,国家的宪法秩序就会受到破坏,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就会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那些不在特别行政区直接适用的宪法条款,同样对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具有拘束力和间接适用性[20],它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因此,宪法在特别行政区整体上是适用的。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遇到需要适用宪法来裁决案件或者需要援引宪法条文来说明裁判的依据时,可以在判决书中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如果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适用的宪法条文产生疑义,或者对适用的全国性法律产生合宪性争议时,应有权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或者阐明法律的合宪性。当特别行政区其他国家机关在适用宪法和全国性法律时对宪法条款产生疑义,或者适用法律遇到合宪性争议时,可以由行政长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或者阐明法律的合宪性。
因此,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必然引发宪法解释。回归以前,香港法院依据英皇制诰,有权根据人权法案对适用于香港地区的法案进行司法审查。回归之后,香港的普通法传统得以保留,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力得以延续。所以香港法院系统一直拥有受理宪法性诉讼的权力,这一点在回归以后并未改变。这样一来,特别行政区完全可能出现直接以宪法作为诉由的诉讼,而特别行政区法院系统也完全可能受理这一类宪法诉讼,并依据其独立的司法权作出审理。不同于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援引宪法,直接以宪法为诉由的案件更具有解释宪法的迫切性。由于我国宪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因此,特别行政区法院如果受理以宪法作为直接诉由的案件,在必要时应有权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
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运作和基本法适用通过了多项具有立法性质的决议和决定。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的宪制地位,其决议和决定具有补充立法的性质,当其适用引发宪法争议或者产生疑义时,仍然有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过多次解释,并且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立法会普选问题作出过多次决定。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这些法律解释和政改决定引发了香港法律界和政治界较为广泛的宪法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通过宪法解释回应宪法争议,进一步对“一国两制”的宪法精神进行权威而详尽的阐释,不仅有利于平息争议,缓解香港社会广泛存在的法治焦虑,而且适应香港社会的法治思维和传统,对于治理香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 基本法的适用与解释引发争议
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法院拥有案件的终审权并且有权解释基本法。当案件遇到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而终审法院没有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而提请时,由于法院的裁判将会对特别行政区的治理带来重大宪法影响,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就案件争议根据宪法第67条之规定依职权解释宪法和基本法,以制约终审法院的司法权。同时,为维护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和治理的有效性,行政长官可以根据基本法和立法法的原则,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宪法和基本法的建议,以及时缓解终审法院裁决引起的不稳定情绪。比如在居港权案件中,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及时对基本法相关条款作出解释,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将会导致新增近百万内地公民拥有香港居留权,这无疑对香港社会的发展造成难以承受的人口压力。事实上不仅限于经济影响,当案件的审理结果实质上涉及中央权力以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时,终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有可能抵触宪法和基本法。但在基本法第158条的框架下,由于是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判断权归属不明,当终审法院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而其判决将引起宪法秩序的不稳定,并进而对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的宪制基础造成损害时,全国人大可以通过修改基本法或者授权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基本法,从而弥补基本法第158条造成的法律空白。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有权立法,但立法增减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时,实践中会出现引发宪法争议的情形。港澳居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主要由基本法第三章作出规定,并且散见于其他各章。宪法与港澳基本法关于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并不一致,既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同时也在权利内容、权利主体和权利行使的限制,基本义务的履行等方面体现出相当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为处理三地之间民众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困扰。根据“一国两制”的精神,内地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内地公民主要适用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义务。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港澳同胞在特别行政区境内遵循基本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二者本不应该发生冲突。但伴随内地与港澳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三地间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而三地间关于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并不一致,无法简单叠加。此时,宪法与基本法关于基本权利义务规定的属人及属地效力就会发生适用上的困扰。特别行政区的特别应体现为地域的特别,而非身份的特别。如CEPA下陆港间双向人才流动成就有限。长期以来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港澳同胞被比照外国人对待,仅部分高端人才享有内地户籍人口待遇,大部分港澳同胞难以享受与内地中国公民同等的待遇,相关待遇也不如台湾同胞。这与宪法原理不符。另外,在基本法第23条国安立法进程在香港长期迟滞的情况下,特别行政区分裂势力大量违反宪法规定的极端行为也无法得到遏制,有宪法适用的必要。内地与港澳之间权利义务规范的这种宪制状况,既不符合宪法原理,也不利于人心回归和国家统合。就特别行政区而言,根据两个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及法院均拥有一定的造法权力。当这些机关作出涉及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增减的立法行为时,必然涉及宪法相关权利义务条款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或者对特别行政区同胞的效力问题。特别行政区法院和行政长官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应有权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以确保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的宪法权利,明确其在特别行政区的宪法 义务。
(三)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适用引发争议
根据基本法规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是关于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法律。一般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不得对其进行实质性变更,但可以根据特别行政区法制特点对全国性法律作出适应性转化[21]。例如,为了实施国旗法和国徽法,立法会制定国旗及国徽条例,转化了不适应特别行政区法制的相关立法。但需要注意的是,立法会的立法转化行为事实上处于缺乏监督的状态,有可能引发宪法争议。在1998年元旦出现的“侮辱国旗案”中,香港特别行政区针对两名被告侮辱国旗、区旗的行为提出刑事检控的依据是国旗国徽条例和区旗区徽条例,这两部条例将侮辱国旗、区旗行为入罪。但这一依据曾经一度受到香港上诉法庭的司法审查而被认定无效。在“侮辱国旗案”中,至少有两方面的权力冲突引发了宪法争议[22]。一是特别行政区立法权和中央立法权的冲突。表现为国旗法和国旗及国徽条例的效力问题。国旗法作为全国性法律,应当是国旗及国徽条例的立法依据和效力来源,香港本地立法的法律效力应当从属于全国性法律。但《国旗及国徽条例》第9条第2款规定,“如本条例与根据《基本法》附件三公布的任何全国性法律有不相符之处,本条例须解释为该全国性法律的特别实施或改编本,并如此实施”。该条款其实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自我宣告为全国性法律的特别法,从而起到优先适用的法律效果。该条例的这款规定显然不符合法律位阶效力原理,也不符合宪法确立的立法权限。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全国性法律作出的特别规定才构成特别法律,任何地方立法的技术性修订不得抵触或者变更全国性法律的实质内容,因为全国性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属于中央立法权的事项范围。两个条例其实体现了特别行政区立法权和中央立法权的冲突。如果其适用引发宪法争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法院有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基本法,以缓解立法权的冲突。二是特别行政区司法审查权和中央立法权的冲突,表现为特别行政区法院系统有无权力对全国性法律进行司法审查。在“侮辱国旗案”中,香港法院以基本法的表达自由条款和人权条约对国旗及国徽条例第7条将侮辱国旗行为入罪的规定进行了审查,但国旗及国徽条例第7条是对国旗法第19条及刑法第299条的落实。法院固然有权对本地立法进行司法审查,但如果该立法的相关规定并非特别行政区固有,实质上来源于全国性法律并从属于中央立法,此时特别行政区法院实质上就构成了对中央立法权的间接审查。特别行政区的本地立法和司法审查均不能抵触中央立法,尤其不能对全国性法律的内容进行合宪性审查,只能够作技术性适应。在“侮辱国旗案”中,侮辱国旗入罪是中央立法在全国性法律中已经确定的事项,特别行政区上诉法庭的司法审查作出侮辱国旗无罪的判决显然与此抵触。这一司法审查行为体现了特别行政区司法权和中央立法权的冲突。对此种宪法争议,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当然,为了维护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根据宪法第67条之规定,依职权解释宪法,从而制约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维持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权威性。
五、结语
基本法实施的实践需要转换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思维,“一国两制”有待于在宪法层面进一步推进,实践表明,特别行政区治理需要解决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和解释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宪法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宪法是公民价值认同的体现,通过宪法适用和解释从法律逻辑的角度减少政治对抗产生的震荡,并在宪法层面逐渐形成政治共识,必将有助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推进。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宪法解释提请权的行使,可以将部分政治争议吸纳到宪法争议中处理,从而将特别行政区治理模式由单一的基本法治理向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治理转型。
注释:
① 由于港澳特别行政区制度构造具有高度相似性,本文的论述主要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基本宪法原理阐发应同样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
② 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效力与适用问题为基本法学界的长期难点问题,据邹平学教授的梳理,相关学说达13种之多。参见邹平学、黎沛文、张晋邦:《我国基本法研究30年综述》,载《中国宪法学三十年》,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311页。
③ 香港基本法第11条第1款规定,香港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均以本法规定为依据,这在法律上保障了“一国两制”方针所要求的香港本地制度、政策的自足性、独特性与稳定性。因此,这一条款可称为“基本法的自足性条款”。这一条款从宪法第31条延伸而来,所以具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作用。在司法层面,香港法院有权根据这一条款化解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基本法的自足性”。参见黄明涛:《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11条第1款的一种解读》,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
④ 有关基本法内在隐藏的逻辑裂隙的提法,可参见陈端洪教授的有关论述。陈端洪教授认为,基本法隐含着两大逻辑裂隙,“一是关于1842—1997年之间香港主权状况的宏大叙事与实际策略之间的裂隙;二是香港高度自治与宪法和主权的普遍性、统一性之间的裂隙”。参见陈端洪:《主权政治与政治主权:香港基本法对主权理论的应用与突破》,载陈端洪:《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⑤ 田飞龙认为,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澄清了香港法治社会的完整宪制基础,即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的宪制基础,也就是“共同基础论”。参见田飞龙:《‘共同基础’夯实‘一国两制’宪法保障》,载2014年6月12日《法治周末》。
⑥ 回归后香港各级法院至少在37份判决书中引用了中国宪法,从其时间跨度和影响力来看,几乎覆盖了香港回归以来所有引发学术争议的判决。这其中存在着在特定案件和特定问题上实质性适用中国宪法作为案件裁判依据的情形,但香港法院未在宪法审查的典型形态上适用过中国宪法,相较而言香港法院以基本法为依据进行司法审查的案件则十分常见。参见王振民、孙成:《香港法院适用中国宪法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
⑦ 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通过答复询问的方式阐释宪法条文的具体含义,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宪法第37条之解释》,参见周伟:《宪法解释方法与案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⑧ 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职权主要由全国人大举行全体会议时行使。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9条和第10条的规定,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个代表团或三十名以上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其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因此全国人大的宪法审查职权主要以立法议案的形式提出,根据立法程序处理,提请主体同样不包含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故本文不进行讨论。
⑨ 相关论述可参见许崇德主编:《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肖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年第3期;刘茂林:《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载《法学家》2007年第3期;孙涉:《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载《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陈玉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上) 》,载《政法论坛》1990年第3 期。
⑩ 如法国宪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各项法律在颁布前应由共和国总统、内阁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或由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60名参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参见郑磊:《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223页。又如德国基本法第93条第1项第2款规定,联邦法律、州法律与基本法,或者州法律与其他联邦法律在形式或者实质上存在抵触的歧见或者疑义时,联邦政府、州政府或者1/4的联邦议员可向宪法法院提出宪法审查的申请。参见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198页。再如波兰共和国宪法第191条规定,总统、参众两院议长、总理、五十名众议员、三十名参议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总检察长、最高监察院院长、公民权利保障专员可以就法律和国际协议的合宪性提请宪法法院裁决。参见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165页。
[1] 陈友清. 论一国两制法学及其形成和发展[J]. 中国法学, 2006(2): 50−67.
[2] 邹平学, 张晋邦, 李岳峰. 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回顾与前瞻——基本法实施中的青年、媒体、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3(4): 20−28+125−126.
[3] 刘茂林. 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J]. 法学家, 2007(3): 14−17+1.
[4] 邹平学. 全面认识基本法的五大特性[N]. 大公报, 2015-3-29(05).
[5] 马新福.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个理论问题[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4): 7−10.
[6] 朱国斌. 坚持依法治港·巩固一国两制[N]. 大公报, 2015-3-23 (A12).
[7] 肖蔚云. 论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的保障[J]. 中外法学, 1999(2): 1−6.
[8] 张定淮, 涂春光. 论邓小平关于香港特区治理方式的设想[J].社会主义研究, 2006(3): 24−26.
[9] 曹旭东. 博弈、挣脱与民意——从“双非”风波回望“庄丰源案”[J]. 政治与法律, 2012(6): 17−25.
[10] 邹平学. 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研究的若干思考[J]. 政法论丛, 2010(6): 13−21.
[11] 邹平学, 等. 香港基本法实践问题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2] 程洁. 中央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以基本法规定的授权关系为框架[J]. 法学, 2007(8): 61−68.
[13] 王振民. 论港澳回归后新宪法秩序的确立[J]. 港澳研究, 2013(1): 28−36+94.
[14] 周叶中, 刘文戈.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7(6): 49−54.
[15] 周叶中. 宪法对治理现代化的作用[N]. 法制日报, 2016-3-2(007).
[16] 殷啸虎. 论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J]. 法学, 2010(1): 49−56.
[17] 叶海波.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合宪性推定[J]. 清华法学, 2012, 6(5): 91−100.
[18] 李琦.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 宪法的特别法[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5): 15−23.
[19] 郑贤君. 宪法解释: 监督宪法实施之匙[J]. 人民法治, 2015(Z1): 24−26.
[20] 邹平学. 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效力和适用研究述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0(5): 58−65.
[21] 张小帅. 论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区的实施——基于对《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的分析[J]. 港澳研究, 2015(3): 34−43+94−95.
[22] 马正楠. 论全国性法律在香港适用的权力冲突——以香港“侮辱国旗案”为例[J]. 法律适用, 2012(11): 95−101.
The legal basis and practical motivation of the power of SAR to submit the proposal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ZHU Fuhui, ZHANG Jinbang
(School of Law,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Bo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stitute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SAR. Practice has proven that without the sufficient appl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Basic Law of SAR in Hong Kong can not suffice for the SAR’s governance. So, the governance of SAR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the governance of the Basic Law to the co-governance of bo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SAR mainly involves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Neither the Constitution nor the Basic Law specifically stipulates on what conditions the state organs of SAR are entitled to submit the proposal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Nor has legal legislation made any stipulations on the censorship claim of the state organs of SAR. As a matter of fact, failure to extend the correct treatment with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SAR is harmful not only to the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SAR, but also to the governance of both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SAR government in applying the Constitution. Therefore, the adoption of the state organs of SAR to submit the proposal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a procedural power,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principle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our country. By executing the power of submitting the proposal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some urgent issues in legal practice of SAR can be solved by the state organs of the SAR so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Basic Law of SAR and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an be maintained.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submitting power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2018−02−06;
2018−04−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机关宪法解释提请权研究”(15BFX038)
朱福惠(1961—),男,湖南双峰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司法制度、公法原理;张晋邦 (1990—),男,湖南沅陵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检察制度、港澳基本法、经济公法,联系邮箱:lonelypalmer@qq.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5.007
D921.9
A
1672-3104(2018)05−0047−11
[编辑: 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