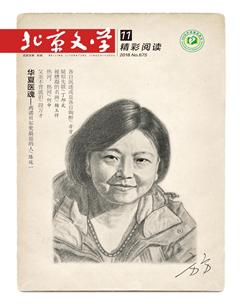漂的五味
张雄文
多年后,我常常翘首北望,无限感慨。心想,若无那一年北漂的滋味,我或许还是南方小城那只温水里的青蛙,至今寥落无成吧?
这是2006年8月下旬北京最早的一波秋风,凌厉而不失柔软,裹着些许临近草原上胡马的气息,远不如后来能吹转身躯的犀利北风,对北京人而言再正常不过;于刚办好离职手续、打算投奔北京边读书边找工作改变命运的我却是一个不小的下马威,将心内深处原本积蓄已久的忐忑倏忽间催迫而出,如潮似浪,不可遏止。
平静下来时已在知春路上大运村学生公寓的1501室。得到早已联系过的一位老乡襄助,我交了一沓相伴千里攥出汗渍的钞票,住进了这8人同室的房间。公寓由私人出资筹建并管理,所需费用不菲,住的多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后来才知,与诸多瑟缩在简陋而阴暗地下室的北漂者比,我已算是“漂”在天堂了。
有了可长住的窝,吃的问题立马被痉挛的胃一阵阵催逼着。大运村的地下室被辟作了食堂,归私人承包。下楼转了一圈,发现没有三块五以下的菜,加上米饭,一餐需四块五。我勉强吃了一次,菜里没几星油,葱蒜作料也近乎绝迹,像某个寺庙粗糙的斋饭。同室的人又告诫我,这里饭菜比北师大、北航贵了一倍,且很不卫生,此后便很少来了。
北师大和北航的食堂也去过。第一次去北航,看到菜盆里一道辣子鸡,鲜红的干辣椒比南方火锅城龙虾里的还多,分外亲切,便点了这道菜,外加一份包菜炒肉及二两米饭,共五块五。果然便宜,在北师大点两份菜要七八块。不过吃起来,包菜炒肉有浓浓的醋味,令我有吐的感觉,因此没再动筷。辣子鸡里的干椒则是整个儿的,而鸡块又炸得焦干,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北师大的食堂,我办了张餐卡,因非正式录取的学生,需加收15%的额外费用,倒是可以不限量免费领取稀饭,色泽橙黄,浓香扑鼻,味道还不错。
吃得最多的还是大运村附近的一家“老马拉面馆”,一份现做的拉面只要4元。热腾腾的汤里,面条浑圆、夯实、筋道,铺几片牛肉,撒上些葱花,白、褐、绿相间,朴素而淡雅,像乡间水之湄端坐的娴静女子。桌上的辣椒油随便倒,我一般要舀五六调羹,汤水瞬间像滑过一轮夕阳的天空,霞光烂漫,红艳夺目。朔风刺骨的冬天到来后,拉面不只让我饱肚,还驱逐了满身寒意。因为常来,店里的伙计熟悉了我,称我为“南方的朋友”。我一拉开玻璃门,他便立马朝里头朗声吆喝:“小碗拉面”,十分灵泛,我常是无声地笑了。
自然偶尔也换换口味,算作“打牙祭”。一次上课回来,穿过蓟门里北区,碰巧刚开了家饭馆,门两旁的对联有点意思,十余年后记忆犹新:“面能饱肚快进来吃几碗;酒能解乏请上座喝几杯。”横批是“民以食为天”。我决定进去吃碗馄饨。馄饨上来后,香菜、虾米、紫菜都有一点,我又加了些辣椒酱,尝一口,很是鲜美。边吃边看街边大妈、大嫂不时进出买油饼、鸡蛋和包子,感觉自己是地道的北京人了。
我选择在北师大做研修生。住所到新街口外大街的北师大校园,可坐颐和园至肖村的826路,但车次既少,绝大部分又多是票价两元的空调车。另一趟经过北师大的304路车只要一块钱,间隔时间却更长,10天内只碰到过一回。一次为了省一块钱,我等了非空调的304路40分钟,最终失望,只得垂着酸疼的脖子上了空调车。车上却没开空调,有乘客愤然质疑,售票员蛮横地说:“起步价两块。”她的胖脸抖动时,我正在看车上张贴的一张北京市政府告示,落款是“市长 王岐山”。不想多年后,王市长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铁面包公”。
日子一久,我开始步行去上课。一是可以避免等车耽误时间,影响心情;二是省去了车费,长年下来,也不是小数目;三是最重要的,锻炼了身体。第一次带我走的是同室黄同学,他在林立楼宇间探索出了一条距离最短的小路。此前,我仅知道两条可供选的大路。他带我从北京体育学院北校区围墙边进入小胡同后,时而社区,时而街道;又过两所仅一墙之隔的中学,一为蓟门里中学,一为学院路中学;之后踏上三环路,沿环线往东,经过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聚集了一些人。黄同学说,他们都是来等电影角色的群众演员。若非他及时介绍,我会以为是为讨薪而集体堵门的下岗工人。他们似乎灰头土脸,衣衫脏乱,或站或蹲或坐。在靠近三环的马路边,一些人还在一床脏兮兮的被子上呼呼大睡,旁边即是呼啸而过的车流。同病相怜,我瞬间对他们肃然起敬。或许,那些已成功的名角里,就有人曾这样睡过;在以后某部当红影片中,也或许就有眼前某些人的镜头。
为了省钱,多年烟龄的我将牌子改为两元一包的双叶。一次在与大运村隔街的便利店里买了一包,回来发现是假的。一根烟两旁的烟丝燃了半截,中间的才刚开始着,总不透气。正宗的双叶有股淡淡清香,这一包则苦涩刺鼻,于是回去找老板。老板接过去点燃一根,悠然吐着烟圈,说,味道很好啊。一旁的老板娘忽然指着我带来的真烟盒,恶声恶气说:“你拿的才是假的!”我一时无语,只得默然走了。
上课之余,也试图找个能拿钱的事做。那时的《新京报》等纸媒还颇红火,每个早晨,知春路公交站都会遇到一个中年妇人在叫卖:“买报,买报,《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商报》……”上了车,也会有夹着一沓厚报纸的人来回穿梭,嘴里不住吆喝:“哎,买报咧,看布莱尔下台了。”我是《新京报》的长年看客,主要是为了寻找些招聘信息。工作没着落,房产价格信息倒时常将我轰炸得咋舌不止,一间50来平方米的居室,竟要五六十万元。
合适我的工作还是找到了,就是熬夜写书。一个偶然机会接触了开国大将粟裕的秘书,我选定了一个主题,写一本关于粟裕的书。首先要采访。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粟裕诸多亲属、身边人和老部下都走访过。一些重要的采访对象,耽搁人家时间,我还得提上些薄礼以表歉意,至今还收藏着府右街顺天府超市的一张购物详单,单据编号:502-018-6003-17-100。有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每晚伏案写作。漂泊的五味令我的心异常坚毅,也无比沉静,像桌边一尊寂寞的雕塑,常常迎来一缕曙光探入窗棂。这部45万字的书稿,在2007年6月我决定离开北京时由人民出版社确定出版。问世后,不斷再版、加印到7万册,令我很收获了些微名。此后,我接连出版了近10部长篇,又在各级文学期刊发表了百余万字,跻身曾梦寐以求的作家行列。
多年后,我常常翘首北望,无限感慨。心想,若无那一年北漂的滋味,我或许还是南方小城那只温水里的青蛙,至今寥落无成吧?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