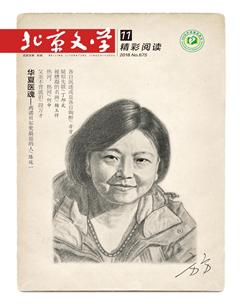狗事杂记(散文)
胡鸿
时光倒退52年。
义水河从罗田县城绕城而过,河上有唯一的一座木桥。一辆老旧的卡车吱嘎着从桥上缓缓开过,车斗里装着些旧棉被、衣物和老家具,还有我奶奶、父母和三岁的我。在车斗的最后,一只大灰狗面朝车后方,昂首肃立,静如雕塑。
大灰狗昂首静立的印象,就这样永远地镶嵌在我的记忆中。
位于大别山区的英山、罗田、浠水三县在联合修建白莲河水库,我们家老屋正在库区,作为党员的父亲响应政府的号召,举家搬迁到70里外的李蟒岩山头。从白莲河水库到县城,汽车已经颠簸了50多里路。大灰狗也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姿势,四腿直立,昂首挺胸,一动不动地望着汽车来时的方向。印在三岁孩童心中的这个印象,让我留存至今,已经大半辈子了,也让我一直在琢磨:大灰狗在往后看什么呢?他一定是想努力记住来时的路径,想着以后怎么回去吧?狗们不像人类思维多元,它们如果有思维的话,也是单线条的,执着到极端。“家”和“主人”是它们最终极的牵挂。
搬到新家后,大灰狗白天跟家人在一起,还有些安全感,但一到晚上,它就紧张起来,房前屋后巡视。一天大清早,村里人起来发现家家大门上都有血迹。好多人说昨晚听到了动物的撕咬和呻吟。
父母在家门口不远的地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大灰狗,它浑身是伤。看见主人,动都不动,只是眼睛转了一下。原来,它在晚上与来访的大野狗干上了,并最终完败给了大野狗。父母把大灰狗搬到家中堂屋的大桌子底下,让它安静地躺着。大灰狗不吃不喝,也不哼唧一声,三天之后,永远闭上了眼睛。
奶奶提议,在后山上找个干净的地方,挖个坑,把它正式埋葬。新家在山区,山里人也许从来没有见过狗死了不吃而把它埋葬的。因此埋狗的时候,聚集了众多的旁观者。我记得那时的情景,当父母给大灰狗挖坑时,充满了宗教的静穆感,这种宗教气氛在我家里一直延续了好几天,一家人都不怎么说话。
这是我们家养的第一条狗。
又过了七八年,我11岁,到了小事可以自作主张而不用看大人脸色的年纪。我就从别人家抱了一只小狗,养了起来。后来发现这是一只母狗。母狗很快长大,做了狗妈妈。结果,她一下子生了5只小狗。
小狗们一天天长大。五只小狗,一只黑色的,一只麻黄的,两只灰的,还有一只深灰色的。我个人最喜欢深灰色的那只,它的毛色其实应该在灰和黑之间,更偏向黑。深灰色小狗它不仅可爱,而且活泼,见了我总是摇着尾巴,晃晃悠悠地朝我跑来。我叫它小灰,可笑的是,我叫小灰的时候,大狗也悄悄地走了过来。小灰曾几何时也是我唤它的名字。
小狗们一天天长大,五只小动物天天围着我们哥儿几个转。我们训练它们“趴下”“立正”“稍息”,最常训练的是经常对着某个东西发出“嗖”“嗖”的短促命令,想让它们像发现野物一样勇敢地扑上去。这些狗是土狗,现在雅号叫“中华田园犬”,它们的本质基因是看家护院的,就像蒙学歌谣里唱的“犬护院、鸡司晨”。因为主人在旁,它们对我们发出的出击命令无动于衷,只是一齐抬头看着我们指的方向,这有些让我们失望。11岁也是最顽劣的年龄,我最小的弟弟也就1岁多,刚走路的样子。从知性上说,我们跟小狗们差不多一个水平,贪玩。就这样,经常是四个小子跟五只小狗滚在一起,发出各种哇哇呀呀的怪叫。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值农村闹饥荒。特别是冬春交接的日子,青黄不接。大家巴望着政府的接济。记得当时来自政府的接济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国家粮仓里调来的陈年存粮,那是不知道存放了多久的谷子,颜色已经开始变成了酱油色了。这种陈米煮粥不好吃,因为已经失去了黏性,但是煮饭是挺有风味的,特别是有锅巴的时候。但乡亲们是等这米来救命的,哪敢用来做干饭?另外一种接济是藕粉。长大到武汉读书才知道,这种藕粉出自武汉东西湖水产区。记得母亲用藕粉做饭时的情形:烧一大锅水,等水沸腾,再放上一些盐,倒入小半碗藕粉,然后不停地搅和,直到一锅水变成了稀稀的糊糊。
人都没有吃的,哪有狗的食物。
小狗们长啊长,到了“抱狗”的时候。所谓“抱狗”,就是小狗长大了,被人领养去。领养是免费的,家乡话叫作“抱”。其实,小猪长大了,也叫“抱”,但小猪是要钱的,因为那是未来的“年猪”。我们四兄弟一边等人来抱狗,一边玩着抱狗的游戏——
甲:王大娘好!
乙:好!搞么事(干什么来了)?
甲:我抱狗来了。
乙丙丁戊:早呢,还冇影呢(还早呢),小狗还没睁开眼呢。
……
甲:王大娘好!
乙:好!搞么事(干什么来了)?
甲:我抱狗来了。
乙丙丁戊:早呢,还冇影呢(还早呢),小狗还不会走路呢。
……
甲:王大娘好!
乙:好!搞么事(干什么來了)?
甲:我抱狗来了。
乙丙丁戊:早呢,还冇影呢(还早呢),小狗还没长牙呢。
……
经常是老二(现在该叫胡教授了)扮“甲”,我带着老三老四和堂妹丹桂扮狗主人,也就是乙丙丁戊。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演。
但是,人都没有饭吃,哪有余粮来养狗?“抱狗”的人一直没有来。我们天天盼着生人来,而且是来“抱狗”。看着这些可怜的“玩伴”一天比一天大,也一天比一天瘦,我心里很苦。没办法,我经常是偷偷把自己碗里的倒给小狗。
母亲不干了。“你们赶快想办法把它们扔了,抱得远远的。”
她当然心疼狗,但更心疼“我的狗”,母亲在向最小的孩子们表达亲热时,常说“我的细狗”(有时也叫“细命”)。我们哥儿几个都做过她的“细狗”,后来她还把这个称呼用在了我儿子的身上。
于是,我们开始“扔”狗。
我们把狗带到邻村,进一人家门,推荐我们的狗。“要狗吗?这狗很好啊。”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要不要”,“人都没吃的还养什么狗啊”,最好的回答是“放那儿吧”。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就兴高采烈地把狗往地上一放,就跑回家。
还没到屋呢,抱出去的小狗就已经在家门口摇着尾巴等我们了。
我们就往更远的村子走。但结果往往是一样的。
每当我疲惫地回家,看到小狗先于我到达,并且在门口摇着尾巴欢天喜地地迎接我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眼泪。就这样为狗哭了好多回。
最后扔掉的是“小灰”。那是我想了一个绝招:蒙上它的眼睛,抱着它走了20里路,在县城一个满地骨头的餐馆里,把它扔了。看着满地的骨头,我心里一阵释然,心里默念:“吃吧,这回饿不死了。”
此后,每当我路过县城中心那个热闹的餐馆,都忍不住进去看一眼,潜意识驱使我想撞见“小灰”。但是,我一次也没有看见它,它永远地消失了。再后来,县城改造,那个热闹的中心餐馆没了。再次经过,看到那些卖布卖鞋的和那些在高分贝宣传喇叭下拥挤的人群,我心里就会有空荡荡的感觉。
童年狗事,让一个顽童变得心地柔软。都到了要抱孙子的年龄了,一想起那群小狗,我就立刻变得沉静起来,心中充满了谦卑。我一直有个执念:有孩子的人家,一定要养个小动物,最好是狗。对孩子来说,狗是你的玩伴,也是你的老师,还是你的学徒。你跟它玩,你学会了游戏规则;它跟你学,它也塑造着你。
成年后,满世界地游荡,看到了许多的镜头里都有狗——
在北京顺义一个豪华别墅区的花坛边,一只大黄狗看着我和14岁的儿子,我们对大黄狗点头,狗也对我们点头。我们不动,大黄狗也不动。我们再点头,大黄狗再点头。
清晨,纽约23街联合国国际学校门口,挤满了上学的孩子和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不少孩子跟陪送的狗道别。他们摸狗的脖子、头,俯下身子,抱一抱,跟狗说“拜拜”。狗呢,很享受地用头蹭蹭小主人的腿,舔舔他们的小手。那些狗中,有普通的小狗,也有大型的圣伯纳、腊肠、德国牧羊犬、大丹、阿拉斯加雪橇犬,等。
泸沽湖边摩梭人居住的村子边,一只大黄狗平静地蹲在那里,任凭游客抚摸它,眨着眼睛,一动不动,非常友善的样子。摩梭人实行走婚制,家中老祖母掌权,孩子们只知道妈妈和舅舅,不知道爸爸是谁。因此,狗在家中就有了很重要的地位。孩子们叫狗叫“舅舅”,做了“舅舅”的狗,在摩梭人的村落中,就培养起了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不像一般的土狗,动不动就对人狂吠、龇牙咧嘴。抚摸着摩梭孩子们的“舅舅”,沐浴着高山阳光,吹拂着泸沽湖送来的温煦的春风,我体验到了人类生存空间的宽度。
美国缅因州巴克斯特山下,一条平静的小河湾处。我和夫人就在这道河湾边的草地上扎下了帐篷,安排妥当后,在露宿营区散步。一只黝黑油亮的小狗嘴里叼着一截木棍跑到我夫人面前,把木棍往地上一放,抬头望着她。见我夫人没有什么反应,就把木棍叼起来,再次往地上一放,抬头看她。我夫人怕狗,战战兢兢地问我:“它什么意思?”“它认错人了,以为你是它的主人,要跟你玩。”我说。我捡起木棍,往远处一扔,小狗噌地跳了开去,叼回那根木棍,回到我面前,我又扔了出去,它又把它捡了回来。我夫人看傻了,也学着我的样子,扔那根木棍。她跟那只漂亮的黑狗玩了好一阵子。小黑狗彻底改变了她對狗的观念。
北京朝阳区一个档次不低的居住小区里,一只狗嘶吼了一晚上。先是大声吼叫,到了最后只能发出低沉的呜咽,它在抗议:主人忽略了它,不带它出去玩。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据说,它是人类从狼驯化而来。人们把这些野性十足的动物圈到自己的社会中来,培养起它们的社会担当和约束力。人和狗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们常说,人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什么样的社会塑造什么样的人。顺着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狗是人的一面镜子,什么样的人群,就养出什么样的狗。有的狗温文尔雅,有的狗任劳任怨,有的狗凶相毕露,有的狗敏感多疑,这都是我们人类自身文明的映照和反讽。
童年的狗事,让我终生跟狗结缘,使我从狗事中抽象出这么多信条和人生的感悟。感谢大黄狗,感谢小灰。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