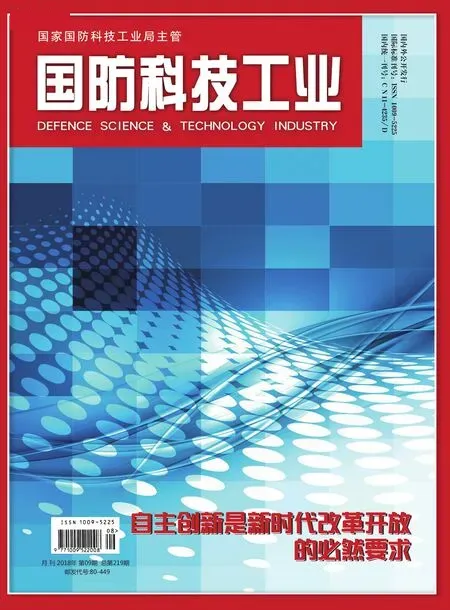军民融合是专业化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选择
王海涛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军民融合发展是我国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其根本目的是统筹配置军民两大体系资源,更大效率地实现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军民融合与社会分工有着以生产力为纽带的深层次的关系。
军与民社会内部分工的结果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论表明,社会内部分工是指国民经济分化为不同的产业部门,主要特征是新产业部门的产生。新产业部门可以是从原有部门中分离出来的,也可以由原有部门重新分化整合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与民首先就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结果。随着国防能力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防军事逐渐在农耕商业文明中分化为独立的部门,而常备军的出现则标志着国防军事作为一个专业化部门诞生。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的制造生产也从街边的铁匠铺发展到由国家专门管理的兵器作坊。专门生产武器装备的国防工业,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部门由此诞生。
四次社会大分工分别产生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服务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工的深入,新兴产业部门不断涌现。由标准普尔与摩根斯坦利于2002年推出的新版全球行业分类系统将行业进行了四级分类,包括10个经济部门、24个行业组、68个行业和154个子行业。我国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则有20个门类、97个大类、473个中类。
自国防工业成为独立的社会部门以来,随着战争形态不断演变,武器装备的种类越来越多,国防工业最终发展成为包括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在内的工业体系。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庞大的国防工业由一个部门来承载,显然是低效率的,按照不同的最终使用价值进行专业化分工再次在国防工业部门内部发生,形成了以核工业、航天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兵器工业、电子工业为主的六大产业部门。
我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正是按照这种理论思路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先后组建了第二至第八机械部服务国防建设,分别对应核、航空、电子、兵器、船舶、航天(洲际导弹)、战术导弹等工业的发展管理。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国防工业体系形成了以各行业集团公司为特征的分工形态,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部门界限。
军民融合分工深化的必然归宿
军与民、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既然已经通过社会分工分化成两个独立的部门以及多个独立的子部门,那么军民融合又从何谈起呢?实际上,军民融合正是由分工继续广化和深化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古时候,军与民的最终消费品的产品结构、生产工艺简单,生产迂回程度很低,中间品数量少、成本低,自给自足式的协调组织成本远小于市场交易成本。因此,一个生产锄头或刀枪的铁匠铺可能会自己准备所需的一切工具,如铁墩、铁锤、碳粉、烘炉等;或者,由于锄头或刀枪的市场规模还不足够大,以致专门生产铁墩、铁锤等产品无法形成产业规模。这个时期的军民融合是一种简单朴素的军民融合,体现在铁匠铺既能生产锄头又能生产刀枪。但由于刀枪的特殊性,生产刀枪是受政府严格管制的。此时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分化为独立的社会部门更多的是政府的制度性安排。而这种强制性安排在事实上也分割了铁匠铺的市场,对整个行业的进一步分工造成了影响。
在到处都闪耀着科技光芒的现代社会,军与民的最终消费品不仅种类繁多,产品结构、生产工艺更是纷繁复杂,生产迂回程度极大延伸,中间品数量成千上万,有些中间品的技术含量高、价值昂贵,甚至在最终产品中占据核心地位。据统计,一辆普通轿车由1万多个不可拆解的独立零部件组装而成,一辆坦克约有8000个零部件,而作为地球上最复杂的机械系统之一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大约有10亿个部件。而且,不同结构、不同形状、不同作用的零部件生产还需要相应的制造装备,许多制造装备的生产复杂程度不亚于一辆轿车。这些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若选择自给自足或者不够充分分工的生产方式,将会产生远高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协调组织成本,因而不可能在一家企业,甚至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完成,需要极高程度的专业化分工和国际分工协作。比如,空客有1500多家供应商,分布在27个国家,有30%的制造在美国进行;波音60%的零部件都转包给其他供应商,其中有35%的制造在日本完成;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飞机有2000多个供应商,国产率仅有50%;即便是保密程度很高的军用飞机,也有联合制造的趋势,如A400M欧洲运输机由空客军用机公司负责设计,多家欧洲著名公司参加研发工作,最后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总装厂负责总装。
当最终消费品能够以更高效率在一家企业里生产时,以企业为单元将军民品的生产分开是符合社会利益的(包括经济效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社会管理成本也能控制在较低水平。但是当最终消费品的迂回生产链条延长,专业化分工经济相对于交易成本上升,中间品的生产甚至需要以一个产业来支撑时,军民融合发展实际上成为了必然选择。
首先,尽管军与民的最终消费品的功能(使用价值)不尽相同,但由于两者的生产链条均得以延长,众多中间品中必然有部分产品相似甚至完全相同,而且这种相似程度往往随着最终产品生产链的前移而不断提高,这是军民融合发展的技术性必要条件,同时这个条件也是从古至今军民品生产所一直具备的。
其次,也是最为根本的动因,是由专业化分工引起的经济性条件的变化,即融合发展的效率逐渐高于独自发展。专业化分工使得许多中间品由一家企业甚至以其为最终产品的一条产业链生产,融合发展即是军与民的最终消费品生产单元“共享”这些中间品的生产企业或产业链,而非将所有中间品的生产都整合在以各自最终消费品划分的一个部门内,根据分工理论这显然会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随着规模的扩大、分工的深入,这种效率损失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若各自组建巨型企业,产品的复杂化必然会导致企业内部层级的不断增多和组织结构的日益复杂,进而产生巨大的协调成本,这种情况的效率损失是最大的;第二,若各自组建产业部门,以企业间分工代替企业内层级,效率会得以提升,但由于中间品产品结构、生产过程和工艺的相似性,必然会产生重复投资,相似程度越高、范围越广,由重复投资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越大;第三,若各自限定在不同区域生产,则无法利用区域间分工发挥比较优势而造成效率损失。
社会分工分化出军与民、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以及社会各行各业,也推动着组织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不断拉扯与变化。军民融合本质上是社会分工进行到一定阶段,处理军与民、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以满足整体社会效率最大化。从历史上看,军民融合不是所有经济社会环境的最优选择,而是与社会分工的历史形态相对应的。专家的研究也表明,军民融合发展是军民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分工、组织结构模式不断演进的过程,其发展路径取决于交易效率、中间品产出弹性和国防支出占比等经济技术特征。
技术性条件和经济性条件是军民融合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技术性条件是长期存在的,经济性条件是根本动因。实际上,实现军民融合发展还需满足第三个必要条件,即制度性条件,包括管理体制、发展规划、政策制度、产品标准等。当前,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早已具备了军民融合发展的经济性条件,但制度性条件还不成熟。这正是党中央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立高规格领导机构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基于进口关联化、多样化与高度化的多维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