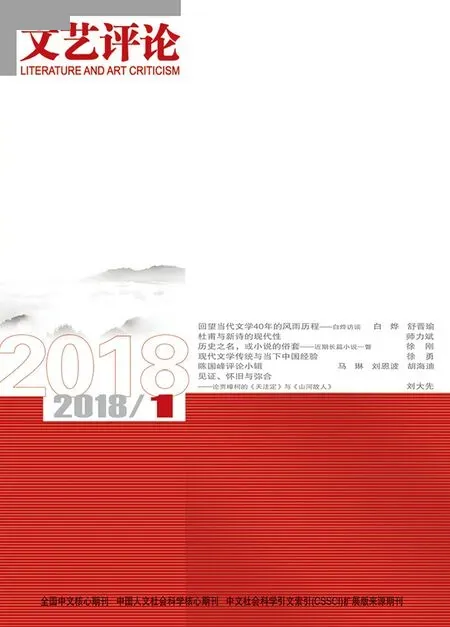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以人道主义反思战争的戏剧力作《上帝作证》
○胡海迪
看过很多抗日题材的作品,令我耳目一新而又萦绕于心的并不多,偏偏有一部尚未排演的抗日话剧,激发了我浓烈的兴致。这部剧,就是剧作家陈国峰先生的《上帝作证》。2016年10月,《陈国峰文集》出版,收录了这个剧本。我前几天再次读它,在脑海里把它演了一遍,不禁生出许多感慨。
这部戏的情节,是有些不合常格的。一般来说,抗战题材的艺术表现,在中国人这里,多年来已经形成一种以中国人为出发点的惯性思维,而且,由于这种思维,日本侵略者必然是反面人物。但是,《上帝作证》却反其道而行之:主角是个日本人,还不是一般的日本老百姓——是个日本军医,从身份上说,他是地道的日本侵略者。奇怪的是,他还是个好人——这个戏里面,他一点都不邪恶残暴。他自幼在奉天长大,有许多中国“发小”,还信仰基督教。——这真是个特别的日本人,一个亲华、不信天照大神、相信“以马内利”的日本人。他和我们印象中的“山田”“龟田”这种家伙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这就有戏了。这戏还一定是个悲剧——就像哈姆雷特的思想、性格与那说杀人就杀人的血腥时代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样,这个日本军医吉野良平,在战争中饱受内心的折磨,最后凄惨甚至诡异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一个反战的日本人,一个与整个国家、种族对抗的日本人,有现实基础吗?戏剧与所有艺术一样,虚构是它的特权,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现实根据的虚构,尤其是面对并非遥远的历史,面对两个大国之间的现实关系,凌空蹈虚将是致命的缺陷——近年来,所谓“手撕鬼子”式的“抗日神剧”一出而为天下笑,就是这个原因。从陈国锋的“作者手记”可以知道,下笔之前,他阅读了许多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对他们的心路历程有深入的了解。而据我了解,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准备和十数年的战争进程中,日本国民中一直存在着反战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步平先生,曾写过一篇长文,题目是《日本侵华时期国内的反战活动》,有非常翔实的梳理和解析。除了日本国内不从属于军部的政治派别的反战活动、知识阶层的反战舆论,有两个事件与我们讨论的这个剧本密切相关:一是侵华战争中,驻杭州的两个日本联队曾发生反战兵变,180名军人遭到残酷镇压,被处以极刑。这是比剧中吉野良平更悲壮惨烈的军队内部的反战行为。二是日本政府要求属于基督教系统的上智大学师生参拜靖国神社,受到后者的顽强抵制,双方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剧作中,少年时代的吉野良平曾向南满教区长老、基督教牧师林川喜雄提出一个“童言无忌”的问题:“叔叔,上帝和天皇谁大呀?”长大后,吉野良平一直都在恪守教义与遵从军令中挣扎,他一生的悲剧也肇始于此。看来,这种精神上的矛盾,也可以在真实的历史中找到根据和佐证。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大增,其主流文化脱亚入欧,渐渐把中国视为落后、野蛮、未开化的国家。因此,很多日本人对中国人有一种优越感。剧中的吉野良平却是一个例外,他尊重中国人,与其中很多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当然与他心中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有关,与他自幼成长于中国的经历有关。但不能不说,历史和现实中很多没有这种特别背景的日本人,也不曾视中国人为低人一等或不共戴天。辽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室已故研究员阎家仁先生在晚年的一份回忆录中写道,他少年时代在日占区的辽宁金州度过,他的初中老师名叫木村常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学生游行,木村老师顶住校方压力,未对学生在激愤情绪下的举动有任何指责,表现出一个普通日本人对非正义战争的不满和对中国人的同情;阎先生升学时,因家中资产不足,一家重点高中对是否录取他表示犹豫,木村常森先生对前来调查的教师说:“这个学生若拿不起学费,我给他负担学费!”这种正直的性格、友善的义举,虽然出自一个日本人,也是令人钦佩的。再举一个鸟居龙藏的例子。鸟居龙藏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他在北平沦陷期间受聘为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与中方师生关系很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关闭附属于美国教会的燕大,当日,鸟居先生身着和服立于校门,以日本人的身份,郑重向离校师生鞠躬致歉。有意思的是,日本战败后,燕大复校,第一笔钱就由大学者洪业亲手送到这位反对战争的鸟居教授手中——当时,他全靠典当为生,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比中国教授过得还苦,因为中国人不理他,日本人也不理他。当代著名学者胡文辉先生曾用一句诗评价他:“倭种何曾都作寇,折腰低首见斯人。”讲得公允、实在,也表达出中国人对当年日本友好人士的深深敬意。
有这样一种现实的可能,吉野良平的形象就是“可信”的,但要让这个形象变成“可感”的,还需要艺术手段的加工,就像找到了合适的大理石,还要有慧心和巧手把它变成打动人心的雕塑。《上帝作证》有七场九个场景,采用的是一种极为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吉野良平是贯穿始终的主角。从少年时代与中日几位小朋友一起打雪仗,到“九一八”事变中一位玩伴的父亲被日本侵略者枪杀,从生日时与南满教区牧师在黑云压城、临近战争的气氛中讨论基督教信仰,到他入伍后拒绝用刺刀杀害无辜中国平民而遭到毒打污辱,从他的一位热爱诗歌的日本军官朋友经历战争后神智不清、即将遭到“人道的手段处理”,到他少年的中国玩伴不再信仰“爱你的敌人”而死在另一个日本发小的枪口下,吉野良平无论外部经历还是内心世界,都承受着巨大的撕裂般的矛盾、冲突、煎熬、痛苦。剧本从开始的1923年,到结束时的1944年,是他从少年到青年的11年,这11年,是成为战争机器还是坚持宗教信仰,是捍卫国家利益还是听从良心召唤,始终是他挥之不去、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哈姆雷特反复犹豫的是复仇与否这一件事,那么吉野良平则是在层出不穷的丑恶、凶残、荒谬中挣扎;如果说哈姆雷特在精神痛苦中被动地走向死亡,吉野良平则在精神痛苦中主动地奔向毁灭。《上帝作证》的结尾意味深长、令人叹惋:吉野良平逃向日本军队占领区和中国游击队活动区之间的交界地带——枪响了,他倒下了,但不知是哪一方的子弹夺走了他的生命。
这部戏剧除了跌宕起伏的剧情,还具有一种思辨的气质。循环往复于吉野良平心头的,有许多人生的困惑。剧作家巧妙地把这些思考融入剧情,让它们自然生发,仿佛柳枝在春风春雨中摇摆着长出柳眉。“九一八”事变之前,吉野良平替吃不饱肚子的少年玩伴马海拉人力车,一个日本浪人因此打了他一记耳光,还羞辱他“给大日本帝国丢脸”,由此他向林川牧师提问:日本人歧视、欺负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有原罪?日本古时派遣唐使去中国,那时的中国人有原罪吗?在新兵训练中,他与重压在头上的集体疯狂、无理暴政辩论的方式,是他的实际行动——他拒绝杀人,即使遭到非人的待遇,也不妥协。而他心里的话,剧中“正言若反”,是新兵训练所教官毒打羞辱他时用揶揄的语气说出的。戏剧的高潮,当吉野良平的信仰世界终于在残酷的战争经历中轰然塌陷,全场回荡着他的独白:“上帝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人间的杀戮什么时候能够停止?……我的上帝啊,你究竟是在考验人类,还是早已遗弃了人类?”这种遗世独立的思考,这种择善固执的追求,深化着戏剧反战的主题,塑造了吉野良平的性格,同时,正如世界上所有优秀的悲剧一样,那被撕碎、被毁灭的东西,总是放射出奇异、美丽的光彩。
《上帝作证》的整体风格是简约的,仿佛取材于《圣经》或古希腊罗马神话的西方美术作品,历史背景点到为止,作者最用力处,是那些背负着历史重轭的活生生的人。这些人,除了主角之外,还有车夫马海、丁银匠夫妇、牧师林川喜雄、军官山本大佐等“配角”“小人物”——他们也是被战争绞肉机撕扯得血肉模糊的悲剧人物。丁银匠的太太略带喜剧色彩,就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些小老太太——她在基督受难像前烧香,画十字时的祈祷词是“阿弥陀佛!我主基督菩萨保佑!”丁银匠笃信上帝,他把守信用当作人生第一原则——结果,这个老实巴交一辈子的小手艺人,因为在“九·一八”那天晚上守约送货,竟然惨死在日本人的枪下,丁太太从此成了可怜的寡妇。马海也是一个基督徒,最初他信仰的坚定,与他的日本朋友吉野良平不相上下,“要爱你的敌人”“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这样的训导,让他隐忍,甚至能在内心中宽恕侮辱他的人。但是,到了戏剧的结尾处,他参加了游击队,他开枪,他仇恨,仇恨几乎所有的日本人,甚至包括童年时一起玩耍的日本人。在他眼里,他们“不是敌人”,而“是野兽,是十恶不赦的魔鬼”。这种变化,让人不禁心痛地暗问:可怜的孩子,这些年,你经历了什么?马海变化剧烈,与其相比,林川喜雄的变化,则缓慢悠长,却令人唏嘘。在戏剧开头,他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一个滴酒不沾、要把一切奉献给宗教事业的人,一个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人,但到戏剧结尾,他成了一个心如寒灰的人,一个不得不承认天皇大于上帝的人,一个“怀疑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听懂福音”的人。他还在吉野良平惊异的目光下“拿起酒瓶斟酒”——他已经成了一个不得不用酒精来麻醉灵魂的人。陈国峰戏剧中还塑造了一个特别的悲剧性人物——山本大佐。这个诗人气质的军官,已经在战争中变成了一个狂魔。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他神智不清,吟唱着日本的俳句,回忆在奈良招提寺樱花下读书吟诗的时光,痛苦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这些“配角”特色鲜明、令人难忘,他们的前后经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举重若轻,减笔传神,深入刻画战争的残酷、人性的脆弱,与主角的内心痛苦形成强烈的呼应。中国的叙事文学向来讲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前有铺垫,后有照映”,剧中马海由忍辱到抗争,林川由滴酒不沾到借酒浇愁,都是精到之笔,洗练有力,可见剧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但是,从整体看,这个作品的这种铺垫照应,也有稍欠火候之处。比如丁银匠一家三口,在第三场、第四场中出现,自丁银匠离世后,便再无一人上场,后来只是在他人对白中略加补叙,分明没有让某些活下来的人物有更充分的发展;山本大佐在精神错乱中吟诗的第六场,是全剧的高潮之一,但此前,只是吉野良平在第四场交待过一句“你是有文化修养的啊”,不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削弱了后面高潮部分的力量。至于另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角色,吉野良平和马海的少年玩伴桥本三郎,是最后击毙马海的人,剧作对他着力太轻,让他显得形象模糊。
“尺寸之瑕,不足以疵累白璧”,这些枝节问题,可以在未来戏剧排演之时加以解决。其实,这部戏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用人道主义思想来观照战争。这种人道主义,就是把人——包括日本人,也看作有价值、有尊严的人。战争铁蹄,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同时,很多或无知或无奈的日本人,也被卷入战争,成为可悲的牺牲品。我们不能忘记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恶,但同时,也不应受制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把所有的日本人都视为穷凶极恶之徒。吉野良平和他代表的日本反战力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如一叶小舟起伏于战争的怒海狂潮之上,时至今日,他们的立场、主张、思想、信仰,并没有因他们的失败和死亡而消逝,而是顽强地生存于广大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日本民众心中。这样的日本人,值得同情,也应当赢得尊重,不能不说,他们也是“大写的人”,配得上我们用人道主义的关怀为他们唱出一曲挽歌。
其实,在艺术表现上,把昔日敌人看作正常人、普通人的作品,《上帝作证》并不是第一部,也决不会是最后一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没有把入侵俄国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和他的元帅将军们描写成一群恶魔,在他笔下,他们具有人类共同的欲望和弱点,也是挣扎于命运漩涡中的平常人;2013年公映的俄罗斯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除了誓死保卫国土的苏联官兵,还出现了一个厌战而多情的德军军官;在美国大片《战马》中,两国交战的士兵,为挽救一匹出现在前线的战马而暂时放下武器,共同用钳子剪断它身上的铁丝网;《血战钢锯岭》中有一个同样信奉“不可以杀人”的军医道斯,他在战场上抢救美国士兵,同时,也把敌国日本的伤兵弄到他们的战地医院里。在中国,《鬼子来了》里塑造了一个有些单纯傻气的日本普通士兵,在《南京!南京!》里出现了一个放走中国人又以自杀谢罪的日本军官形象。这些作品已经展现出破除丑化模式和敌视态度的端倪,但这些昔日敌人,通常还只是配角、陪衬、补充。《上帝作证》不同,它是把昔日敌人推向了主角的位置,而且,更为不同的是,他不仅表现他们的外部生活,而且潜入他们的灵魂深处,展现他们的精神世界,显示出非凡的思想强度。
《庄子》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寓言。老聃的学生柏矩来到齐国,看到一个罪犯的尸体在刑后示众,他赶忙把尸体放下来,把自己的朝服脱下盖上去,为他保留了一个人最后的生命尊严。随后,他仰天大哭,说道:“先生啊,先生啊,天下有大患,你先遭了难!”接着,他历数主宰天下者的种种不公甚至邪恶,说他们愚蠢、歹毒、自私、不负责任,想出种种办法压迫百姓,逼着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最后他质问道:世间有这些罪恶,应当处罚的人究竟是谁呢——“于谁责而可乎?”我读这则寓言时,对庄子的逆向思维很是佩服——他没有让柏矩像许多平常人那样发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而是直接把这个非亲非故的罪犯当作一个受害者——他受到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些制度的压迫、伤害,因此,他并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普通人。庄子这种表达,当然有寓言特有的夸饰,也有他对于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的强烈批判,更有一种发自内心、令人感动的悲悯。这是庄子的可贵之处、可爱之处、可敬之处——他就是这么一个嘴冷心热的人道主义者。《上帝作证》何尝又不是如此?剧作家陈国峰把吉野良平这个表面的罪人从人生十字架下背下来,为他血迹斑斑的赤裸尸身盖上衣服。同时,他也向天大哭,用一个个人物、一串串思考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那些愚蠢、歹毒、自私、不负责任的战争发动者。这,岂不也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悲悯?
现实地说,中国所有的抗战题材的艺术作品,除了让人们牢记历史,还要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新上演。当世界上还存在着战争的阴云,还存在着用战争方式解决种种矛盾、危机的思想和人群,任何防止战争发生的努力都是值得称许的。“期于治病,不择甘苦。”陈国峰的这样一部戏剧,从一个特别的视角谴责了战争,也为清除、预防可能产生、业已存在的战争思维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艺术样本。他的这种人道主义视角,看似柔弱,实际柔韧,因为它可以潜入人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的这句话,不是可以成为陈国峰这部《上帝作证》一个最好的注解么?
——论《怀风藻》吉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