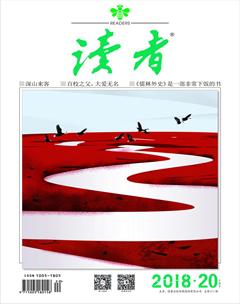写作的真相
蒋方舟
人们对于写作最大的误解,是认为写作是由灵感来支撑的。实际上,那些看似活得随意的作家都具有高度的自律性。
天才如马尔克斯,在写《百年孤独》时,依然处于非常艰难的状态。他把自己写作的房间称为“黑手党的洞穴”,大概3平方米,连接一间小浴室,一扇门和窗户通往外面的庭院,房间里有一张沙发、一个电暖炉、几个柜子、一张小而简单的桌子。
他每天一早送两个孩子上学,8点半之前就坐在书桌前,一直写作到下午两点半小孩放学回家。下午的时间则用来为小说的写作查资料。
他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短暂地见一下自己的孩子,而对孩子的态度基本也是爱答不理。孩子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俯首在满是烟雾的房间里的背影。
格雷厄姆·格林是一个生活异常丰富的作家,他当过记者,做过间谍,去过战场,和表妹徒步穿行过非洲,同有夫之妇谈恋爱,把一个人生命的容量扩展到最大。
看似不羁的格林,在创作上却努力得像是备战高考的学生。战争来临前夕,他马上要被招募,把家庭撇在身后。他当时想写的作品是一点也不挣钱的《权力与荣耀》,他知道这本书的收入无法支撑自己入伍期间的家庭支出,所以决定再写一部畅销书。
距离入伍还有6个星期的时间,他决定在下午继续艰难缓慢地创作《权力与荣耀》,而在早上写畅销书。他把工作室设在一个工厂里,这样就没有电话和孩子的干扰。
他开始吃一种叫作安非他命的中枢神经兴奋剂,连续6个星期,每天清晨服用一片,中午服用一片。因为药物作用,每天他的手都在颤抖,心情低落,会无缘无故地暴跳如雷。
他后来回忆,他和妻子的婚姻破裂,多是因为那几周服用的安非他命,而不是战争造成的分居。
如果不创作,作家可以拥有幸福平静的生活,那么作家可以选择吗?
他们可以,但是他们不能。
小说《自由》的作者乔纳森·弗兰岑,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写第二本书时,婚姻关系非常紧张,他的父母又生病,可是他每星期、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想着要如何修改小说的内容,最终导致离婚。
他说:“我明显地感觉到,如果我不再当作家,我的婚姻还能延续。不只是我的婚姻,我和父母的关系也是。每次我回老家4天,就大概有半年到8个月不會再回去,因为我必须维持自己的情绪平稳,才能继续手边的写作。我的本质就是创造冲突的根源,我就是个小说家。”
旺盛的创作状态和幸福的家庭生活无法平衡,这是从事艺术的人的宿命。是艺术之神选中你,而不是你选择服侍它。华兹华斯有句诗说:“我等诗人年轻快乐地动笔,最后的结局却是消沉和疯狂。”
比如当我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某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时,我就会去看井上雄彦的纪录片《最后的画展》。
《最后的画展》讲的是井上雄彦筹办《浪客行》画展的经历,21天要独立完成101幅画,其中有很多是巨大的展板画。井上雄彦每天从早上10点画到凌晨三四点,睡在帐篷里。在距离画展开幕只剩5天的时候,他还有30幅没画。开幕的前夜,他甚至通宵作画,最后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部画作。
这部纪录片我看了十几遍,从中获得的动力和感动丝毫没有减弱,每次我都会心潮澎湃地想:这样可怕的任务人类都可以完成,我也没什么好怕的。
特别惭愧地说,我现在真的有些懒惰了。和自己的过去相比,我真的懈怠了很多。
我最努力的时候是初中,那时候没有集中创作小说的时间,只能平常写些草稿,等暑假来完成和修改。写到凌晨3点,实在太困了,就开始做仰卧起坐来提神,每天做100个仰卧起坐,一个月就练出了一肚子肌肉。
我那时候对自己还没有总结能力,要不然我也可以像村上春树一样写一本《当我做仰卧起坐时我想些什么》。村上春树早上5点开始写作,写四五个小时,然后出门晨跑。他说:“写文章本身或许属于脑力劳动,但是要写一本完整的书,更接近体力劳动。”
的确,体力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旁人的想象。我曾经听不止一个作家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能写2000字,现在只能写500字了。”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灵感的枯竭,而是体力的衰退,导致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
但创作者锻炼身体,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说——“肉体修炼”,它的意义其实在于锻炼对自己的控制力。
必须承认的是,写作对天分的要求远远高于对汗水的要求,鼓励一个没有天分的人在写作上花一万个小时练习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秋水长天摘自中信出版社《东京一年》一书,小黑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