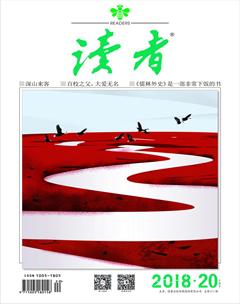孤独
李娟
大部分时候我妈独自生活。在阿克哈拉村,她的日常安保措施如下:在房子后墙上多开一个后门——一旦有坏人闯入,就从后门撤退;若坏人追了上来,就顺着预先靠在后门外的梯子爬上屋顶;若坏人也跟着爬上来,就用预先放在屋顶上的榔头敲他的头……此外,还有在椅垫下藏刀子,在门背后放石灰等很多措施——她老人家连续剧看得太多了。
她说:“能不害怕吗?就我一个人。”
说来也奇怪,像我妈这么胆小的人,到了荒野里,一个人守着一大块地,生活全面敞开,再也没有墙壁了,也没有后门、梯子和榔头……却再也不提害怕的事了。
她说:“怕什么怕?这么大的地方,就我一个人。”
真的再没有人了。在戈壁滩上,走一个小时也遇不到一个人,如同走了千百万年没遇到一个人。不但没有人,路过的帐篷或地窝子也没有炊烟,眼前的土路上也没有脚印。四面八方空空荡荡。站在大地上,仿佛千万年后独自重返地球。
关于地球的全部秘密都在风中。风声呼啸,激动又急迫。可我一句也听不懂。它拼命推我攘我,我还是什么都不明白。它转身撞向另一场大风,在我对面不远处卷起旋风,先指天,后指地。我目瞪口呆,仿佛真的离开地球太久。
风势渐渐平息。古老的地球稳稳当当悬于宇宙中央。站在地球上,像站在全世界的制高点,像垫着整颗星球探身宇宙,日月擦肩而过。地球另一侧的海洋,呼吸般一起一伏。
眼下唯一有人的痕迹的是向日葵地,幼苗横平竖直地排列着,整齐茁壮。我走进去寻找我妈,又寻找赛虎和丑丑。地球上真的只剩我一人。
我回到家,绕着蒙古包走一圈。突然看到一只鸡在附近的土堆旁踱步,并偏头看我,我这才暗舒一口气。
我妈说:“我有时候想唱歌,却一首也想不起来。有时候突然想起來了,就赶紧唱。有时候给赛虎唱,有时候给兔子唱。”
赛虎静静地听,卧在她脚边抬头看她,眼睛美丽明亮,流转万千语言。兔子却心不在焉,跳跳走走,三瓣嘴不停蠕动。
兔子尾随她走向葵花地深处。道路更窄,兔子的视野更窄。世界再大,在兔子那里也只剩一条深不见底的洞穴。而我妈高高在上,引领兔子走在幽深曲折的洞穴世界里。我妈不唱歌的时候,洞穴前不见头,后不见底;我妈唱歌的时候,洞穴全部消失,兔子第一次看到天空和海洋。
劳动纯洁而寂静。我妈心里惦记着该锄草的那块地,惦记着几天后的灌溉,惦记着还没买到的化肥。所有这些将她的荒野生活填得满满当当。她扛着铁锨从地东头走到地西头,心里一件一件盘算。突然一抬头,看到了世上最美丽的一朵云。她满满当当的荒野生活瞬间裂开,露出巨大的空白。她一时间激动又茫然。她想向世上所有人倾诉这朵云的美丽。她想:在倾诉之前,得先想好该怎么说。于是她就站在那里想啊,想啊。云慢慢变化,渐渐平凡,她心中的措辞却愈加华美。她又想唱歌,仍旧想不起一首。这时她发现兔子不见了。她想,兔子和云之间肯定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至少它们都是白的。
赛虎也是白的,但它是不安之白,退避之白。它有无限心事。它总是不被允许进入葵花地。因为它的腿受过重伤,我妈不忍心它走动太多。她对它说:“不许跟着我,就在这里自己玩。我一会儿就回来接你。”它似乎听懂了,原地卧下。我妈边走边回头望。它一动不动地凝视她,乖巧得近乎悲哀。它是黑暗之白,破碎之白。我妈无数次离它远去,也无数次转身重新走向它,抱起它,一同深入葵花地深处。
我做好了饭,在蒙古包里等我妈回家。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哪怕睡着了,我也能清晰感觉到置身睡眠中的自己是何等微弱渺小。
我在梦中起身,推开门,走向远处的葵花地,走了千百万年也没能抵达。千百万年后我独自醒来。饭菜凉了,我妈仍然没有回家。
吃饭的时候我妈再一次称赞:“这里真好!一个人也没有!”
我说:“那出门干吗还锁门?”
她语塞三秒钟,说:“关你屁事。”
(田宇轩摘自花城出版社《遥远的向日葵地》一书,全景视觉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