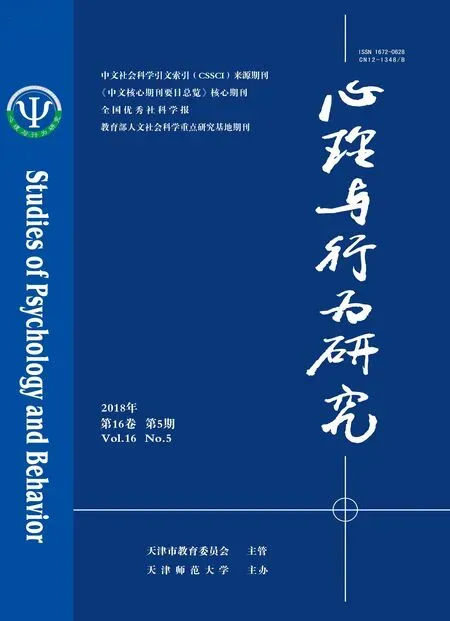厌恶与恐惧情绪习得的性别差异研究:一项ERP研究 *
曾 庆 郑希付
(1 暨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广州 510632) (2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州 510631)
1 引言
情绪反应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是情绪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问题。不同群体流行病调查结果表明,男、女性在某些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发病率与患病风险方面存在差别(Klose & Jacobi, 2004),女性患上抑郁症与焦虑症的风险更高(Bao & Swaab,2011),女性终身患抑郁症的几率约为男性的两倍(Karger, 2014)。并且研究一致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情绪化(Plant, Hyde, Keltner, & Devine, 2000;Šolcová & Lačev, 2017),女性对威胁或伤害性刺激等不愉快事件反应更强烈(Reyes-Aguilar &Barrios, 2016)。
研究者使用不同研究技术进行了大量关于男女性在负性情绪上的差异研究。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负性情绪体验量表上的得分高于男性(Grimshaw, Bulman-Fleming, & Ngo, 2004),女性对不同效价情绪刺激的反应,如对哭与笑的行为反应均比男性更为强烈(Vigil, 2009)。使用脑成像技术研究发现,虽然男女性对负性图片刺激的效价或唤醒度的主观评定无显著差异,但面对负性及中性图片刺激时,女性在杏仁核、右额中叶、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左中颞回的活动比男性更强(Domes et al., 2010)。
同时研究表明对正性和负性情绪,女性比男性的体验更多,而男女性最大的差异则体现在如恐惧和嫉妒等一些更为具体的负性情绪上(Whittle, Yücel, Yap, & Allen, 2011),如研究注视负性人际关系词语(Shirao, Okamoto, Okada, Ueda, &Yamawaki, 2005)、厌恶面部表情(Aleman &Swart, 2008)、生气面孔刺激(Sacher, Neumann,Okon-Singer, Gotowiec, & Villringer, 2013)和恐惧面孔刺激(Williams et al., 2005)时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女性在皮层下、脑边缘和前额区的活动更强。对厌恶刺激的反应中,Caseras等(2007)发现女性在左腹侧额叶的活动比男性强烈(Caseras et al.,2007)。在面对恐惧面孔刺激时,Schneider等(2011)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反应初期左杏仁核的活动更强;而稍后则是在右杏仁核的活动更强(Schneider et al., 2011)。从持久性来看,Williams等(2005)发现对恐惧刺激的反应中,女性杏仁核始终有持续不断的活动且有更强烈的皮肤电传导,而男性此区域的活动却快速变弱(Williams et al., 2005)。Andreano, Dickerson 和 Barrett(2014)也发现女性杏仁核对熟悉的负性刺激反应持续更长(Andreano et al., 2014)。
事件相关电位研究发现,不论是情绪还是中性面孔刺激,女性在N170成分波幅比男性更大(Choi et al., 2015)。当控制负性情绪刺激的强度后,Li, Yuan和Lin(2008)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脑电N2与P3b成分波幅均增大,表明高负性情绪刺激均能够唤醒明显的情绪反应,然而当面对强度较小的情绪刺激时,只有女性仍表现出较强的大脑活动状态(Li et al., 2008)。相应地,Campanella等人(2004)通过oddball范式任务,研究被试在标准中性表情面孔中找恐惧和高兴表情面孔,发现与高兴表情相比,在面对恐惧表情刺激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N2与P3b成分脑波均更大,但男性在处理高兴表情刺激时比女性显著慢(Campanella et al., 2004)。Lithari等人(2010)的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在面对引起情绪不适或高唤醒度的刺激时,脑电N2与P3会产生更强的负成分(Lithari et al., 2010),当对恐惧面孔的阈下反应中,女性P100成分波幅显著大于男性(Lee, Kim, Shim, & Lee, 2017)。
情绪过程相关神经活动的时间进程可能存在性别差异(Whittle et al., 2011)。绝大多数基于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都将焦点放在威胁或伤害刺激下的情绪反应,而忽视了中性刺激下的情绪习得反应(Olatunji, Cisler, Meunier, Connolly, & Lohr,2008),但在临床实践中,多数恐惧症或强迫症患者所恐惧的刺激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危险,均为生活中习得的对一般刺激的不寻常反应,所以本研究的焦点在于研究厌恶与恐惧情绪习得过程中时间进程的性别差异。事件相关技术(ERP)研究表明,男女性对高负性情绪刺激均敏感,女性对正性情绪刺激和低负性情绪刺激比男性更为敏感,这可能是决定女性在情绪判定中所具优势的重要机制(Campanella et al., 2004; Li et al., 2008)。因此,我们假设在厌恶与恐惧情绪习得的早期阶段,由于均是负性情绪的习得,男女性均较敏感,所以性别差异不显著。但到了中晚期,女性对负性刺激的高敏感性则突显出来,即女性在N2成分上,三类情绪刺激的习得差异均显著;但男性则仅在条件性厌恶的习得上与条件性中性刺激差异显著。
2 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36名(其中, 男生18名),年龄范围为19–25岁,平均年龄为22.1岁。采用状态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厌恶敏感性量表对被试进行筛查,结果1名男性被试因为抑郁量表超出常模平均值2.5个标准而被剔除。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或者色弱,并且均无神经系统疾病或者精神病史。被试均采用自主报名的方式参与实验,均为首次参加此类实验。在开始实验前,告知被试,在实验中可能包括一些不舒服的图片,他们可以随时终止实验,并且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不良影响。所有被试在实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后给予50元人民币作为实验报酬。
2.2 实验材料
条件性刺激:三个几何图形,分别为正方形、圆形和多边形(Zeng et al., 2015)。
非条件性刺激:选用曾庆等人(曾庆, 郑希付,2016)评定过的实验材料,共135张图片,图片大小为137×104cm,像素为640×480。其中厌恶图片45张,恐惧图片45张,中性图片45张。三类图片的效价差异显著,F(2, 118)=671.28,p<0.001,恐惧(2.40±0.36)与厌恶图片(2.31±0.41)的效价差异不显著,但均比中性图片(5.22±0.60)的效价显著负性。三类图片的唤醒度差异显著,F(2,118)=184.11,p<0.001,恐惧(5.98±1.22 6)与厌恶图片(6.15±1.29)的唤醒度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中性图片(3.26±1.42)唤醒度。三类图片进行厌恶度与恐惧度检验,结果表明厌恶图片(6.60±0.99)引发的厌恶度显著高于恐惧度(4.8 4±1.3 4);恐惧图片引发的恐惧度(6.06±0.94)显著高于厌恶度(5.51±1.11);中性图片引发的恐惧和厌恶程度都显著低于恐惧图片和厌恶图片(ps<0.001),并且无显著差异。
2.3 实验程序
把被试带入相对安静和昏暗的实验室。为了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首先进行9个试次的练习,然后进行正式实验。正式实验时,每进行100个试次之后,被试都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
使用的电脑为17英寸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分辨率为800×600像素,刷新率为100 Hz。被试与电脑显示器之间的距离约为100 cm,被试进入实验室后,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坐好。在正式实验之前,告知被试,稍后在电脑屏幕上会呈现一系列的几何图形和图片,在实验过程中,被试的主要任务是认真看屏幕,并且注意几何图形和图片之间的关系,在实验结束前要进行测试。同时,为了确认被试是否真正习得各类关系,在实验开始前和开始后,各进行一次条件性刺激的效价、唤醒度、恐惧程度和厌恶程度评定。在实验中,几何图形与图片之间的关系在被试间进行平衡。
条件化程序:首先在屏幕中间呈现红色“+”注视点500 ms,提示被试开始注视屏幕,然后呈现持续时间为600–1000 ms的黑色空屏。接着在屏幕中央呈现条件刺激(方形、圆形或者多边形)1000 ms,后面跟随非条件刺激(恐惧、厌恶或者中性图片),呈现时间为1000 ms,最后再是500 ms的黑色空屏结束一个试次。实验采用E-prime进行编程,共分为2个block,每个block共有135个试次,其中每类各45个试次(如圆形-恐惧图片45试次, 多边形-厌恶图片45试次, 方形-中性图片45试次),每个试次随机呈现。
2.4 脑电记录
采用Brain Product(BP)脑电记录与分析系统,按国际10-20系统扩展的64导电极帽记录EEG,由于有3个电极损坏,实际记录59个电极数据。脑电记录时各电极参考于左侧乳突,离线分析时通过对右侧乳突再参考,实现以右侧乳突和左侧乳突的平均值参考。前额中央接地。垂直眼电(VEOG)电极分别安放在左眼的上下1.5 cm处。水平眼电(HEOG)电极分别置于左右眼外眦。所有电极阻抗降到5 kΩ。记录采用的滤波宽带为0.01~100 Hz。脑电与眼电均采用500 Hz采样频率连续采样。离线分析的数字滤波为低通30 Hz(24 dB/octave),自动矫正眼动伪迹,波幅大于±100 μV的试次被视为伪迹剔除,所得ERP波形经0.1~30 Hz的无相数字滤波。对几何图形呈现的脑电活动进行叠加平均,实验中每个被试获得3种脑电,分别为后面跟随恐惧图片的条件性刺激(简称CSf),后面跟随厌恶图片的条件性刺激(简称CSd),后面跟随中性图片的条件性刺激(简称CSn),脑电分析时程为1200 ms,基线为条件刺激呈现前200 ms。
2.5 脑电数据分析
选择每种条件下的有效试次均大于等于40个的数据进行叠加,平均女性每个条件选取82.3个试次,男性每个条件选取81.8个试次,选取试次男女无显著差异。根据已有相关研究结果及本研究的目的,对N1(时间窗口为100–160 ms)、P2(时间窗口为170–230 ms)、N2(时间窗口为260–340 ms)、P3(时间窗口为 350–420 ms)四个成分的平均波幅进行处理和分析。研究发现,N1及N2成分主要出现在前额及中央区,因而选取选取该区域21个电极点分半球位置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左侧的9个电极点为F5, F3, F1, FC5, FC3,FC1, C5, C3, C1,中间位置的3个电极点为FZ,FCZ和CZ, 右侧的9个电极点为F6, F4, F2, FC6,FC4, FC2, C6, C4, C2。对于P2成分,主要对顶枕区附近的 12电极点进行分析,其中左侧顶枕区的6的电极点为P7, P5, P3, P1, PO3, PO7,右侧包括对应的P8, P6, P4, P2, PO4, P08 6个电极点。最后,对于P3成分, 主要分析右侧顶枕区的7个电极点,即O2, PO4, PO8, P2, P4, P6和P8。所有分析均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采用Greenhouse-Geisser方法校正方差分析的p值和自由度。
3 结果
3.1 行为结果
习惯化阶段、习得阶段分别统计,从效价、唤醒度、厌恶度与恐惧度四个维度进行3(CS刺激类型: CSd、CSf、CSn)×2(性别: 男、女)重复测量方差分析,CS刺激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性别为被试间变量。
习惯化阶段:效价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2, 66)=1.36, p=0.263,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 33)=0.23, p=0.636,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0.28, p=0.760。唤醒度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2, 66)=0.60,p =0.549,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 33)=0.18,p=0.673,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0.87, p =0.424。恐惧度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2, 66)=1.22, p=0.301,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 33)=1.43, p=0.240,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1.22, p=0.302。厌恶度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2, 66)=1.04,p=0.356,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 33)=0.44,p=0.5 1 3,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66)=0.73, p=0.478。结果表明,在条件化阶段之前,刺激类型的各个维度均差异不显著,男女性别亦差异不显著。
习得阶段:效价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差异显著,F(2, 66)=15.75, p<0.001,CSf(3.95±0.31)和CSd(3.58±0.36)的效价显著低于CSn(6.01±0.34),且CSf与CSd效价差异不显著。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 33)=2.47,p=0.126,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0.67,p=0.514。唤醒度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6)=30.47,p<0.001,CSf(6.06±0.30)和 CSd(6.12±0.27)的唤醒度显著高于CSn(3.06±0.32),且CSf与CSd唤醒度差异不显著。性别主效应显著,F(1,33)=12.45, p=0.001,女性的唤醒度(5.59±0.20)显著高于男性(4.57±0.21),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1.62,p=0.205。恐惧度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6)=84.83,p<0 .001,CSf(6.39±0.19)的恐惧度显著高于 CSd(3.09±0.42),且CSd的恐惧度显著高于CSn(1.28±0.14)。性别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1, 33)=0.23,习得阶段:效价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差异显著,F(2, 66)=15.75, p<0.001,CSf(3.95±0.31)和CSd(3.58±0.36)的效价显著低于CSn(M=6.01±0.34),且CSf与CSd效价差异不显著。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 33)=2.47,p=0.126,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0.67,p=0.514。唤醒度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6)=30.47, p<0 .001,CSf(6.06±0.30)和CSd(6.12±0.27)的唤醒度显著高于CSn(3.06±0.32),且CSf与CSd唤醒度差异不显著。性别主效应显著,F(1, 33)=12.45, p=0.001,女性的唤醒度(5.59±0.20)显著高于男性(4.57±0.21),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1.62,p=0.205。恐惧度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6)=84.83,p<0 .001,CSf(6.39±0.19)的恐惧度显著高于CSd(3.09±0.42),且CSd的恐惧度显著高于CSn(1.28±0.14)。性别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1,33)=0.23,p =0.64,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0.49, p=0.619。厌恶度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6)=38.69, p<0.001,CSd(6.17±0.30)的厌恶度显著高于 CSf(4.14±0.49),且CSd的厌恶度显著高于CSn(1.86±0.25)。性别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1, 33)=0.116,p=0.735,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66)=0.21, p=0.813。结果表明,被试成功地习得了3类几何图形与图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被试成功地习得了条件性恐惧与条件性厌恶。p =0.64,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0.49, p=0.619。厌恶度维度,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6)=38.69, p<0.001,CSd(6.17±0.30)的厌恶度显著高于CSf(4.14±0.49),且CSd的厌恶度显著高于CSn(1.86±0.25)。性别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1,33)=0.116,p=0.735,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6)=0.21, p=0.813。结果表明,被试成功地习得了3类几何图形与图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被试成功地习得了条件性恐惧与条件性厌恶。
3.2 ERP结果
N1:对习得的不同情绪CS图片诱发的N1波幅在100-160 ms时间窗的平均波幅进行3(位置:左、中、右)×3(CS类型: CSd、CSf、CSn)×2(性别: 男/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电极位置和CS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性别为被试间变量,将同一时间窗内各半球位置所包含的所有电极的平均波幅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因变量。结果表明,CS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6)=3.78,p=0.037,η2=0.10,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CSn诱发的N1(–1.62±0.28 μV)成分的波幅显著小于CSd(–2.23±0.26 μV)和 CSf(–2.14±0.28 μV),但CSd和CSf诱发的N1成分波幅无显著差异。电极位置主效应显著,F(2, 66)=3.56,p=0.034,η2=0.10,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左侧电极位置(–1.8 5±0.2 8 μ V)和右侧电极位置诱发的N1(–1.85±0.28 μV)成分的波幅均与中线位置诱发的N1(–2.17±0.27 μV)成分的波幅差异显著,但左右侧电极位置之间的N1成分波幅无显著差异。除此之外,在N1成分中没有其它主效应或者交互显著,ps>0.10。
P2:对习得的不同情绪CS图片诱发的P2波幅在170–230 ms时间窗的平均波幅进行2(位置:左、右)×3(CS 类型:CSd、CSf、CSn)×2(性别: 男/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电极位置和CS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性别为被试间变量。结果表明,CS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6)=13.81,p<0.001,η2=0.30,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CSn诱发的P2(3.93±0.47 μV)成分的波幅显著大于CSd(2.77±0.42 μV)和 CSf(2.57±0.38 μV),但CSd和CSf诱发的P2成分波幅无显著差异。 除此之外,在P2成分中没有其它主效应或者交互显著,ps>0.10。
N2:对习得的不同情绪CS图片诱发的N2波幅在220–280 ms时间窗的平均波幅进行3(位置:左、中、右)×3(CS 类型: CSd、CSf、CSn)×2(性别: 男/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电极位置和CS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性别为被试间变量。结果表明,性别主效应显著,F(1, 33)=5.76, p=0.022,η2=0.15,女性诱发的 N2(–0.80±0.36 μV)成分的波幅显著大于男性(0.44±0.37 μV)。CS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6)=9.64, p<0.001, η2=0.23,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CSd(–0.77±0.27 μV)诱发的 N2成分的波幅显著大于CSf(–0.03±0.28 μV)和 CSn(0.26±0.32 μV),p=0.005,但 CSf与CSn诱发的N2成分波幅无显著差异。同时,左右位置主效应显著,F(2, 66)=13.77, p<0.001,η2=0.29,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中线位置(–0.62±0.30 μV)的波幅显著大于右侧(–0.05±0.24 μV)和左侧(0.12±0.28 μV)波幅,ps<0.001,但右侧与左侧波幅差异无显著差异。CS类型与性别交互作用显著,F(2, 66)=4.29, p=0.018, η2=0.12,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于男性,仅CSd(0.11±0.39 μV)与 CSn(1.03±0.47 μV)诱发的N2(0.11±0.38 μV)成分的波幅差异边缘显著,p=0.056;但对于女性,CSd(–1.66±0.38 μV)诱发的 N2成分的波幅显著大于CSf(–0.25±0.39 μV)和 CSn(0.50±0.46 μV),ps<0.009。CS 类型与左右位置交互作用显著,F(4, 132)=4.86, p=0.001,η2=0.13,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电极左侧位置,CS类型差异显著,F(2, 68)=6.07,p=0.005, η2=0.15,CSd(–0.40±0.33 μV)诱发的N2成分的波幅显著大于CSf(0.23±0.32 μV),也显著大于 CSn(0.49±0.34 μV),CSf与 CSn 诱发的N2成分波幅无显著差异。在电极右侧位置,CS类型差异显著,F(2, 68)=11.70, p<0.001,η2=0.26,CSd(–0.67±0.27 μV)诱发的 N2 成分的波幅显著大于CSf(0.04±0.23 μV),也显著大于CSn(0.45±0.34μV),CSf与 CSn诱发的 N2成分波幅无显著差异。在电极中线位置,CS类型差异显著,F(2, 68)=9.12, p<0.001, η2=0.21,CSd(–1.33±0.36 μV)诱发的 N2 成分的波幅显著大于 CSf(–0.3 9±0.3 3 μ V),也显著大于CSn(–0.21±0.39 μV),CSf与 CSn诱发的 N2成分波幅无显著差异。电极位置、CS类型与性别三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P3:对习得的不同情绪CS图片诱发的P3波幅在400-600 ms时间窗的平均波幅进行3(CS类型: CSd、CSf、CSn)×2(性别: 男/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CS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性别为被试间变量。结果表明,CS类型主效应边缘显著,F(2, 66)=2.82, p=0.067, η2=0.14,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CSd(1.99±0.47 μV)诱发的P3成分波幅显著大于 CSf(1.28±0.50 μV),CSn(1.86±0.55 μV)诱发的P3成分波幅显著大于CSf。除此之外,在P3成分中没有其它主效应或者交互显著,all ps> 0.10。

图 1 厌恶与恐惧习得阶段的ERP女
4 讨论
与我们假设一致,男女不同性别在厌恶情绪与恐惧情绪的习得上,随着神经加工进程存在性别差异。在早期成分上,厌恶情绪与恐惧情绪的习得性别差异不显著,如N1和P2成分;但到了中晚期成分,如N2成分,男女不同性别在厌恶和恐惧情绪习得上出现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女性在厌恶、恐惧、中性情绪的习得上,三类CS的N2成分均差异显著,但男性仅厌恶与中性情绪的习得CS差异显著,恐惧与中性情绪的CS差异不显著。
从行为结果来看,在成功习得厌恶、恐惧和中性情绪之后,男女性在效价、厌恶度、恐惧度上均差异不显著,但在唤醒度维度上,男女性别差异显著,即相对于男性,女性对CS表现出更高的唤醒度,这与以往的行为研究结果有些许不一致,先前使用情绪图片的研究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评定不愉快图片上不愉快感更高,唤醒度也更高(Gard & Kring, 2007),Codispoti,Surcinelli和Baldaro(2008)研究也发现男、女性在效价与唤醒度的主观评价存在显著差异(Codispoti et al., 2008),但肌电活动、皮肤传导水平与心率指标上均无性别差异。在本研究中,条件性习得后,对CS效价评价上没有出现性别差异,原因主要是本研究使用ERP作为技术手段,为了有足够多的叠加次数,习得试次增加到90次,显著多于其它行为研究使用的次数,使被试对CS的不愉快感均降低,导致性别差异不显著;但由CS引发的唤醒度性别差异仍然显著,可能源于文化上的塑造与强化(Codispoti et al., 2008),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究。
从脑电结果来看,N2成分是与视觉相关的脑电成分,反映注意资源的分配,是对刺激特性的选择性注意(Campanella et al., 2002),研究发现当有一个短暂的唤醒或者对某一相关刺激进行选择性注意时,N2成分的波幅会发现变化(Määttä,Pääkkö;nen, Saavalainen, & Partanen, 2005)。在N2成分上,习得的厌恶情绪诱发的波幅显著大于恐惧和中性情绪;女性对三类CS均差异显著,而男性仅在厌恶CS与中性CS差异显著,即到了中晚期成分,女性对负性情绪均有较高的敏感性与区分度,但是男性仅对厌恶情绪较为敏感。
首先,本研究结果表明习得的厌恶情绪诱发的波幅显著大于恐惧和中性情绪,说明与习得的恐惧情绪相比,习得的厌恶情绪得到了更多的注意资源,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Charash和McKay发现,在情绪stroop任务中,厌恶刺激比恐惧刺激更容易引起自下而上地自动注意(Charash & McKay,2009)。原因可能是因为厌恶感最终与食物相关,厌恶情绪的生物目的是力求回避潜在的感染与可能引发的疾病(Rozin & Fallon, 1987),厌恶刺激有些仅仅是令人厌恶的,有些则是危险信号,需要加大注意来确定刺激的性质,然后决定后继行为,而且这种注意所需要消耗的资源较少。但是对于威胁性、引发恐惧的刺激信号投入过多的注意资源则有可能丧失最佳逃跑机会,弊大于利(Carretié,Ruiz-Padial, López-Martín, & Albert, 2011),所以对厌恶性刺激有更多的注意是生物适应的结果。
然后,在厌恶与恐惧情绪习得过程中,女性诱发的N2成分波幅显著大于男性,与以往结果一致。以往对男女情绪加工的大脑分区研究发现,女性在情绪鉴定和认知上比男性更快且更准确(Caseras et al., 2007; Wang, LaBar, & McCarthy,2006),主要表现在情绪感知过程中,女性在脑边缘和颞叶的活动比男性强烈,而男性在额叶和顶叶的活动比女性强烈(Hofer et al., 2007);同时,在情绪反应方面,虽然男女性的神经回路(额叶和脑边缘/亚属皮质)相似(Whittle et al., 2011),但大脑活动的差异取决于情绪刺激的具体类型,女性对负性情绪刺激的反应比男性更强(Deng,Chang, Yang, Huo, & Zhou, 2016)。表明女性对负性情绪刺激给予更多的注意资源,从而使她们对这些刺激反应更快,所以她们在处理负性情绪上所具有的行为优势可能归结于她们对所有负性情绪刺激敏感度均高(Campanella et al., 2012)。
再从男女性对具体负性情绪的反应上进一步分析,对于男性,仅习得的厌恶与中性情绪诱发的N2成分的波幅差异边缘显著;但对于女性,习得的厌恶情绪诱发的N2成分波幅显著大于习得的恐惧和中性情绪诱发的N2成分波幅,即男女性均对厌恶情绪有较高注意,但仅女性对恐惧情绪给予特殊注意,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如面孔识别情绪研究认为男女性别差异取决于引发情绪的类型,女性更能识别和记忆恐惧和悲伤面部表情(Sergerie, Chochol, & Armony, 2008; Tsolaki et al.,2017),而男性则擅长识别愤怒情绪(Kret & De Gelder, 2012),所以男女性最大的差异体现在诸如恐惧和嫉妒等负性情绪上(Whittle et al.,2011)。究其原因,进化理论认为,情绪行为不断进化是为了增加不同个体之间的吸引力或厌恶度,社会-关系理论表明,男女性心理以及与此相关的神经生物机制的不断进化是为了表现或鉴定某种情绪是服从情绪(如恐惧、悲伤)还是主导情绪(如生气、厌恶)行为。服从性的情绪行为与“信任线索”相关,通常被认为对女性更为重要,因为从进化过程来看,女性更需要关注危险的可能性。而主导性的情绪行为则与“能力线索”相关,通常被认为对男性更为重要。所以在神经机制上,女性对情绪反应更为敏感,特别是对恐惧、悲伤情绪更敏感,男性则对生气、厌恶情绪刺激更加敏感(Vigil, 2009)。虽然进化理论从一个角度解释了男女性对情绪具有不同神经敏感度的原因,当然这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本研究没有将人格特征因素(比如“述情障碍”)考虑在内,未来的研究有必要研究不同人格的男女性别在负性情绪条件性习得的不同,通过临床工作与实验研究的结合加深对神经病理学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