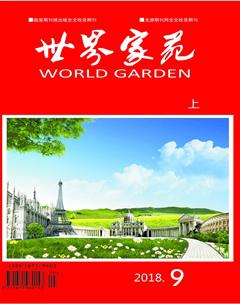浅析中学语文教材解读的多元性
谢欣伶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中学语文教材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多,因此关于中学语文的文本解读也是各种各样,那么该怎么对中学语文课本进行解读呢?如今,有非常流行的两种文学批评的观点来解读中学的文本:第一,作家中心论,考虑其作家的深层次思想与创作时所处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第二,作品中心论,也就是文本解读必须尊重其文本自身的价值,文本一旦创作完,那么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身的价值。本篇论文主要围绕这两点来进行阐述含义和总结建议。
关键词:中学文本解读;作家中心论;作品中心论
一、作家中心论
作家创作作品是在一个环境下创作的,这个环境能分为一个关于社会等大的环境,或者是自身所处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就是这两种环境的综合,作家在环境的影响下就会引起一些心绪的变化,当这种心情无法排解或者表现出来,那么作家的这种心情就会反映到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因此这也就是“作家中心论”的大概意思。
关于鲁迅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一个“作家中心论”的例子。关于这一篇文章有多种解法,鲁迅又是一个思想型作家,并且在写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已经四十六岁,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型作家,因此,他的作品必然带着成熟的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所写的“百草园”。明明“只有一些野草”鲁迅先生却说那时“是我的失乐园”,这是什么原因呢?文中描写的“三味书屋”。确实具有某些封建私塾的性质,于是有人认为文章的主题是“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其价值是“认识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身心发育的束缚和摧残”,其写法是用“乐园似的百草园生活和阴森、冷酷、枯燥、陈腐的三味书屋相对比”。那么,这种看法是否恰当呢,那么首先,我们要研究鲁迅先生写作这篇文章时的心境。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鲁迅先生有一段对他当时心境的描述: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下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这段文字引起我们思考的是鲁迅先生究竟受到了什么“纷扰”?心里为什么感到“芜杂”?为什么想着要“寻出一点闲静”?为什么“只剩了回忆”便觉得“生涯大概总算是无聊罢”?我们知道,从1925年1月18日开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学生驱赶压迫学生、反对校方中饱私囊违反章程向学生征收额外费用、反对压制民主自由的反对校长样荫榆的风潮;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为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的罪行,举行集会请愿,遭受到段祺瑞执政府卫队的疯狂虐杀。在这期间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鲁迅先生一直在进行着两段侧翼斗争:一是愤怒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二是无情地批判各种“文人学者”的种种“谰言”。后一翼的斗争尤其复杂,因为“文人学者”的面孔是多种多样的,外加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发表《失题》一文,对鲁迅先生的坚决斗争不以为然。面对这些,鲁迅先生怎不感到“纷扰”?怎不感到“芜杂”?这应该是鲁迅先生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个基本动因吧,抵御“纷扰”,抵御“黑暗”,排解内心的苦闷,正是鲁迅先生创作时的心境。
的确,“百草园”里只有一些野草,但这里有许多动物植物,有吃的玩的,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下,真是色彩缤纷。园里还有许多令人向往的神奇故事,冬天只要一下雪,就可以捕鸟来玩......这是一个充满童心,无忧无虑的世界,它怎么不会是“我的乐园”呢,这美好的回忆告诉我们,鲁迅先生童年和少年读书期间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是没有什么“纷扰”和心里“芜杂”的。因此鲁迅先生回忆起这样的生活,鲁迅的心里总的来说是感到闲静和愉悦的。
受封建教育体制的影响,“三味书屋”确实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它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以及师生关系都是封建的。文中也有这样的描写。但是,先生“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只是瞪几眼”;先生教读书和对课,没有强迫的影子,孩子们常常溜到后花园去“折腊梅花”“寻禅蜕”“捉了苍蝇喂蚂蚁”,在先生自己“读书入神的时候”,还给孩子们玩乐的时间和空间,孩子们“或用纸糊得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或“画画儿”。这哪有揭露和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身心发育的束缚和摧残”,哪有描写“三味书屋”阴森、冷酷、枯燥、陈腐的意味。鲁迅先生对这些回忆的描写只是在寻求摆脱当今的纷扰,抹去内心的芜杂,获取心灵的慰藉。
这样我们站在鲁迅的生活和思想经历的大背景中来解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思想内涵,不仅可以摆脱各种“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影响,而且可以真切地走进鲁迅。
二、文本中心论
文本中心論主要是以文本为中心,探究文本本身的价值,而在这些文本解读中不只是有作家的创作,更有他们创作的文本之后,文本就变成独立的了,就有它自身的价值。
关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首先题目《荷塘月色》四个字就包含着它到底是并列短语还是偏正短语,从课文中看,它是一个并列短语,包含着两部分,荷塘和月色,同时这两个内容又并不孤立,荷塘为“月光下的荷塘”,月色为“荷塘上的月色”。在这篇课文的第四自然段中用来这样的一个比喻:零星地点缀些白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这里的“明珠”言色彩,月下“零星地点缀着”的荷花,在夜色中的暗色调的背景下,白花就像“一粒粒”的明珠般晶莹剔透。“星星”动态。白花“点缀”在“层层的叶子中间”,在绿从中隐约闪烁,忽隐忽现,与“碧天”里的“星星”相似。“美人”言内质。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质朴、清新、纯洁、淡雅而高贵,与“刚出浴的美人”都纤尘不染;“刚出浴的美人”还使人想到水中月、雾中花那种朦胧美的意境。这三个比喻分别写出了淡月辉映下的荷花晶莹剔透的色彩,绿叶衬托下荷花忽明忽暗的动态,以及荷花不染纤尘的美质。并且在课本中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比喻,那就是通感,文中有句描写荷香“微风过处,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通感是被陈述者和陈述内容间诉诸于不同的感官。如:“缕缕清香”与“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相似处是:断断续续,若有若无,捉摸不定。但荷香属于嗅觉的范围,而“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则属于听觉的范围,朱自清先生把嗅觉和听觉交织在一起,启迪读者更加深远地想象和联想。
文中有这样的一句: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婀娜地开着,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在这看似很简单的一句描写中,其实它有着作者内在的安排,比如说为什么要先写婀娜地开着,然后再写羞涩地打着朵儿,这里是用了拟人的手法写出了荷花饱满盛开时轻盈柔美、妩媚的姿态。“羞涩”的意思是难为情,态度不自然,专写人的情态,在文中同样用了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荷花的骨朵儿羞羞答答,不好意思,含苞待放时娇羞妩媚的忸怩神态。这两个词把荷花写活累了,赋予了荷花以生命力,倾注着作者的主观感情,写出了荷花的神韵,可谓形神兼备物性人情统一。
因此,我们在对文本进行解读的时候,眼界一定要打开,多看文本解读资料,对文本有其自身的看法,不应只局限于一种观点。
参考文献
[1]王世群 《中学语文教学艺术研究与实践》重庆出版社
[2]程汉杰 《高中语文教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张卫中 《对话理论视角下的中学语文文本解读》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