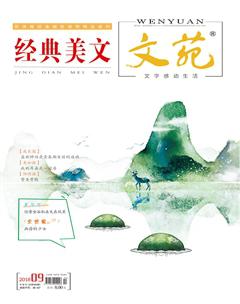纸上的李白(一)
祝勇
写诗的理由完全消失,这时我写诗——顾城
很多年中,我都想写李白,写他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我去了西安,没有遇见李白,也没有看见长安。长安与我,隔着岁月的荒凉。岁月篡改了大地上的事物。我无法确认,他曾经存在。
在中国,没有一个诗人的诗句像李白的诗句那样,成为每个人生命记忆的一部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人只要会说话,就会念他的诗,尽管念诗者,未必懂得他埋藏在诗句里的深意。
李白是“全民诗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家”。忧国忧民的杜甫反而得不到这个待遇,善走群众路线的白居易也不是,他们是属于文学界、属于知识分子的,唯有李白,他的粉丝旷古绝今。
李白是唯一,其他都是之一。
他和他以后的时代里,没有报纸杂志,没有电视网络,他的诗,却在每个中国人的耳头心头长驱直入,全凭声音和血肉之躯传递,就像传递我们民族的精神密码。
中国人与其他东亚人种外观很像,但精神世界有天壤之别,一个重要的边界,就是他们的心里没有住着李白。当我们念出李白的诗句时,他们没有反应;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抬头看见月亮,低头就会想到自己的家乡。所以我同意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话:“(古代的)‘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李白的诗,是中国人的精神护照,是中国人天生自带的身份证明。
李白,是我们的遗传基因、血液细胞。李白的诗,是明月,也是故乡。
然而李白,毕竟已经走远,他是作为诗句,而不是作为肉体存在的。他的诗句越是真切,他的肉体就越是模糊。他的存在,表面很具体,实际很抽象。即使我站在他的脚印之上,对他,我仍然看不见,摸不着。
谁能证实这个人存在过?
不错,新旧唐书,都有李白的传记;南宋梁楷,画过《李白行吟图》——或许因为画家天性狂放,常饮酒自乐,人送外号“梁疯子”,所以他勾画出的是一个洒脱放达的诗仙形象,把李白疏放不羁的个性、边吟边行的姿态描绘得入木三分。但《旧唐书》,是五代后晋刘昫等人撰写的,《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等人撰写的。
梁楷比李白晚了近五个世纪,相比我们,他们这些人距离李白更近,但和我一样,他们都没见过李白,仅凭这一点,就已经把他们的时间优势化为了无形。
只有那幅字是例外。那幅草书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李白写上去的。这幅字笔画回转,通过一管毛笔,与李白的身体相连,透过笔锋的流转、墨迹的浓淡,我们几乎看得见他手腕的抖动,听得见他呼吸的节奏。
这张纸,只因李白在上面写过字,就不再是一张普通的纸。尽管没有这张纸,就没有李白的字,但没有李白的字,它就是一片垃圾,像大地上的一片枯叶,结局只能是腐烂和消失。
那些字,让它的每一寸、每一厘,都变得异常珍贵,先后被宋徽宗、贾似道、乾隆、张伯驹、毛泽东收留、抚摸和注视过,最后被毛泽东转给北京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的书法,是法术,可以点纸成金。
李白的字,到宋代还能找出几张。北宋《墨庄漫录》中记载,润州苏氏家,就藏有李白《天马歌》真迹,宋徽宗也收藏李白的两幅行书作品《太华峰》和《乘兴帖》,还有三幅草书作品《岁时文》、《咏酒诗》和《醉中帖》,对此,《宣和书谱》里有载。到南宋,《乘兴帖》也漂流到贾似道的手里。
只是到了如今,李白存世的墨稿,除了《上阳台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张。问它值多少钱,那是对它的羞辱,再多的人民币,在它面前也是一堆废纸,丑陋不堪。李白墨迹之少,与他诗歌的传播之广,反差到了极致。但幸亏有这幅字,让我们穿过那些灿烂的诗句,找到了作家本人。好像有了这张纸,李白的存在就有了依据,我们不仅可以与他对视,而且可以与他交谈。
一张纸,承担起我们对于李白的所有向往。我不知该谴责时光吝啬,还是该感谢它的慷慨。
但终有一张纸,带我们跨过时间的深渊,看见了李白。
所以,站在它面前的那一瞬间,我外表镇定,内心狂舞,顷刻间便与它坠入爱河。我想,九百年前,当宋徽宗赵佶成为它的拥有者,他心里的感受应该就是我此刻的感受,他附在帖后的跋文可以证明。《上阳台帖》卷后,宋徽宗用他著名的瘦金体写下这样的文字:“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 不特以诗 鸣也。”
根据宋徽宗的说法,李白的字,“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与他的诗歌一样,“身在世外”,随意中透出天趣,气象不输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黄庭坚也说:“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只不过他诗名太盛,掩盖了他的书法知名度,所以宋徽宗见了这张帖,才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原来李白的名声,并不仅仅从诗歌中取得。
那字迹,一看就属于大唐李白。
它有法度,那法度是属于大唐的,庄严、敦厚,饱满、圆健,让我想起唐代佛教造像的浑厚与雍容,以及唐代碑刻的力度与从容。这当然来源于秦碑、汉简积淀下来的中原美学。唐代的律诗、楷书,都有它的法度在,不能乱来,它是大唐艺术的基座,是不能背弃的原则。
然而,在这样的法度中,大唐的艺术,却不失自由与浩荡,不像隋代艺术那么拘谨收压,而是在规矩中见活泼,收束中见辽阔。
这与北魏这些朝代做的铺垫关系极大。年少时学历史,最不愿關注的就是那些小朝代,比如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两宋之前的五代十国,就像一团麻,迷乱纷呈,永远也理不清。自西晋至隋唐的近三百年空隙里,中国就没有被统一过,一直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政权,多的时候,甚至有十来个政权。但是在中华文明的链条上,这些小朝代完成了关键性的过渡,就像两种色块之间,有着过渡色的衔接,色调的变化就有了逻辑性。在粗朴凝重的汉朝之后,之所以形成缛丽灿烂、开朗放达的大唐美学,正是因为它在三百年的离乱中,融入了草原文明的活泼和力量。
假若没有北方草原文明的介入,中华文明就不会完成如此重要的聚变,大唐文明就不会迸射出如此亮丽的光焰,中华文明也不会按照后来的样子发展,一点点地发酵成李白的《上阳台帖》。
大唐皇室包容四海、共存共荣。于是,唐朝人的心理空间一下子放开了,也淡定了,曾经的黑色记忆,变成了簪花仕女的香浓美艳,变成了佛陀的慈悲笑容。于是在唐诗里,有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视野,有了《春江花月夜》那样的浩大宁静。
唐诗给我们带来的最大震撼,就是它的时空超越感。这样的时空超越感,在此前的艺术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曹操面对大海时的心理独白,比如王羲之在兰亭畅饮、融天地于一体的那份通透感,但在魏晋之际,他们只是个别的存在,不像大唐,潮流汹涌,一下子把一个朝代的诗人全部裹挟进去。魏晋固然出了很多的英雄豪杰、很多的名士怪才,但总的来讲,他们的内心是幽咽曲折的。唯有唐朝,呈现出空前浩大的时代气象,似乎每一个人,都有勇气独自面对无穷的时空。
有的时候,是人大于时代,魏晋就是这样。而到了大唐,人和时代,彼此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