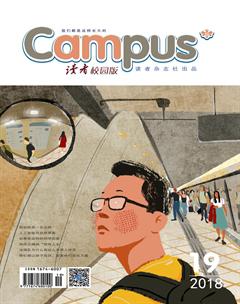一位化学家笔下的“美术史”
马凌
千百年来,艺术需求刺激了化学工艺的演进,绘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色彩谱系又因科学而扩张。化学家菲利普·鲍尔在《明亮的泥土:颜料发明史》一书中,从色彩的角度为西方美术史做出新的诠释。
锡管包装的“明亮泥土”
菲利普·鲍尔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在3万年前就开始装饰洞穴,他们所使用的颜料大部分来自矿物,还有一部分是从动物或植物中提取的有机物质。洞穴壁画绘制者从周围环境中获得常用色,红土和黃土来自赤铁矿氧化铁与不同温度的水结晶,绿土来自铝硅酸盐黏土,黑色来自木炭,棕色来自氧化锰,白色来自白垩和磨碎的骨头。它们虽然粗糙,但直至今日依然光彩照人。在19世纪现代合成颜料出现之前,这类“明亮的泥土”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物质材料。
从化学史的角度看,古埃及文明是一个真正掌握了化学知识的文明。古埃及的能工巧匠会使用酸和碱,懂得发酵、升华、沉淀、过滤,并把化学方法应用于玻璃制造、陶瓷上釉、肥皂生产等日常生活用品领域。在当时,色料制造是庞大兴旺的古埃及“化学工业”的分支。
在颜色的化学史中,炼金术也占据着重要席位。它披着神秘学的外衣,却有着一定的科学内涵。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相较于那些改变了18世纪科学的物理定律,艾萨克·牛顿花在炼金实验上的时间可能更多。作为一种古代的实践工艺,炼金术在根本上是一种“转化的艺术”,能够向艺术家提供人造颜料。在炼金的坩埚里诞生了红铅,它由白铅受热转化而来,在中世纪人们称之为“红丹”,曾在手抄绘本的方寸之地被大量应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17世纪的安特卫普,都曾经是“颜料之城”。不过在科学时代以前,颜料制作匠和染色匠,与伪炼金术士、蒸馏师、药剂师一样,并不受到尊重。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到19世纪20年代,化学家成为一种职业,收益可观,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在某种程度上,合成化学在19世纪取得的重要进步,正是被对人造颜料的需求所激励的,巴斯夫、拜耳、赫斯特、汽巴-嘉基等大型化学制品公司,都是以生产合成染料起家。
化学和艺术是互惠的关系:一方面,对颜料的需求激励了化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化学的发展也为艺术开辟了道路。例如,在印象派常用的调色板上,20种主要颜料中有12种是新的化学合成品,包括柠檬黄、铬黄、镉黄、铬橙、舍勒绿、翡翠绿、翠绿、铬绿、天蓝、钴蓝、人造群青、锌白。“明亮的泥土”不仅扩大了色阶,也呈现出各种新型样态。配合以商业化销售、机械化颜料研磨、锡管包装的发明,印象派画家们才有可能走向室外,在画布上表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颜色的文化属性和个人属性
菲利普·鲍尔在《明亮的泥土:颜料发明史》一书中涉及了另一个维度:颜色的文化属性和个人属性,他说:“画家们对颜色的运用还有其历史传统、心理原因、偏见、虔诚以及神秘之处。”
以古希腊为例,虽然发掘出的历史遗迹和文物有多种色彩,但是百科全书式作家普林尼声称,古典时期的希腊画家只用4种颜色:黑色、白色、红色和黄色。古希腊人之所以崇尚这种“高贵而节制”的理念,多半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影响——4种原色对应着亚里士多德的4种元素:土、气、火、水。古希腊人不喜欢将颜色混合,他们认为,与单纯的原色相比,混合的颜色低了一等。
又比如中世纪对金色、朱砂和群青的推崇,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美”,而且因为它们“贵”。展现昂贵而美妙的色料,不过是为了在观者心目中激起钦佩和敬畏之情。
到17世纪,铅白、大青、铅锡黄和朱砂从安特卫普的工厂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而传统的群青等上等蓝色,因为战事和资源耗尽,越来越难以获取,在1626年时,群青的价格非常昂贵。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位北方画家不惜代价,坚持用群青作画,他就是维米尔。他善用黄色、蓝色和珍珠白色,特别是对蓝色的精致使用,使他被称作“蓝色画家”。也正是这些用蓝色完成的作品,不仅使他与17世纪的其他荷兰画家区别开来,也使他超越了时代,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