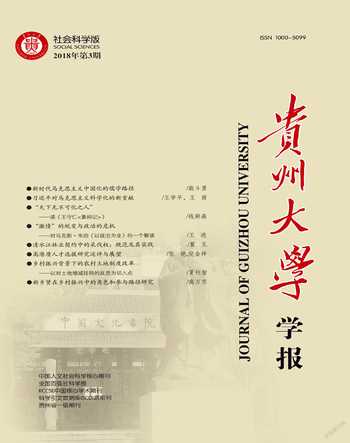晚清至“五四”时期男性视阈中的女权理论
杨飞
摘 要: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在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当务之急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的女权理论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女性问题主要由男性提出,男性主导,对新女性形象的设计和想象主要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是男性建构自身现代主体身份的方式之一,即通过对女性的言说来确立现代男性的主体位置;二是女性问题跨越了性别界域,成为民族国家话语的一部分,女性被要求与男性一样,将为民族国家的利益尽忠职守看成个人存在的最高价值,而作为女性主体的精神和价值、存在和体验则被忽视、被压抑。
关键词:晚清;“五四”;民族国家话语;启蒙话语;性别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3-0152-07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founding a modern nation as top priority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re are two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theory of feminism. First, female problems put forward by men, guided by men, were for the men to establish the self subject position through female stuffs as a way. Second, female problems crossed the border of sexuality, becoming part of national discourse, and therefore, females were required to regard being faithful to national benefit as the highest self value of existence,while their spirits, values, existence,and experience as women subject were ignored and depressed.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 the May 4th Movement; national discours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sexual power
晚清的女权理论由戊戌变法前后的“男女平等”逐渐过渡到20世纪初的“男女平权”,在实践上主要体现为“戒缠足”和“兴女学”两项措施。到了“五四”时期,晚清时附着于“强国保种”的女性问题由民族国家视角转向“个性解放”的文化思潮。从主张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个人主义出发,“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在学理探讨和实践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与晚清时期的情形一样,有关女性的话题仍然是由男性主导的。“五四”初期到1920年代以男女青年婚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典型地体现出这种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
一、 女权理论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互构
1938年,英国女权主义小说家弗吉利亚伍尔芙在其著名的反战文章《三枚旧金币》中写到:“作为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女人,我不需要祖国。作为女人,我的祖国是整个世界”[1]。我们只能把这句话看成是一个女性试图对抗和超越男权世界的情绪宣泄和愿望表达。事实是,身为一个女人,永远不可能和她生活着的民族国家脱离干系,伍尔芙在一个男士写信征求她如何阻止战争时写下这篇振聋发聩的女性主义宣言,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在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的时代环境里,重读这篇文章,给人以深思的,不是伍尔芙以女性身份向国家说“不”的激进态度,而是她对女性被国家随意征用的清醒认识:一直以来,女性无权参与国家一切大事的决定议程,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但是,一旦危机来临,战争爆发,国家却以民族大义之名,理所当然要求女性为战争做出贡献和牺牲。检视中国晚清至“五四”时期热闹纷纭的女权话语,尽管关于女性权利和女性自身的观念认识有所变化,但占据主流地位的女權理论始终从属于民族国家的话语建构。
“在历史上,无论什么时候,当深刻的社会变化发生时,当整个社会似乎受到威胁时,女人就会被‘邀请去积极参加公共生活;这几乎是一条规律了。”[2]中国历史上无声的女人们,就是这样,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在男性知识精英们的“邀请”之下,“浮出历史地表”,登上了民族国家的历史舞台。从19世纪中叶到新中国建立,面对西方洋枪大炮和文化知识的入侵,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成为时代的首要课题。在反思和应对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时候,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照成为时代精英们考虑问题的主要思维方式。在与西方文明的对照之下,“女性”作为一种文化符码,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盛和文明与否的价值标尺之一。在这种思维视野之下,中国女性群体的愚昧落后成为民族国家积贫积弱的标志,要建立一个国富民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改变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的生存现状。中国的女性问题就这样进入了民族国家的话语构架。由是,中国最初的女权理论便具备了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女性问题主要由男性提出,男性主导,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尽管当时也有一些杰出的知识女性如陈撷芬、张竹君、秋谨、何震等人从女性本位的角度提出以女性本身来解放女性为目的的女权理论,但她们的观念在当时处于边缘位置,并不能占据话语中心,而且除了何震之外,其他几位女性并不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参见须藤瑞代《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的相关论述。
其对未来女性形象的设计和想象主要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是男性建构自身现代主体身份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女性的言说而确立了现代男性的主体位置;二是女性问题跨越了性别界域,成为民族国家话语的一部分,女性被要求与男性一样,把为民族国家的利益尽忠职守看成个人存在的最高价值。这两个特点从晚清一直延续到“五四”之后。在学理上,晚清的女权理论由戊戌变法前后的“男女平等”逐渐过渡到20世纪初的“男女平权”,在实践上主要体现为“戒缠足”和“兴女学”两项措施。作为时代引领者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郑观应、严复等人对女性解放问题都有相关的陈说主张,但无一例外,在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学理探讨还是制度建设,女性问题都只是 “强国保种”的手段,非以女性利益为目的。作为最早创立不缠足机构的先行者之一,康有为即是以民族国家的建构为出发点来指斥缠足弊病的:“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发,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奕事体弱,是皆国民也,何以为兵乎?”[3]而所以要“兴女学”,是因为:“欲富强,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推女学之源,国家之兴衰存亡系焉。”[4]“故使中国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5]
梁启超是当时这些男性知识精英中最积极地倡导女权的人,影响也较深远,他将女性问题纳入民族国家整体框架的思路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自1896年的《论女学》开始,到1922年的《人权与女权》,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废缠足、兴女学的时文,并且在《记江西康女士》《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传记作品中,塑造了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国家相连的新女性形象。梁启超把缠足和女学联系起来,认为缠足是阻碍妇女上学接受教育的因素之一,他指出:“今中国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不宁惟是,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6]33梁启超大力倡导女学,其出发点与严复、郑观应等人一致: “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6]30
从戒缠足始,再到“妇学”而“蒙养”而“治天下”,女性身体和精神的解放就这样环环相扣地与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中,一些类似中国花木兰的西方民族女英雄,如法国大革命中的罗兰夫人,英法战争中的民族女英雄贞德,俄国的虚无党人苏菲亚等,她们的照片和事迹频频出现在中国当时的报刊书籍之中。与此相应,像《女娲石》《黄绣球》《东欧女豪杰》等此类女子救国题材的小说也流行一时。这两类关于女英雄的叙事形式反映了文化界将女性纳入民族国家整体框架的运作思路,并且强化了这一思路的意识形态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倡导个性解放的启蒙语境之下,尽管已有不少男性知识精英如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女性为本位的妇女解放,但女性问题关乎国家兴衰的声音依然在回响。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就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7]如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的《新青年》,在号召女性参与女子问题讨论的《新青年记者启事》中写到:“女子居国民之半数。在家庭中、尤负无上之责任。欲谋国家社会之改进、女子问题固未可置诸等闲。”[8]新文化运动主将吴虞也呼吁“贤妻良母”们“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
吴虞:《女权平议》(此文最早载《新青年》3卷4号,1917年,署名吴曾兰,后吴虞称此文实为他代夫人曾兰所写,故曾收入1921年上海亚东书局出版的《吴虞文录》“附录”中,后收入《“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时作者署名改为吴虞),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1年,第14页。,又如:“今之女子,非复一家一族之女子,而属于国家社会。其教育遂亦不仅系于一家一姓之兴衰,而系于社会国家之治乱。”[9]日本学者须藤瑞代在《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一书中清晰地勾勒出从梁启超、金天翮到1920年代的母性论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他指出,中国1920年代关于母性主义的讨论承续了梁启超和金天翮有关“国民之母”的思路:“女性也是‘人的意识已经为许多知识分子所共有,然而在此认识之下,他们的女性论还是将终极目的调整为不超越‘母之角色范围之内。”[10]在民族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刻,男性精英们“邀请”女性出场的方式:无论是“邀请”的名义——“国民母”“女国民”
“国民母”,“女国民”这两个名称是晚清时期女权理论界对新女性形象的想象与设计,其出现的时间约在1903—1904间,可见于金翮的女权主义著作《女界钟》(1903年),王妙如的小说《女狱花》(1904年)及《论铸造国民之母》(载《女子世界》1904年第7期),《女子为国民之母》(载《顺天时报》1904年6月17日)等文。,还是“邀请”的仪式——“戒缠足”“兴女学”,其最终目的乃是指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总之,“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 女子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 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 男性提出妇女问题( 妇女是‘问题), 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的途径, 妇女是载体/手段, 强国是目标。”[11]因此,从晚清一直到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女性理论始终隶属于民族国家的话语建构,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伟业相比,女性的解放问题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当更急迫的革命战争来临之际,女性问题就随时可能被替代或搁置。不过,可以庆幸的是,也正是作为民族国家话语的一部分,中国的女性问题从提出伊始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这在客观上加快了女性群体“浮出历史地表”的速度,在历史的舞台上获得了初步的社会地位。
二、“人的发现”对女性所指和性别权力的遮蔽
有学者指出,整个中国现代史上的新文化存在一种结构性缺损:没有建立一种科学的、反神秘化的求真传统,对大量涌进国门的西方学说,只是取其成果为信念,而非取其方法为科学。这种结构性缺损也体现在女性问题领域,“新文化更似一种政治焦虑的产物,一种自鸦片战争和东西文化碰撞以来民族主体对自身政治前途的巨大焦慮的外射物。女性在某种意义上同其他字眼——人,个性解放,民主、科学一样,成为缓解这种焦虑,象征性地满足这种政治愿望的一个意识形态筹码”[12]。即女性问题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作为知识或科学的对象,没有找到一种界定女性主体的语汇系统。在“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启蒙语境中,晚清时附着于“强国保种”的女性问题由民族国家视角转向“个性解放”的文化思潮。从主张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个人主义出发,“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在学理探讨和实践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与晚清情形一样,有关女性的话题仍然是由男性主导的。“五四”时期主张女性解放的先锋和旗手周作人就曾直言:“女子问题,终究是件大事,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不得不先来研究。”[13]由于一直以来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加诸女性的种种限制,使得当时能够借文字言说自身问题的女性少之又少。“五四”时期力主女性解放的文化精英们聚集的新文化阵地《新青年》曾有意识地引导女性来谈论自身的问题,为此特设“女子问题”专栏向女界征稿,但这一专栏自2卷6号始到3卷5号终,仅持续了四期,一共只有七位女性分别是李张绍南《哀青年》(《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陈钱爱琛《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梁华兰《女子教育》(《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1日);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陈华珍《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吴曾兰《女权平议》(《新青年》3卷4号,1917年6月1日);孙鸣琪《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新青年》3卷4号,1917年6月1日)。这七位作者中除李张绍南和吴曾兰二人经《新青年》说明确实是女性外,其他几位只从署名看像是女性,实际身份并不能确定是女性。而且,吴曾兰的《女权平议》由吴虞代笔,所以看似有七位女性,实则可能更少。发表了言论。从这几位作者的文章内容来看,她们的思想言论并未脱离民族国家话语的范畴:强调女性在尽妻子和母亲职能的同时,应和广大男青年一起为民族国家效力。即是说,个别女性虽然在男性启蒙者的期待和鼓励下出场了,但她们所发出的声音不过是在附和甚至是在复制男性导师们的声音,女性自我的声音是微弱的、缺席的,并很快就被男性启蒙者的声音所覆盖。指出这点,并不是要否定男性知识精英们对于中国女性解放的发起和进展所做出的贡献,毕竟,自晚清而“五四”,女性解放因被整合于民族国家和个性启蒙话语而进入了时代变革的核心领域,由此而加速了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进程。问题在于,这种非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权话语,当其旨向与民族国家和文化启蒙的归趋一致时,就得到加强并迅速播散开来成为时代共鸣,但与女性主体身份密切相关的身体和心理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当有更急迫的国家、社会问题(比如说革命战争)来临时,女性问题就因其与主流话语的疏离或冲突而被搁置和遗忘。
以新文化启蒙的先锋阵地《新青年》而论,该报主编陈独秀一开始就关注妇女问题,但早期刊载的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如陈独秀的《妇人观》《欧洲七女杰》,李亦民的《罗兰夫人》等, 《妇人观》载《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15日;《欧洲七女杰》载《新青年》1卷3号,1915年11月15日;《罗兰夫人》载《新青年》1卷5号,1916年1月15日。其讨论的语气和思路还是延续晚清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维模式。从第2卷4号陈独秀的《孔教与现代生活》明确打出反孔旗号开始,到第4、5卷陆续刊出周作人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胡适和罗家伦翻译易卜生的《娜拉》,胡适的《贞操问题》和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孔教与现代生活》载《新青年》2卷4号,1916年12月1日;《贞操论》载《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娜拉》载《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15日;《贞操问题》载《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我之节烈观》载《新青年》5卷2号,1918年8月15日。作为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最为深重的受害者,女性话题成了整个文化启蒙运动批判、攻击传统儒家文化的有力载体,这是“破”的一面。从“立”的一面来看,从“五四”初期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中期的关于女子教育、婚恋自由、社交公开、女子职业等妇女问题的探讨几乎涉及了女性社会生活的各个具体层面,但却少有触及女性主体作为一个“女人”的特质的探讨。要之,“五四”时期由男性启蒙者发起和主导的女性解放,在“人的发现”这一整体性的启蒙框架内,重点在将女性从旧文化旧礼教的压迫和束缚中解脱出来,求得人格独立 ,做与男人一样的“人”,而作为女人主体的特质和从封建礼教中挣脱出来的女性可能遭遇到的来自男权世界的新的压迫,却鲜有讨论。即便是周作人这样注意到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特质,倾注更多心力关注女性身体解放的启蒙者,也难免男性中心的视角局限。他在小说《可爱的人》的译后记中评论说: “他(女)爱男子,生育儿女,此外还应做人,他(女)对于丈夫儿女,是妻是母,还有对人类是个人,对于自己是唯一所有,我辈不能一笔抹杀他(女)的‘人,他(女)的‘我,教他(女)做专心奉事别人的物品。”并希望将来的女子“成为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14]。这里,周作人主要表述了如男子一样的女主角的“人”,而女主角的“我”则是空缺。
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对易卜生的三幕剧《娜拉》的戏仿改编,形象地阐释了“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解放的特色:将女性的反叛之声融汇于子辈反抗父辈的斗争而忽略了两性之间的性别权力关系。1919年3月,胡适在《新青年》第6卷3号发表《终身大事》,一时成为各校学生纷纷上演的热门剧目,当时“《终身大事》及《娜拉》的公演,使‘出走的意象,成为无数渴望自由的青年人浪漫悲壮的自我想象”[15]41。然而两剧中的“出走”意象差异颇大:《娜拉》中的女主角娜拉是因为拒绝做丈夫的“玩偶”,为追求女性的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而毅然离开家庭,揭示的是性别关系中父权对家庭和女性的绝对权力;《终身大事》中的女主角田亚梅,是为了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在爱人(对田亚梅而言是启蒙者)的启蒙和鼓励下离家出走,她反抗的是以母亲为代表的迷信愚昧和以父亲为代表的传统宗法制度,突显的是个人与家庭、青年与家长的冲突矛盾,至于在青年一辈之中是否存在新的性别权力关系,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启蒙话语是否会对女性(启蒙的对象)造成新的压抑和霸权,则付之阙如。诚如杨联芬的分析:“很明显,《终身大事》所代表的‘五四反抗包办婚姻的个性主义,确实没有从性别的角度对宗法制与父权制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辨析,而是笼统地将个性主义等同于个人反抗家族礼教和宗法制度,将个性主义的主题简化为青年与老年、个人与(父亲)家庭的矛盾。这样,女性自由,被个性自由囫囵代表了;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被新与旧的文化问题遮蔽了。”[15]42
三、想象女性:男性建构和确认自身现代主体身份的话语实践
梅雨蒸人,荷风拂暑,长林寂寂,远出沉沉。立于不自由之亚东大陆国,局处不自由之小阁中,呼吸困倦,思潮不来。欲接引欧洲文明新鲜之空气,以补益吾身。因而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烟卷,手榔杖,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吾惟以间接法知之。[16]
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部倡导女权主义的专著《女界钟》(1903年)的开篇,作者金天翮是晚清主张女性解放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该书从女子道德、女子教育、女子参政、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系统地讨论了妇女问题,一向被认为代表了晚清女性解放理论的最高水平。作者在该书“小引”中说明自己为何要提倡女权,上面一段引文乃是“小引”的开头。从这短短的开篇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第一,与欧洲“白色子”相比,哀叹自己的衰弱;第二,因此欲借欧洲文明“补益吾身”;第三,但是欧洲自由自在的情境只是出于作者的想象。由此可知,作者金天翮如此大力提倡女权,是出于男性自身需求的焦虑心理:在全球国家竞争的时代环境中,面对欧洲“白色子”“昂头掉臂”的优越,作为弱国子民的自卑、焦虑促使男性先觉者们努力要做一个自由、文明的现代人。由于对自己主体身份的想象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女人的定位也就起了变化,所以开始以新的标准(主要是参照西方的自由、平等、文明等概念)来规范女人,以便培养出能够陪同现代男性出入于公共场所的现代女性。“对这个年代的知识男性来说,借用海外的、特别是西方的男女平权这种言说是建构现代男性主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他把自己和以往的男性区分的标志。”“他推崇女权,既表达了处于种族等级劣势的汉族男性对平权理念的追求,也是出于动员女子加盟国族主义革命的需要,同时,这也成为标志他是现代男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17]5所以,“《女界钟》尽管通篇都在谈女性,但作者勾画现代女性图景的时候,无意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男性自画像,一个‘现代 中国男性的欲望的自画像。”[17]3自晚清而“五四”,男性启蒙者们不断综合古今中外文化中有关女性的描述,依照他们的现代梦想来阐释、规划现代女性的理想形象。“五四”时期男性对现代女性的想象鲜明地体现在启蒙与被启蒙的权利关系中。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8]当这一强调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智思考的主体性行为变为一场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时,就必然会产生话语霸权:凡不符合启蒙标准的便是不合理的。中国现代的文化启蒙就是一种由知识精英发起的超人对庸众、强者对弱者、智者对愚者的高高在上的启发与教化。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落后这样一种“进化论”的线性思维中,女性一直被视为落后的标志,处于弱者地位。所以,很自然地,在这场启蒙运动中,女性就成了被启蒙的对象,而男性则自居于导师的启蒙者角色,根据“平等”“民主”“自由”等等概念来启蒙、塑造并想象现代新女性形象。男性启蒙者先是从时代流行的话语中建构出一个现代男性主体的形象;接着从身边搜寻一个实实在在的女性朋友,借用一系列关于“进步”的神话,将他所选中的女性变形、塑造成他理想中的现代女性,这不仅确证了他作为启蒙者的主体身份,还满足了他的欲望想象;最后,当他塑造的现代女神为了一日三餐而不得不沦落为家庭女仆或超越他而成长为一个女性主体时,他为了维持自己的主体身份或抛弃她或指责她。鲁迅《伤逝》中的涓生于子君、茅盾《创造》中的君实于娴娴、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倪焕之于金佩璋,形象地呈现了这一男性启蒙者对女性的想象和形塑过程,彰显了中国现代启蒙话语中的性别权力關系。
这种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典型地体现在“五四”初期到1920年代男女青年们异常关注的婚姻和恋爱问题领域。自由恋爱成为“五四”“浪漫一代”的文化价值尺度,在这一主流话语的裹挟下,许多女性在男性启蒙者的召唤和鼓励下,为了爱情和自由,勇敢地冲破家庭的阻挠,与恋人一起坚定、骄傲地承受别人投来的轻蔑和讥笑。由学生、恋人到主妇,这些离家出走的叛逆女儿们很快发现,她们从父母之家到丈夫之家,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跳到另一个牢笼,在自由恋爱的名义下掉进了一场残酷的骗局。庐隐的小说《蓝田的忏悔录》中的蓝田被誉为“奋斗的勇将”“女界的明灯”,最后却愤慨道:“本来男子们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也可以狡兔三窟式的讲恋爱。这是社会上予他们的特权,他们乐得东食西宿”,“然而自何仁欺弄了我,不谅人的人类有几个有真曲直的,于是我便成了新旧所不容的堕落人了。”[19]在以“进步”为名的自由恋爱热潮中,“五四”时期非婚同居现象很普遍,[20]而一旦恋爱关系破裂,这些“进步”女性面临的道路无外乎三条:“第一是奋斗,其次是屈服,最后是自杀”[21]。在一个“女子没有真相”的时代,奋斗是模糊而艰难的(如茅盾《幻灭》中的章秋柳),屈服则意味着“落后”,终究是要被摒弃的(如叶圣陶《微波》中的忆云),自杀(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则彻底否定了女性解放话语,在她们追求自由的路上自由仓促地结束了。
上述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由男性所主导的女权理论,典型地符合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性:“而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则大都与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建国运动相伴生;而且及为有趣的,大都首先由男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存状况间或成为社会动员的有力方式之一,成为控拆前现代或殖民时代社会暴行的最佳例证,成为传播、印证现代性话语的成功途径。……而更为有趣的是,男性启蒙者的妇女解放的话语,尽管间或用于反殖民的社会动员,却同时成就着一种对‘进步、文明的西方的臣服,一种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文化父权结构。”[22]因此,在启蒙话语的召唤下,中国女性的解放不是附着于民族国家,就是依赖于男性启蒙者的阐释,女性自身没有话语权。在“个性解放”的潮流中,“五四”时代的女性们虽然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呐喊,但“我自己”是什么,则是一片空白,填补上这片空白,女性才能成长为主体,才能避免成为男性想象中的观念和欲望的客体。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生相伴,在这一进程中,伴随着每一次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中国的女权理论和女性解放程度也时隐时显、时高时低,处于变化不定之中。自晚清至“五四”,在“强国保种”的时代危机中,由男性主导的中国的女权理论和妇女解放的历史,始终和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但又充满张力和矛盾。一方面,借助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呼唤呐喊,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迅速地“浮出历史地表”,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加入了创造历史的行业队伍;另一方面,在由男性启蒙者主导的,以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而非从女性本位出发的妇女解放过程中,女性往往成为时代思潮和社会观念的载体而充当了意识形态工具,作为女性主体的精神和价值、存在和体验都被遮蔽、被压抑了。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女性因为自身语言和所指的匮乏,其主体的成长陷入了“女子没有真相的”意义困境。
参考文献:
[1]弗吉利亚·伍尔芙. 三枚旧金币[M]//伍尔芙随笔全集:第三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141.
[2]克内则威克.情感的民族主义[C]//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45.
[3]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摺[G]//麦仲华.戊戌奏稿.上海:广智书局,1911:43.
[4]郑观应.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M]//夏东元.郑观应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64.
[5]严复.论沪上创新女学堂事[M]//王栻.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468-469.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3.
[7]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
[8]新青年记者启事[J].新青年,1919,6(4).
[9]陶履恭.女子问题[J].新青年,1918,4(1).
[10]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M].须藤瑞代,姚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04.
[11]王政.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M]//越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178.
[1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绪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37.
[13]周作人.贞操论[J].新青年,1917,3(4).
[14]周作人.可爱的人[J].新青年,1919,6(2).
[15]杨联芬.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16]金天翮.女界钟[M].陈雁,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
[17]王政,高彥颐,刘禾.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C]//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8]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M]//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
[19]廬隐.蓝田的忏悔[M]//庐隐小说全集.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253.
[20]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7.
[21]奚明.社评[N].妇女周报,1923-11-8.
[22]戴锦华.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C]//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2.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