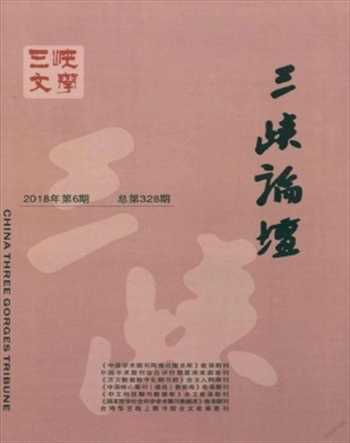从贵州土家族葬仪看土家先民的生活
何立高
摘 要:贵州土家族丧葬仪式是非常程式化的,有开光、穿神点祖、祭祀祖先、打绕棺等系列仪式,透过葬仪可窥见土家先民的生存样态。
关键词:土家族葬仪;贵州;先民生活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6-0025-04
土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说其古老,是因为源于古代巴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武陵山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说其年轻,是因为直到1957年才认定为单一民族。[1]本文以贵州土家族葬仪入手,试图对古代土家先民的生存狀态进行探讨,敬请专家、学者斧正。
一
丧葬仪礼,是人生最后一项“通过仪礼”,也是最后一项“脱离仪式”。倘若说诞生仪礼是接纳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话,丧葬仪式则表示最终脱离社会,它标志着人生旅途的终结。丧礼,古代社会视其为凶礼之一,它是处理死者时,殓殡奠馔,拜涌哭泣的礼节。《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丧礼哀死亡”的记载,说明丧礼之主要内容是对死者以示哀悼。一个人死后,活着的人为之发丧,表示悲哀悼念之情,完全是正常行为。但是,各民族的观念千差万别,有的认为灵魂可以转世,或灵魂不死。这样死亡往往被涂上神秘色彩,并由此产生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慰问死者灵魂的风俗。加之,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所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宗教信仰各自不同,于是形成丰富多彩的丧葬仪礼。
贵州土家族的丧葬仪礼活动,历来为土家族人民所普遍重视,丧礼主题基本相同:其一,表现生者对死者的哀悼;其二,怀念死者生前之功德;其三,超度亡灵,使死者灵魂得到安息;其四,通过信仰和禁忌仪式,免除生者对死者的惧怕心理和寄托于死者美好愿望。在贵州土家族的心目中,死对活着的人是悲痛,但对死者却意味着解脱了人间一切烦恼。所以,他们在葬仪上具有其独有特点:第一,在举办丧事的指导思想上是越热闹越好,就在热闹的土家族丧葬活动中,通常称其为悲事喜做,又叫“白喜事”。内容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第二,土老师(即土司子,有此土家族地区叫“梯玛”)是整个葬仪活动的主持人,声称其行走在阴界和阳界,能够与神鬼及死者沟通,并赋予很大权利,具有权威性;第三,祭品需由生食到半生半熟食到熟食。
二
贵州土家族对丧葬仪式十分重视,而且丧葬习俗至今改变不大,在整个过程中体现了对老人的崇敬,丧葬仪式较为隆重,并遵循着严格的程序。当老人病笃,就要准备伏包(纸钱封装好),按老人年龄的大少而决定伏包的数量。到老人谢世之际,马上烧“落气钱”和“路引”、放鞭炮。其“路引”是用白纸写上死者的生辰和死亡年、月、日、时,以此作为通过“地府”的凭据。之后由孝子给死者洗身。洗身的秩序是:额头一帕,胸口一帕,手心、脚心各一帕,洗手、脚是男左女右为序。再其后就是穿寿衣(有胸襟的衣衫和裤袜鞋),上衣全系布制成的纽扣,一般穿五身、七身、九身。穿五身即上衣三件裤子两条,七身则是上五下二,九身则是上六下三,裤带用蓝线或黑线,根数与年龄相等,鞋一双,袜一双。穿好寿衣后就开始了丧仪的四大步骤。
第一,开光仪式。其做法是将死者扶起成半坐状,或扶下床坐在板凳上,用两个碗装上大半碗生米,将死者双脚放在碗内米上,土老师手把灯盏在死者面前晃动,开头光、眼光、耳光、鼻光、口光、胸光、手光、脚光。土老师一边晃动一边口中念道:“开头光,亮头光,头顶青天亮堂堂;开眼光,亮眼光,眼光婆娑世界光;开耳光;亮耳光,耳听人间祸福祥;开鼻光,亮鼻光,鼻闻凡间五色香;开胸光,亮胸光,胸怀世界照四方;开心光,亮心光,心如明镜亮堂堂;开手光,亮手光,手拿乾坤日月光;开脚光,亮脚光,脚踏红莲万年长……”
第二,穿神点祖仪式。用一木牌,上写死者姓名、生死年月,将一只公鸡鸡冠血用笔沾血点在木牌名字上,口念道:“点头头动,点脚脚动,点心最光明……”当念到点头时,将鸡血点在名字的头一个字上,念到点脚时,将鸡血点在名字最后一个字上。然后送进祖祠安位。
第三,祭祀祖先仪式。祭祀祖先,又叫祭“八部大王”。人死后,由土老师主持丧礼。土老师一般有弟子三五人,他们是丧仪活动的中心人物。在入殓前,要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正中。正前方安放一张方桌,桌上放土老师及弟子的弓箭、师刀、锣、鼓、牛角等用具。再放上供品,有水果、大米、猪肉、鸡肉、豆制品等。供品开始供生食,随着葬仪的进展,换成半生半熟,再换成熟食。开始祭祀祖先,由土老师领唱,弟子随唱或合唱。唱词内容为祭颂赞祖先“八部大王”功劳业绩。每唱完一段就由土老师起舞,手执师刀,有时吹牛角,弟子则用锣、鼓配乐。跳舞内容则是表现祖先开山造田、生儿育女等情况。“整个土家民族的祖先,统一是‘八部大王。……八部即八个部落,八部大王即八个部落的酋长。”同时土家族又称之为“八部大神”,据笔者调查,并多次与土老师核对得知,“八部大王”即神王地主、将军老爷、三抚相公(田宣慰、冉宣慰、杨宣慰)、九风老爷、八面地君、川主、土主、药王三圣。
贵州土家族祭祀祖先或八部大王的记载,在明朝以前文献中不太明显,而在明代则较清楚了。明嘉靖《贵州通志》中有:“冉家蛮,……死丧、杀牛、击鼓、哀唱,祭毕,安于山洞而散”之载。明嘉靖《思南府志.风俗》亦有“击鼓”、“哀唱”等载。清《铜仁府志·风俗》记载:祭“八部大王”时,“巫党(指土老师及其弟子等人——引者注)椎锣击鼓,以红巾裹首,戴观音七佛冠,登坛歌舞,右手执有柄铁环曰师刀,上有数小环,摇之声铮铮然。左手执牛角,或吹或歌或舞,抑扬拜跪,电旋风转”。民国《贵州通志》亦有“丧葬亦歌舞”的记载。[2]祭“八部大王”唱词为:“鸣角扰扰叫一声,神王地主大神,将军老爷得知闻;鸣角扰扰叫二声,三抚相公三尊神;鸣角扰扰叫三声,九风老爷得知闻;鸣角扰扰叫四声,八庙地君八尊神;鸣角扰扰叫五声,川主、土主得知闻;鸣角扰扰叫六声,药王三圣三尊神。”唱词一完,则祭祖活动结束,就将死者装进棺材,跳丧活动进入第四阶段——“打绕棺”。
第四,打绕棺仪式。又叫“穿花”或曰“绕棺”,就是围绕灵柩旋转,且歌且舞的活动,这一阶段是葬仪的高潮时期。
“打绕棺”活动参加人数不限,三五人或十佘人不等,有时多达数十人。凡参加操办丧事之人、亲戚朋友及看热闹的旁观者,均可参加合唱、跳舞之行列。前面由一人执引导灯领唱或领舞,后面的人也随即起舞或歌唱,加之又配上锣、鼓等打击乐器,使整个绕棺场面更加活跃,丧仪变成了有趣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唱词唱法别具一格,内容丰富,掺杂了大量的民歌歌词,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其唱词内容大部分为死者在生时怎样成家立业、养儿育女、待人处事之事。若死者为男子则内容为“勤苦勞动”、“围山守猎”、“孝敬父老”等等。若死者是妇女,则内容大多为“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等。“跳舞”的内容表现出渔猎活动,农事活动、军事活动等情形。首先,“跳舞”一开始就表现出渔猎活动的情形,如“黄鹰展翅”、“野羊钻网”、“围山守猎”等动作。再跳表现为农业生产活动,如“播种”、“栽秧”、“薅草”、“收割”等动作,这正好是粮食生产的全过程。接下来是跳表现军事活动的,如“引弓射箭”、“舞刀耍剑”等。整个打绕棺活动终结,标志着丧仪的高潮阶段结束。
“打绕棺”仪式的舞蹈刚劲有力,表现了土家族人民粗犷豪放的性格。“打绕棺”最早见于《隋书·地理志》的载述,“其左人则又不同,无哀服,不复魂。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词说尽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犹今之挽歌”。考究其文中“左人”是指住在僚人聚居地附近的人,书中所指之地正好位于今天渝黔湘鄂四省交界之武陵山区,笔者不敢说“左人”就等于土家族先民,但是,说“左人”中有部分是今天土家族的先民是完全可能的。前面说到的《贵州通志》、《思南府志》、《铜仁府志》,没有《隋书》这样记载详细,但可以看出,“击鼓”、“哀唱”、“或歌或舞”与“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有许多共同之处。“说尽平生东事,以致辞终卒”,与今天的打绕棺内容完全相同。[3]既然跳丧活动很早就有,为什么又能保存下来经久不衰?这除了自身心理特点外,还与黔东北地区山高路险、水流湍急、荆棘丛生和交通极不便有关。还有与葬仪既安慰死者娱乐生者的二者统一性有关。
三
从整个葬仪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
关于土家族的族源问题,至今学术界多种说法,主要有“湘鄂渝黔边土著说”,“江西移入说”、“巴人后裔说”和“贵州乌蛮后裔说”等。虽然都举出了一些证据,但均难以令人信服。尽管有人从地理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角度进得过探讨,都终究没有得出一致意见。笔者对这些说法不敢妄加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土家族先民很早就定居在渝黔湘鄂四省交界地区。这从土家族丧仪和祭词中就有所反映。祭祀祖先的人名、地名均出自渝黔湘鄂边地区,如“思南十八堡”、“播州十八坪”、“梅花洞府”、“悬花岭”等。说明土家族很早就在这一带生息。三抚相公中的田宣慰、扬宣慰、冉宣慰为三大姓,他们分别在思南、务川、沿河、印江、德江、遵义及重庆酉阳、秀山等地,这亦是土家先民活动生产于该地区的佐证。
从跳舞的动作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家族的先民亦经过从渔猎生活到农耕生活的过程。生产方式同样是由渔猎向农耕过渡。而土老师的祭具从“弓箭”转变为“刀”、“鼓”、“锣”及文献中“杀牛祭祖”的记述来看,说明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先民有畜牧业,但牛很少用于农耕或者纯粹不用于耕地。换句话说是农业生产不发达,耕作面积小,没有认识到牛耕的重要性。在明以后的文献中未有杀牛的记载,说明贵州土家族地区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耕种面积扩大,牛在农耕上占有重要地位,就不再杀牛祭祖了。丧仪中舞蹈难度系数较大,这无疑与土家族先民们“喜险阻,善战斗”的性格和生活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地域有关。再者土家族本来就是一个善舞的民族,古有“巴渝舞”,近有“巴山舞”,现有“摆手舞”,今天贵州的土家族还喜爱“打闹鼓舞”、“薅草锣鼓舞”等。
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旁观热闹者,均可参加“打绕棺”仪式,这表现了土家族尊敬长辈的高尚品德,团结精神。恰恰再现土家族先民们,在渔猎生活时,单个人力量不能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需要团结起来,共同获取生存资料的历史。在生产力有所发展,产品有了剩余,需要团结起来,保护劳动产品,抵抗外族入侵的历史。
土家族的葬仪活动中,祭祖的供品,从生食到半生半熟再到熟食来看,则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有过生食的阶段。在原始社会狩猎时期,当时人们不曾认识到利用火来烧烤食品,防寒取暖,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才逐渐过渡到熟食。这一历史痕迹在葬仪中均有所保留。
从贵族土家族葬仪活动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认识:土老师在整个葬仪活动中是核心人物,具有权威性,一切听从他指挥,一切问题都必须征得土老师的同意方能进行。土老师在土家族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威望,他的灵魂能够上天。若土老师死,要先“开天门”,将灵魂“升天”后才能安葬,在手心、胸口、背上都盖了红印,印是“到天朝地府”通过各路关卡的标记,[4]反映出土老师在历史上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可能是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之一。
结语
贵州土家族的葬仪活动,始终保持着浓郁的民族色彩,内容丰富多彩,带有集体性、娱乐性,既安慰死者灵魂又娱乐生者。我们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窥见土家族先民经过“茹毛饮血”的生活到渔猎再过渡到农耕生活这一历史进程。
土老师很可能是原始部落酋长的影子,故今仍享受历史的余光。另外,从丧葬祭祀中也可看出,土家族先民们很早就定居于今渝黔湘鄂四省交界地区了。
注 释:
[1] 严天华主编:《贵州土家族文化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4年。
[2] 陈国安主编:《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辑·土家族卷》,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8年。
[3]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辑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4] 陈国安主编:《贵州土家百科全书》,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8年。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向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