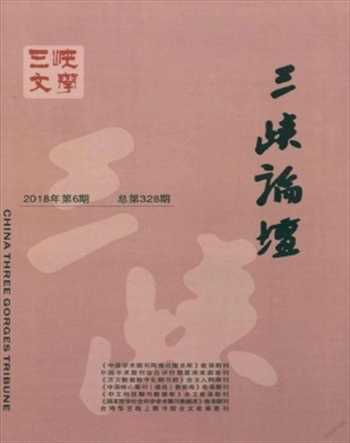论土家族传统医药的基本特点
梁正海 罗钰坊
摘 要:土家族传统医药是土家族民众生产生活和抗击疾病经验的积累,它源于生活实践,又反作用于生活实践,具有可及性强、毒副作用小、简便价廉、疗病奇效等特点。总结这些特点,对于正确认识土家族传统医药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土家族医药;可及性强;毒副作用小;简便价廉;疗病奇效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6-0012-07
土家族传统医药是土家族民众生产生活和抗击疾病经验的积累,它源于生活实践,又反作用于生活实践;它为民众所创造,又为民众所利用;它是民众对大自然的认知与感悟,又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无私馈赠。在土家族村寨从事田野调查期间,让我们感受颇深的就是民众经常说的这样一句话——“大自然能够让你致病,也一定有治愈你疾病的药物。”在土家族民众看来,人与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共生系统。正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无私馈赠,形成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可及性强、副作用小、简便价廉、疗病奇效等基本特点。
一、土家族传统医药可及性强
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基本药物和药物政策项目使人们对药品可及性产生关注。2003年的SARS病毒、2005年的禽流感以及2009年的HIVNI等流行疾病爆发,由于治疗药物的稀缺、药品费用高等原因造成的治疗困难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关注药品可及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人类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维持健康手段的医疗需求与日俱增,及时获取医疗资源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主题。从供方角度研究了影响药品可及性的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包括:到卫生服务机构的距离、市场的药品拥有程度、医疗机构的采购状况和医生的处方行为。”[1]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看,土家族传统医药作为一种医疗类型,其可及性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到治疗点距离近、治疗手段简便、治疗者易得、习俗规约下的上门服务等。
其一,患者到达治疗点的距离近是土家族传统医药可及性强的表现之一。传统医药是在传统背景下依托地方性土壤孕育而生,是普通民众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它的形成背景、过程决定了它与普通大众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造就了知识持有者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既可以是普通劳动者,也可以是医者,还可以半农半医。民间医生往往没有专门的医疗点,其医疗点就设在自家庭院。村落是人类聚落发展的一种低级形式,其空间范围通常较小,民间医生的住所作为其中的一个结点,它连结着住户与住户,其形成的半径通常在1千米以内。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当村民生病求医时,能很快达到就医地点,得到医生的及时治疗。相关研究表明,城乡结构失调是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一大现实,城市集中了全国80%的卫生资源,而城市大医院又集中了80%的卫生资源。更多的卫生资源又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这此地区的大城市、大医院;卫生资源在农村的配置却极其有限,相比之下,老少边穷地区的卫生条件更差。[2]因此,对于药品可及性的距离障碍主要存在于农村以及不发达城市。[1]产品供给的不足,再加上距离的时空障碍,广大乡村民众从现代医疗服务机构获得及时性治疗的机会变得极其有限。土家族主要分布于黔湘鄂渝交界的武陵山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地区很难从现代医疗服务机构获益;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山区交通虽然有极大改善,但交通水平依然不高,民众从现代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及时性治疗的难度依然很大。比如,位于恩施州来凤县百福司镇的兴安村,是鄂、湘、渝三省交汇之地。此处距离百福司镇近30千米,离来凤县城更远。若村民遭遇急性病,无论去百福司镇还是去来凤县城救治,长距离的奔波对患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我们在湘西龙山县苏竹村调研时,[3]彭大尧用手指着他家对面的岩上说:“那是保靖的地方,离保靖很远,有一个小孩晚上害病了一直背到坡脚去看,要赶十五里路。如果是大人害病就更加麻烦了,是很急的病就更麻烦了。” 事实表明,偏僻村落中的民间医生在场,对于患者不仅是一种希望更是一种幸福。
其二,土家族传统医药治疗手段的简便易行是其可及性强的又一个表现。土家族人对疾病的治疗模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对自然疾病的药物治疗,二是对象征疾病的仪式治疗,三是神药两解。[4]比如淋巴节发炎,彭大尧告诉我们用三味药调和后敷在患处即可治愈。“三味药一是捉老鼠的猫拉的屎;二是成年老石灰,一般在老坟上、老房屋上都可以弄到;三是芝麻油或香油。”这是显而易见的药物治疗。叶金桂又告诉我们说,“腰带疮最扎实,痛得很,用韭菜兜兜、油菜叶子就能包好。小孩起包,用蛤蟆草顶上那个托托,捣啐了敷就可以了。妇女流产,生小孩流血多,用散血草,用菜油或茶油煎鸡蛋都可以治。小孩感冒了,咳嗽,用树油籽一捶包在肚脐上,可提寒。端午节时,用金银花、九灵罐、千年光、四棱草给小孩洗澡,不生疮。”彭大尧和叶金桂给我们提供的药物治疗病例,不仅用药十分常见,而且用法也十简单,只要知道用药,操作过程几乎人人都会。这种治疗方式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形式:一是内服,二是外用。内服或用水煎服,或与食物同煮而食,或与酒同泡。外用又有捣碎外敷或煎水擦洗。藥物治疗使用的药物多数都易获得。“百草都是药。”这已经形成了传统村落民众的共识。平时有个小伤小痛,不必看医生,只要自己去住所附近的沟沟坎坎找药就可以治疗。
其三,土家族传统医药持有者的易得性也是其可及性强的表现。张厚良对黔东南州苗医进行调查。得出了与张东风相同的结论,民众应用草药极为普遍,几乎每个人都能掌握几种甚至几十种药物治疗方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特点,“百草皆药,人人会医”。[5][6]事实上,不仅苗侗村落,而且土家族村落也是如此。我们在武陵山区土家族村落调查时就发现,无论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几岁孩童,多多少少懂一些草药知识都是一种普遍现象。生活于村落中的民间土医生也不在少数。他们有自己的行医准则,一般而言,只要病人请求其治疗,他们便会欣然允诺,会竭力为病人治病。而为患者提供上门服务形成了一个显著特点。民间医生为什么情愿提供上门服务,乡村患者为什么更愿意在家接受治疗?我们认为关键因素在于民间习俗的制约。乌丙安先生以研究民俗威慑理论为前提研究了民俗控制类型,并将之概括为六大类,即隐喻型民俗控制、奖惩型民俗控制、监测型民俗控制、规约型民俗控制、诉讼型民俗控制、禁忌型民俗控制。[7]167从我们的调查研究来看,乌丙安先生概括的六类民俗控制类型中的禁忌型民俗控制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一般而言,汉语词语“禁忌”与英语单词“Taboo”的基本含义是相同的,都是禁止接触的意思。从民俗学意义上理解,“禁忌是对于社会行为和信仰心理活动加以约束的传统观念和做法的总称。它既有传统习俗观念约定对俗民某种行为加以禁止的客观意义,也有习俗化了的俗民在信仰心理过程中自我抑制的主观意义。”[7]206禁忌的主客观意义使得乡村民众不会冒险破坏习俗的控制。这既是为人处世的需要——谁都不愿被他生活的群体摒弃,又是“安全第一”原则[8]的需要——谁愿意因为某种违禁行为而给自己带来灾难呢?从我们在武陵山区域调查的数个村落来看,乡村传统对于特殊人群——诸如伤病患者、孕妇、产妇等——的活动范围有着特殊的规约。《思南县乡镇概况》[9]对27个民族乡镇的信奉禁忌作了较为概括性的介绍,从“信奉禁忌”条目所列举的内容看,不准身带血污进屋,以免引来“血光鬼”,影响产妇分娩,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禁忌。忌说带有病、死、杀、痛等不吉利的话等禁忌则是整个武陵山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禁忌。[10]湘西土家族甚至不让伤病患者进入灵堂,这种行为被视为对死者和主人家的不尊重,等等。显然,在乡村民众的认知心理上,伤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是一群不洁之人,他们的不洁会像传染病一样,因为他们走动而传播给其他人。同样的道理,由于民众禁忌病、痛等言语的表达,带着病、痛之人进入他者的家,显然是不合适宜的。事实上,类似的案例和研究,无论是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为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回到我们提出的问题,对于民间医生提供上门服务和乡村民众那种家庭式就医选择就更加容易理解。既然患者担心因为自己的“位移”而把不幸带给他人,把医生请到家里治疗或医生主动到患者家里实施治疗就变得合情而又合理了。由此,我们不仅深深感受到了民俗文化对于俗民控制的强大功能,而且更加体会到了在民俗规约下乡村民众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宽容。这种理解与宽容无论对社会和谐稳定,还是对患者病愈都大有裨益。
二、土家族传统医药对人体副作用小
我们曾通过《土家族传统医药及其现代利用》[11]一文,对土家族传统医药的病因机理、防病治病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研究来看,鲜药的现采现用、科学的药物炮制、日常生活中的食物疗法等,都有效地降低了药物对人体的毒副作用。此不赘述,但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所涉及主题,对土家族日常生活中的仪式疗法进行深入分析是必要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土家族仪式疗法的实质是一种心理疗法。如果说药物治疗有低副作用,那么仪式治疗可谓“纯天然”疗法。巫医结合、神药两解,是土家等各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防病治病习俗。英国一位名叫罗伯特·玛格塔的医学史学家曾经说过:“医学起源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原始社会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复杂仪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产生于其中。”[12]10参杂巫术行为进行防病治疾是土家族传统医药应用的一大特点。伴随着仪式治疗进程的推进,我们发现最初用于治病的药物被道具化,药物被视为治病仪式的一种重要元素。从形式上看,仪式治疗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视其为迷信,因为在这一神秘化的治疗情境中,巫术治病的作用机制无限彰显,现代医学所称的心理疗法正以一种倒置的方式发生作用,医生充当了一个中介,以一种特定方式代替病人宣泄,激发某种抗病的潜能。事实上,依靠本能和自身的潜力抵抗疾病,是人类早期维持身体健康的主要方式。[13]巫术仪式在医疗过程中的作用正在于它对人类本能和潜在能力的激发。模拟病人症状、表演绝技、同鬼神沟通交流等,巫医这些看似怪异的行为,不仅对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减轻病人心理方面的痛苦有效,而且还能有效增强患者信心,激发病人对抗疾病和疼痛的自我潜能,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比如“卡子水疗法”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的一种疾病治疗方法。当鱼刺或尖硬的物质卡在喉咙的患者救治时,巫医先打一碗清水,然后开始念口诀[14],并不时用手指在碗里沾一点水,向空中弹一下,表示敬天。接着在水碗上画一个字徽[15],不过他们到底是画一个什么字,外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然后砍九节竹筷到碗里,每节长约3厘米,然后,让患者端起水碗,连水带竹节,一口气吞进肚里。据说,除留下一点水敬地,碗里的水和竹筷必须吞完。毫无疑问,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有学者研究认为,卡子水本来是治疗鱼刺卡在喉中的一种巫术,现在已演化成一项带有一定表演色彩的巫术。[16]204这一方面反映了传统文化在文化产业化尤其是全域旅游背景下的变迁和主动适应,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民间文化极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卡子水疗法之所以广为人知,因为它在解除患者疾苦方面的确发挥了积极功效。[17]我们在土家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期间,卡子水疗法常常是中老年人向我们津津乐道的主题,这种津津乐道本身即深切表明了他们对这种疗法及其功效的认同。对社会经济持续生产意义是文化的本质,其生产的意义又需要为涉及到的人创造一种社会认同。[18]1显然,卡子水療法作为一种民间医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持续生产了意义,而且为其意义所涉及的民众创造了一种社会认同,这种社会认同正是它持续生存的根基。
在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民间社会这种仪式疗法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关于其合理性的讨论,我们需要明确对三个概念即疾病、病患和病态的认知。对于这三个概念,我们不能简单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界定和分析,因为人体的某种异常状态不仅与生物结构本身的常态有关,而且也与患者的文化和信仰关系密切。对此,医学人类学对“疾病”“病患”和“病态”三个概念做了区分。医学人类学认为,作为一种生物尺度,疾病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做出的医学判断。病患是病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感知和判断,是一种主观状态。相对于疾病和病患而言,病态则是他人对病人健康状况的承认,因此,它被视为一种社会状态。在生活中,我们通常用“疾病”一词代替了上述三个词的涵义,这说明我们对生活中疾病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病人自身共同建构的结果。这种疾病认知的多元化建构无疑为仪式疗法提供了理性基础,这是仪式疗法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它存在的必然性。当然,仪式疗法的存在也涉及民众对医生医术认知的问题。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乡民对民间医生医术高低的认知度往往与医生掌握的法术相关,不懂法术的民间医生在民众的眼中甚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医生,当然更不是一个好医生。
三、土家族传统医药的获取简便而价廉
土家族传统医药的简便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利用天然药用植物防病御病,还是运用咒语、口诀等巫术仪式治疗,它们操作起来都十分简单易行。价廉是土家族传统医药的另一个特征。与现代生化医学昂贵的医疗费相比,其价廉的特征显而易见。简便与价廉密不可分,它们共同组成了土家族传统医药的一大优势。
土家族传统医药获取和治疗都十分简便,这主要决定于其治疗手段的简单易行和生态药物资源的就近和免费利用。就治疗手段而言,我们知道土家族传统医药的治疗模式通常有三种,即天然药用植物治疗、巫术仪式治疗及神药两解。其中药物治疗大致为内服、外用或内外兼用;用药多为鲜药,常常现采现用。总的来看,无论是用水煎服、泡药酒服,还是同食物一道服用、捣碎外敷、浸泡擦拭等,这些用法都不复杂,普通人都能掌握。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民间医生也会采摘一些药物放在家里晾干,除了以备不时之需,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增加药物的神秘性。鄂西兴安村一位医生这样说:将采摘回的草药晒干,是为了给病人心理安慰。因为有些治病药方颇有实效,但药物普通,将药物晒干后很难辨识,这样一来可以使自己的药方保密;另一方面,如果病人得知药物实在普通,未必相信药物的疗效。很显然,他们晾晒药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消患者心理上的顾虑,从而提高治疗的效果。由此可见民间医生的一片良苦用心。
土家族传统医药不仅方便,价格也便宜。苏竹村彭大尧用自己祖传的医药知识给村民治病,不仅给村民带来了方便,而且也给贫穷的村民减轻了负担。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在请他对民间用药与医院用药费用做一个比较,他说:“我这里花两三元可以买到的药,在龙山县城花十几元才能买到。我试过一次,就是有一次文文的婆婆胃痛,在龙山抓的药,花了十几元,在我这里只需要三四元。”彭大尧简简单单的一个案例比较,不能不令人深思。事实上,反思现代医疗体制下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已不仅仅是学者的视野,它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因为如此,对于民间医生陈永常的深度访谈,我们至今难忘。采访的时间为2014年8月9日,地点在思南县胡家湾苗族土家族乡一街长虹专卖店。为了进一步讨论的需要,我们不妨把采访录音整理如下:
笔者:听说您接骨头很厉害?陈永常:这个是原来学到的嘛。笔者:我是特地来向您请教的。陈永常:我这个不是知识撒。笔者:您这是技术。听说您给别人接骨头都是到别人家里去,为什么呢?陈永常:这个原因是,骨折的人不能轻易挪动,家属也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去,在自己家里安全,没有什么顾虑,这个有利于病情治疗。骨折就是第一要归位,第二要预防破伤风。笔者:据说有些人粉碎性骨折,要特别注意归位。陈永常:有些骨头露出来,很残忍。笔者:归位了有没有什么影响?陈永常:没有什么影响。笔者:您行医多长时间了?陈永常:我从1976年一直干到现在。我是专门干这个,庄稼都没种,我今天还要去医冠心病、胃病,这些我都是特效。我行医比较宽,凤冈、德江、许家坝都去,昨天交通局还来了两个。笔者:是来接您去治病的?陈永常:它送过来的,我负责包的。方式说给他听了,别人负责给他上药。我每天到处跑也跑不全撒,但药是在我这里拿。笔者:像这种粉碎性骨折要治多长时间?陈永常:要棒棒的话就要四十多天,不要棒棒可能要年多点。笔者:您现在给接一个一般要多少钱?陈永常:现在一般重点的伤要三四千块钱,但是去医院的话,钱花得更多又更复杂,虽然钱可以报销但是疗效没得我这个快。笔者:一般重伤都来找你?陈永常:一般轻伤不来找我,他自己搞点药就能解决事情。再说也轻易找不到我了嘛,我是这里跑那里跑的。笔者:你都是到病人家里去?陈永常:方便撒。
陈永常医生行医治病至今40年过去了。从未放弃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是一个民间从事医疗的专职医生。如他所说:“我是专门干这个,庄稼都没种。”但是,他却是一个没有从业资格证的民间医生。作为转业军人,把在部队所学的知识与民间医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悬壶济世的秘笈,不能不令人称道。作为一个农民,放弃对庄稼的耕种,可以说是对庄稼汉生活的一种反叛,但是,他却因手中掌握的医药知识,四处游历,治病救人,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活。我们从他质朴的话语中深切地感受到,即便自己医技高明,对粉碎性骨折、冠心病、胃病等疾病手到病除,但他总是把方便留给患者,自己上门施治,或把药物配好,治疗方式告诉患者亲人,既减轻患者痛苦,又减少对亲人的折腾,当然,这同时减轻了他来回跑动的劳累,可谓多方受益,其乐融融。如此建立起来的医患关系,完全可以想象那种和谐——充满感激的和谐。当然了,这种和谐不仅仅建立于上门服务或方便式服务,适度的医疗费用也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关键的因素。之所以说它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如果医疗费用太贵或贵得离谱,患者根本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或放弃这样的选择性治疗,医患之间无从建立治与被治的关系,自然无所谓和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患者对这样的医生一定充满了恨!“一般重点的伤要三四千块钱。”这是陈永常对收费的自我把握。这里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个概念,否则我们无从进一步讨论“方便价廉”这个话题,那就是“一般重点的伤”。如果我们离开特定人群特定习惯而按照通常意义的理解,那么这个“一般重点的伤”其实并不重,那么“三四千块钱”的收费就值得质疑。从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一般重点的伤”概念的界定在陈永常的心中指的是“粉碎性骨折”之类的重伤。“一般重点的伤”的表述是民间日常的习惯性表达,这本身也表达了乡村民众对疾病的一种超然态度。事实上,大量事实表明,即使一个人行将就木,当有人问及其病情时,其亲朋大多会这样表达:有点重、可能不行了。在乡村民众心中似乎根本不存在“病危”、“重症疾病”等这样的概念。或许正是因为乡村民众保持着这样一种心态,他们很少无病呻吟,面对疑难重症,他们常常顺其自然,不会为了自己疾病的治疗而给儿女留下大笔债务。人财两空,通常不是他们的选择。回到“一般重点的伤”的话题,再对照民间医生这一概念的界定和对应收费,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点赞。
四、土家族传统医药疗病有奇效
疾病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都是认知和治疗疾病的重要密码。土家族人主要聚居于武陵山一带,特殊的自然生态为各种毒蛇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场域,生产劳动中人们常常受到毒蛇伤害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土家族人掌握了大量治疗毒蛇咬伤的秘方,疗效十分显著。我们在湘西土家族村落调研时,报道人就特别向我们介绍了治疗毒蛇伤的专科医生和治愈毒蛇伤的案例。叶金桂是苏竹村公认的治疗毒蛇伤的土专家之一,我们第二次到苏竹村调研时她给我们讲述了治愈海伦(彭大针的乳名)的过程。她是这样讲述的:那边有个被毒蛇咬了,两三天了,全身都长泡了,还开始吐血呢,牙齿缝里都是血。跟乡里县里医院联系,说至少准备五千块钱。他家医不起,开始也不晓得我会,别人给他说我晓得,他家里的人就来请我,给我说好话,他妈还跪着求我,我也很同情他们,就去给他治。他两只手都被咬了,全身都是泡,我说不敢打包票,给他弄点药试试,又给他包药,又用棉花陀陀沾药了竹棍夹起擦洗身上的泡,后来他就睡着了,喊都没反应,我还以为他死了,后来他醒了说:您的药好哦,敷上了就不痛了,我就睡着了,我两三个晚上没睡着了。
粉碎性骨折对于患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然而,在灾难面前民间医生并没有退缩。他们凭借着一腔热情和执着,在實践中积累了治疗粉碎性骨折的经验,形成了一种独道的治疗风格。在此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深入体味对陈永常医生的采访录音,它能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民间医生对治疗粉碎性骨折的自信。治疗粉碎性骨折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困难的就是把碎骨归位,归位的关键在于懂得筋脉。“筋脉很重要,要把它理顺。骨头外面有一层白色韧带包着,你可以拿手顺着摸过去,哪里有情况就清楚了,然后把突出的按平,手法很重要。”陈永常医生一边讲述,一边用手比划,也许是担心自己没有说清楚,怕我们听不懂吧?但是,陈医生是坦率的,他甚至可以把药方给我们,也不担心药方被人拿走。“我不担心,因为他拿去不起作用。一是他不懂手法,骨头不能归位。二是他不懂经脉和穴位。”“这个药的配制和配量也很重要,光告诉你药方是没得用的,我也希望有个人来专门研究一下,把这个药方能够传给后人。乡村老百姓在医院消费不起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有意义的事情。”陈永常医生真就把药方告诉了我们,还对配方作了一番说明。出于一种职业道德和对被访者的尊重,我们不便公开药方。但是陈永常医生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钦佩。陈永常医生还掰着指头列举了用这个药方治愈的好几个案例。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陈永常医生治疗粉碎性骨折的特殊技法和用药的特殊功效。
土家族對粉碎性骨折疾病治疗的功夫是独到的——尤其是仅靠对经脉和穴位的理解而全凭手法实现归位。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背景,传统医药既把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元素,又把人体与大自然之四时相对应,很早就对于经脉有着独特的认知——通过脉象之阴阳,论证病情和判断预后。与四时相应,人有四经,与月份相应,人有十二从。即如《黄帝内经素问卷第二·阴阳别论篇第七》所言,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而“切”更是中医察病的四大要素之一。依据脉象察病疗病成为传统中医的重要生存和发展之道。陈永常作为一个具有“再生性”民间医药的传承人,不仅熟悉经脉特点,而且还能根据经脉的分布靠手法归位粉碎性骨折,其医技不可不谓之高明。或许正是因为他对经脉认知之深刻,使他对自己的医技充满了自信。因为自信,所以,他不怕把自己治疗粉碎性骨折的药方告诉别人,因为,他相信就算别人知道了药方,不懂得经脉和穴位,依然等于零。
作为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家族传统医药在维系民众身心健康,保障土家族持续发展,至今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可替代。随着现代医药的冲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土家族传统医药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传承面临重重危机。延续土家族传统医药这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医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应有贡献,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土家族传统医药的优点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注 释:
[1] 李海涛:《从供方角度探讨我国药品可及性问题》,《医保视角》,2009年第5期。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概要与重点),新华网http://www. china.or.cn/chinese/health/927874.htm.,2008年12月21日。
[3] 湘西苏竹村是一个土家族为主体的村落,笔者于2007年7-8月、2008年7-8月、2009年11-12月先后三次前往该村进行田野调查。
[4] 梁正海:《传统知识的传承与权力》,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
[5] 张厚良:《农村医疗与苗族民间医师合法化问题研究》,《亚太传统医药》,2006年。
[6] 张东风:《苗侗医药,亟待开发的矿山》,《中国中医药报》,2010年。
[7]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8] “安全第一”原则,是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时借用J.罗马赛特的术语,见《农民农业技术的风险与选择:菲律宾的安全第一与水稻生产》,载于威斯康星大学社会体制研究所:《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1978年8月第7118期。转引自[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9页。农民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对古典经济的利益最大化提出了挑战。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经济问题,借用这个术语主要目的是讨论乡村民众面对对传统习俗的破坏可能招致各种想像中的超自然力量的惩罚而带来生存危机而自觉遵守习俗惯制,接受民俗的控制,优先选择安全第一原则。
[9] 思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思南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思南县乡镇概况》,黔内字(97)第5-027号,贵州省地勘局一〇三队印刷厂,1997年。
[10] 关于这一禁忌,彭英明主编《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禁忌”条、向柏松著《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土家禁忌”条都有记载。
[11] 梁正海:《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及其现代利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2] [英]罗伯特·玛格塔:《医学的历史》,李诚译,希望出版社,2003年。
[13] 程瑜:《乡土医学的人类学分析——以水族民族医学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4] 卡子水口诀:画个圈圈,师傅在身边;画个圆圆,师傅在眼前。弟子叩请师傅某某,差言请师傅添言,差语请师傅添语。吞谷单,化谷单,是谷化成灰,五龙归大海。铜钉铁钉,一律磨成水吞。铜钉化成灰,铁钉化成水,是谷化成灰,五龙归大海。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
[15] 亦说是在画字讳,但无论字讳,还是字徽,都是巫医在治疗过程中的一种行为方式和创造行为意义的过程,书写的差异可能在于发音,但这种差异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仪式的理解,也不会给仪式操演主体带来混乱或误解。
[16] 龙云清总纂:《铜仁百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
[17] 有学者认为,吞筷子本身实际上并不是治病,而是为了显示巫者的功力和本事,给患者增加信心。(见龙云清总纂:《铜仁百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4页。)这显然是以仪式操持者为中心的一种陈述,但是这种陈述本身却蕴含了一种极为巧妙而又高超的心理暗示。对于病人而言,相信医生,充满希望,也许是一种最好的疗法。
[18] [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向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