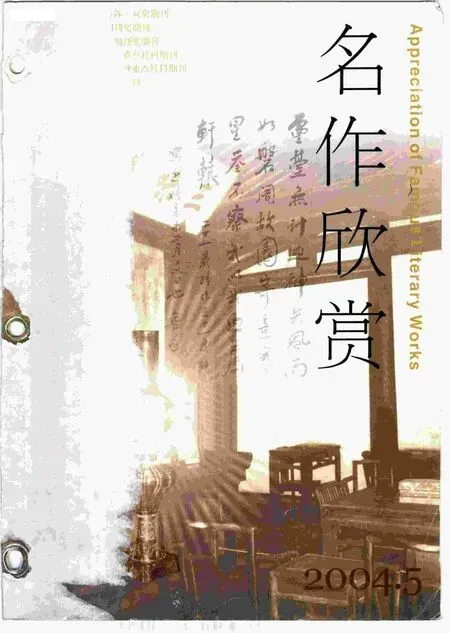银幕档案:吕班电影创作巡礼(五)
陈墨
《没有完成的喜剧》(1957)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8本。编剧:罗泰、吕班;导演:吕班;摄影:张翚;演员:韩兰根、殷秀岑、方化、陈衷等。
影片由三个互不相干的故事组成。一是,大华器材公司经理朱福生无视法规,铺张挥霍,盛气凌人。去外地休养途中,在火车上遗失了钱包,捡钱包者贪财,遭遇乘警,心虚跳车,失足被火车轧死。有关部门在死者身上发现朱经理的工作证,遂通知朱经理的工作单位,单位得到此讯,为朱经理布置了灵堂。朱经理无法忍受疗养院的规则,提前归来,死人复活,嚇坏了杨秘书。朱经理作风依旧,挑剔灵堂和悼词,说应该加上“永垂不朽、万古流芳”,并要杨秘书订制高级棺材,可在家具费里报销,由他签字。杨秘书说,已经有了新经理,他无权签字。朱经理大为恼火,说:“我没死!我活着呢!我还很健康地活着!”
二是,胖子和瘦子二人参加联欢会,瘦子小侯喜欢吹牛,说他会跳各种舞,从前在上海演出,场场满座。听者当真,要他们俩现场献艺,胖子大窘,小侯灵机一动,分别扮演小宝贝和小公鸡,稚拙的表演,让全场捧腹。见到体育专科学校的人,小侯又吹牛说他们也擅长体育,胖子怕他再吹牛,灌了他一嘴啤酒。
三是,母亲进城,胖瘦兄弟俩争抢母亲当保姆,见母亲年老体衰,又相互推脱。母亲在两家轮流居住,干粗活,吃劣食,外加儿媳冷脸与白眼,母亲不堪虐待,只好到女儿家去住。报上登出某老太向国家献一古瓶,得奖5030元,兄弟俩都想起,母亲也有一个旧瓶,遂重扮孝子,不约而同地来到妹妹家,再次争夺母亲。其实母亲所带旧瓶并非古董,哥儿俩并不知情,争抢之际,将旧瓶摔破。
影片中三个故事,分别被称作《朱经理之死》《大杂烩》和《古瓶记》,其中前两个名字若改为《生死记》和《吹牛记》,或更有味道,也更合乎实际。在喜剧形态上,三段故事有不同特色,分别是黑色幽默、轻喜剧和讽刺剧。第一段故事采取了多种喜剧手段,滑地板、哈哈镜、夸张、巧合、滑稽表情,还出现了牛科长的花圈,让人联想到《新局长到来之前》。这段喜剧的核心元素,其实是一个大活人出现在自己的灵堂中,还对灵堂布置、悼词写法挑三拣四,呈现典型的黑色喜剧情境。第二段故事很短,也很简单,小侯吹牛说自己会跳舞,其中包括“瓶子舞、罐头舞”;说当年演出,剧场爆满,不仅有坐票、站票,还有“绑票、骑票”,会听的人,一听就知是谎言。让吹牛者表演节目,不过是寻欢作乐,要将吹牛者打回原形。第三段喜剧比较板正,两个儿子自私自利,儿媳刻薄无情,本是苦情戏的标准桥段;只因儿子要扮孝子,言行严重分离,才作为喜剧元素,出现在讽刺剧中。为争古瓶,装作报答慈母恩,如此孝行,当然令人齿冷。
《没有完成的喜剧》的真正重点,是它的元戏剧式创意,亦即采取戏中戏形式,将三个不同的故事,嵌入同一叙事框架中。影片开头,是由两位主演自报家门:“我们找电影,电影找我们,要问名和姓,(韩:)我叫韩兰根,(殷:)我叫殷秀岑。”这两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成名的喜剧演员,以真名实姓出现,形成了纪实性叙事线索。他们进了电影厂,与批评家易浜紫(谐音“一棒子”)相遇,即跨过了虚拟情境的边界。他们之间有一段关于喜剧之花的对话,易浜紫说:“这块园地上又要增添一朵新鲜之花,喜剧之花呀,开吧,开吧,尽情地开吧!”韩说:“就怕我们开不出鲜花来。”殷接:“反而开出一蓬野草来。”易浜紫总结:“讽刺喜剧呀,这可是一条危险、曲折而又难走的道路,还要不怕挨打,那才行。”这场对话,是喜剧电影人的自我解嘲,竟成了喜剧命运的谶语
在审查节目时,易浜紫对三个故事无不挑剔批评。第一个故事,他说是:“恶意的诽谤”,“打击面太宽了”;第二个故事,他说“在政治生活当中竟然会是这样的吗?这种片面的、夸大的表现方法所造成最明显的恶果,就是把生活当中极个别的现象,当成了生活的本质,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当前的生活认识不清。”对第三个故事,他说:“这不是喜剧,绝对不是喜剧。喜剧应该使人发笑,可是我看了之后,反而发怒。这不是喜剧,而是怒剧。”最后是:“总而言之,依我看你们这三个节目都要不得,绝对要不得。”——这些话,正是“反右运动”时对影片的批判台词。
六十年后重看这部电影,人们有各种不满:觉得它主题直露,或内容简单,或格调不高,或思想不深,或喜剧性不足。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只不过,我们不能忽略,在当年,吕班拍讽刺喜剧,是戴着镣铐跳舞。影片中的故事——三段喜剧外加易浜紫的挑剔批评——看似互不相干,且形态不同,却有更深层的相通:影片中人大多有病,共同症结是:心智发育不良。看起来,他们都是成年人,但他们的心智、理性、良知,都没有达到成年合格标准。《生死记》中的朱经理,位高权重,作威作福,其主要性格特征,无非任性,公然批评杨秘书“对我也讲起制度来了!”就是证明。在疗养院里,他既不想锻炼,更不愿节食,终因受不了疗养规则,负气提前离开;在自己的灵堂中,不处理生死误会问题,反而挑剔悼词美恶,如此表现,恰如不可理喻的小顽童。《吹牛记》中的小侯爱吹牛,喜欢逞口舌之快,实质上,是分不清或不愿区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这正是儿童心理的典型特征。其后,瘦子扮作小公鸡,胖子扮作小孩,还穿上印有“小宝贝”的围嘴兜,正是恰如其分。《古瓶记》中两个不孝之子的道德病,说到底也是心智病,完全不懂伦理推理,不明白自己也会老去。最终扮孝装哭,扮小装愣,为争古瓶,耍猴戏,装狗熊,仿蟋蟀,种种儿戏,暴露其儿童心智原形。批评家易浜紫,老气横秋,脱发秃顶,似乎满腹经纶,实际上,不过是装腔作势、模仿教条、任性胡批,这种言行,正符合康德定义的心智不成熟状态:亟须启蒙。
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完成的喜剧》确实没有真正完成。作者虽抵达社会文化病的前沿现场,且努力呈现出喜剧艺术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二者毕竟尚未水乳交融。换个角度看,这部喜剧电影匆匆做结,即使未达标,但找到了正确起点,并已在探索途中。只可惜时不他与,“反右运动”开始,吕班成了右派。他的艺术天才没有完成,且——恐怕没有人会想到——永不再有完成的机会。
后语
吕班拍摄喜剧,是因为他热爱喜剧,且有喜剧天赋,但也是为了响应当年电影局领导的号召——1954年10月,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为提高电影艺术的思想艺术水平而斗争》,提出了要拓展题材样式,专门提出了我们没有喜剧、传记片、儿童片的问题。喜剧有多种形式,诸如诙谐、幽默、滑稽,当然还有讽刺,更有后来的(《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那样的歌颂性喜剧。呂班独钟讽刺喜剧,不仅是出于对讽刺喜剧的自信,更有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忠诚,要做新时代的啄木鸟: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槐未肯归。
不料会遭遇“反右运动”。在当年批判“右派”大会上,有人(姑隐其名)这样批判吕班电影《没有完成的喜剧》:“作者所处理的贯串在三个节目之间的所谓辩论,就像一根锁链一样拴着三条恶狗,张牙舞爪地向着新社会、向着党、向着人民做着疯狂的咆哮和攻击。如果说这个作品有什么主题思想,那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它的主题思想了。”证据是:《朱经理之死》中“有一个姓朱的朱经理,有一个姓杨的杨秘书……这两个姓都是谐音,因演经理的是个胖子,所以姓朱,其实就是‘猪’;因演秘书的是个瘦子,所以姓杨,其实就是‘羊’。在这个机关里头,上级是蠢如猪,下级是可冷而受压迫的羊,这就是右派分子心目中我们机关里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简单地说,这里没有人,只有畜生!”依此类推,“在第二个节目《大杂烩》里头,那个瘦子演员又被叫作小侯了。姓侯原没有什么不好,但这里姓侯却是作为猴子来解释的……吕班的目的是在‘丑化’新社会,因此又是一个‘畜生’!”如此索隐比附,肯定让今天的读者眼界大开,若非文字俱在,或许有人怀疑,这样的言语是出自八千年前人类的原始思维。
在“反右运动”中,吕班低头认罪,在接受批判过程中,写下了多份检讨,揭发和批判自己,也揭发批判喜剧社同仁。正如那些同时罹难的同仁,也同样在自我揭发批判的同时,揭发和批判吕班,这种行为在当年非常普遍,可以说是政治生活所要求。
被打成“右派”的这一年,吕班44岁,正处于人生的鼎盛之年,亦是一个导演艺术家的黄金岁月。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其后19载,即19~1976年,吕班44岁至63岁,成了他沉痛荒芜的余生。吕班没有自杀,因为孩子都还小:小班7岁、小宁6岁、小飞2岁。他没有死,更重要的原因,是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忠心,期望等到党组织为他平反昭雪的那—天。
成为右派后,吕班被降职降薪,留在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先后从事过杂工、装卸工、锅炉工等工作,这些活,他少年时都曾干过。最难也不过是,在卸煤的时候,会腰酸背疼,外加气喘咳嗽。到道具车间管库房那一段,一定是吕班当年最惬意的日子,不只是因为这活轻省,更因为在道具车间有许多沉默老友
不少道具都曾在他的影片中出现过,每件道具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回忆,甚至对话。例如,在拍摄《六号门》时,他曾自作主张,用摄制组的经费,在天津购买了多套红木家具,送给电影厂做道具。作为道具库管员,他仍“贼心不死”,钻研道具和道具管理的学问,写下了厚厚几大本笔记,想著书立说。
1969年,吕班的日子不好过。不是因为挨斗挨批,这算不了什么,此类事他已习惯,羞辱和伤痛,打不倒曾经沧海的人。难过的是,须与妻子离婚,与孩子断绝父子/父女关系——孩子长大了,要各奔前程,有个右派父亲,如同乌云盖顶——只有离婚,妻子才能解脱,孩子们前途才有一线光明。于是,离婚。命途多舛的吕班,再次妻离子散,独自在吉林省东丰县凉水村被管制劳动,天涯一隅,孑然孤身。只不过,温厚而倔强的吕班,把凉水村的日子,过成了另一段生命传奇,据凉水村的乡亲们回忆:“我吕大爷人家那老头厉害,木匠活、铁匠活啥的都会,给大伙儿做”;“我家小孩儿多,有病了他给治”;“专政组找他有啥用?大伙儿不给他说坏话,那老头为人老好了!”(引自小班、小宁:《吕班百年》)
1976年5月,吕班生病,因不愿牵累儿女,只身投奔河北农村的妹妹郝碧玺家疗养。曾入天津和平医院,遭遇唐山大地震。当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吕班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写信,表示:“今后我有生之日,此生已非自有,谨以挚诚请求党委,希在我一息尚存之际,即时给我以机会,让我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党中央,来悼念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贡献一切。我宁愿在战斗中粉身碎骨,也不愿在病床上了此残生。”(小班、小宁:《吕班百年》)吕班的这一心愿,未能实现。1976年11月14日22时,吕班突发心梗逝世,结束了他多灾多难亦多姿多彩的63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