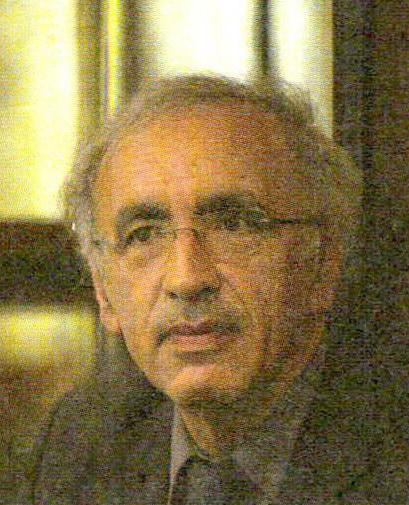去中国留学
白乐桑
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有几个时刻是难忘的。
对我来说。第一个难忘的时刻是1973年5月15号下午,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当时我正在学校里(巴黎第八大学),再有一个来月我就大学毕业了,正处在学习中文与就业之间的纠结当中。这个难忘的时刻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中国恢复了同法国的文化交流。当时作为普通大学生,文化交流所涵盖的内容以及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不太了解。原来,中法两国1964年1月27日建立外交关系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互派留学生,当年的秋天法方派遣了20名法国不同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去中国留学。为什么说中国恢复了呢?那是因为中国在“文革”开始后中断了与法国等国的文化交流。这时中国又宣布恢复与法国等部分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在当时,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就是互派留学生。我们当时对文化交流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但对中法互派留学生感兴趣。我们问学校有关人员,留学生有助学金吧?他们说对了,你们会拿助学金的。有了这种机会,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说,你们赶紧去外交部,领取申请表格,以后有没有面试,现在还不知道。
这一切就发生在我快要放弃中文的前一个月!于是,我就跑到外交部拿了一张表格。我记得,表格中让我们填写研究计划。我们哪有什么研究计划呀?所以,当时在填写表格的研究计划一栏时,我现在也不知道填了什么,大概随便写了两三个研究计划(好像其中一个是成语),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行过研究。然后,我就将表格交给学校了。
在1972-1973年最后一个学年中,我正在写毕业论文。本来中文系的学生人数就不多,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学生就更少了。可是,我还是坚持到底了。我们人数虽然很少,但也得写一篇毕业论文,差不多有一百页。虽然知道我们那个中文系的文凭就业价值等于零,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放弃,所以,必须得写一篇论文。当时,我对成语典故特别感兴趣,可能是因为我学过哲学的原因吧,觉得有的成语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活化石。于是,我就去找我的两个同学,对他们说我有一个想法,你们看看行不行。他们也要写毕业论文,但写什么还没有主题。所以,当我说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们就问是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是对成语故事感兴趣吗,咱们把那本中文的《现代汉语成语小辞典》译成法文并加以前言、解释、注解等。它一共有三千个成语典故。我说我们三个人,每个人承担三分之一。具体做法,第一是翻译,找出一个与它对应的约定俗成的一个法文说法。第二就是对那个典故加以注解。我还建议,每个人也写一个关于成语的导读。这样比较实用,一方面可以继续提高我们的语言水平,因为那时我们的汉语水平毕竟还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这样翻译出来的东西也比较实用。我问:“怎么样?”他们说:“好,同意。”我们就按分工各自动手进行了。分工是按每位同学姓名的字母顺序安排的,这样我就承担这一部成语词典的前一千个成语,从a(记得有按部就班、安居乐业、爱屋及乌等)到h(邯郸学步、豁然开朗等)。结果,他们没完工,我完工了。1973年6月,我通过了这一千个成语的论文答辩。在论文的评委当中,有一位教文言文的知名汉学家,吴德明先生(Yves Hervouet),还有我说的那位丹尼斯教授,她一两个月后就得病去世了。
正好在那段时间,也就是参加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去中国留学的申请已经由学校转交给了外交部,但要求去中国留学的人数还比较多,我当时算最年轻的一个,已有许多人在排队了。其中,有一个比我们大五岁,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就是贝罗贝先生(Alain Peyraube),后来跟我一起留學北京大学,并且成了一位著名的汉语言学家。我跟他比较熟,他比我们大五岁。我觉得,外交部当然要优先考虑他,我当时是比较年轻的。当时还没有面试,也不知道外交部召集的评委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但无论如何,最终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一年,中国给法国选派交换生的名额特别多,有30个。当时中国对外交往中是区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同当然被列为资本主义国家,可是法国是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名额数量最接近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国30个名额,阿尔巴尼亚42个名额,意大利与英国分别是8个和9个名额,瑞典3个名额。可能就是因为名额多,我才被选上,当然也有很多没有被选上的。所以,这个结果我完全没有想到。但是,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就这样发生了。教育部公布了一个名单,里面有我。当时,我高兴万分,像做美梦似的。
不久,外交部召集我们这些被选上的学生去开会,负责留学事务的官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的信息。别忘了,当时也没有旅游业,我们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开会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认真地记笔记,他们向我们通报了一些比较古怪的信息。其中,有两个我印象最深。一个是“中国的电压是110伏”。当时,我就想,法国电压都是220伏的,电压不对,我刮胡子怎么办?我想的也是一些比较古怪的事情。结果到中国以后发现,中国的电压跟法国是一样的。为什么外交部官员那样说呢?我后来才知道,好像只有三里屯使馆区的电压比较特殊,全中国的电压都是220伏。另一个是“中国没有洗发香波”。教育部的官员说:“好,请你们记一下,中国商店没有洗头发的香波。”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个信息的。开完会回来,我们就犯愁了。我们在中国可能要待一年啊,不洗头怎么行?当时不知道我会一待就是两年。其实,到北京之后,我第一次到学校周边的商店转了一圈之后就发现中国是有洗头发用的东西的。
这些信息当然是从法国驻华使馆传过来的。但是,法国使馆工作人员应该知道至少北京友谊商店是有这些东西的。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得到相反的信息?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另外,在这次会上,他们还告诉我们中国有人民币呀什么什么的。但总体来讲,我们对中国的日常生活情况其实一点都不知道。
知道了自己被选派到中国留学之后,我非常激动,在做随时出发的准备。所以,在1973年的夏天,我决定休假的时候不能走得太远,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离开法国。我觉得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所以,我当时就在法国境内等待着消息。8月份当然是休假的时候,不可能有什么消息。到了8月底,也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到了9月份,我去外交部问,负责的官员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去中国。还是等消息吧。”那好吧,我只能等着看。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接待外国留学生的各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北京语言学院刚刚复校。所以。我们才等了很长时间。本来,我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去中国了。已经通知我的父母说9月份就要离开法国。我父母说,你9月份走,那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他们不信,说你走得那么远,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真的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很可能学一年,但两年或更长时间真的不知道。9月份过了,没有消息。10月份过了,也没有消息。最后,可能是11月初,法国外交部传来消息说,我们是11月18日出发。
巴黎第八大学(文森大学)
在此之前,大概是9月中旬。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学区给了我一封信,聘用我在中学当临时教师。法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当时在中学就已经有正规的汉语课程了。课时虽然不多,但都是正规的。欧洲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没有这样做的。所以,在这方面法国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头。我好像是在开学不久收到这个聘书的。当然,我很快就去了那个学校,但不是去上课。我很自豪地说,我是专程过来告诉你们的。我可能过了几个星期就要去中国留学了。但是,校方说没关系,你能不能现在马上开始上课?因为除了你,我们没有找其他的人。我说,那好吧。于是,在我的人生中,就有了第一次教中文的经历。我现在还保留着那个月的工资单,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使用中文去工作了,是教高中生的正规中文课程。那些高中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在高三高考的时候要考汉语,直到现在很多国家在汉语学习上也达不到这种规模。
巴黎第八大学(文森大学)
在这所中学教了两个月的中文课,我终于要去中国了。人的生日都只有一个,可我却感觉像是有两个生日。1973年11月18日是礼拜天,下午4点,我们30个法国留学生乘法国航班前往中国。这个时间。或者说北京时间11月19号晚上22点,是我第二个生日。这种感觉是我自己的,但一点也不过分。从此之后,我的一生才真正与汉语、与中国分不开了。
我们的机票是法国政府提供的。当时戴高乐机场还没建成,所以我们是在巴黎南郊的奥利国际机场起飞的。当时,法国和中国之间没有直达航线。这个航班是巴黎飞往东京的。要经停好几个地方,其中包括北京。第一个经停地是意大利的罗马,停了两个小时。然后,飞机又落在了埃及的开罗。停靠开罗机场时,我注意到机场漆成蓝色的伪装后面。有一挺警戒用的机枪。飞机在这儿也停了近两小时。第三个经停地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土地的颜色显示出这是一个平坦而又贫穷的国家。飞机最后经停的是缅甸的仰光,这里潮湿闷热。我真后悔走出舱门。在这儿也停了近两个小时。经过漫长的旅行,飞机最后终于在19号晚上的22点左右到达了北京。
在这个航班上的乘客就是我们30个法国留学生,没有其他任何游客,更没有中国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廉价的航线,又好像是试航,所以飞机在中途多次经停。在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男留学生,他的名字叫卡里诺夫斯基(Marc Kali-novski),他祖籍可能是波兰。后来,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叫马克。现在,他可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专门研究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我们坐在一起是个偶然,虽然我不相信偶然性,可是偶然还是出现了。他告诉我,他对哲学特别感兴趣。本来我们根本不认识,可是,他一看是我就问:“你不是写过一本书吗?”的确,我刚刚出版了一本跟哲学有关的小册子,书名叫《哲学与保存西红柿》,当年我才23岁。我很惊讶地问:“您怎么知道?”他说:“我读过,对它也很感兴趣。”
这本小书就是我在哲学系的硕士毕业论文。当时中国的报纸报道说,一个司机报告自己的心得,题目是“我怎么通过学了哲学,安全开了货车20年”。还有崇文区菜场里一个普通售货员说:“学了哲学,我才改进了保存西红柿的方法。”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当代哲学,副标题就是“哲学与保存西红柿”。这本书介绍了中国当代哲学和古代哲学,当时博得了法国《世界报》的好评。后来我去看一个书店老板。本来是说围棋的事情,他看我夹着一份资料,就要来看。我很不好意思,说这是我刚刚答辩的论文。他坚持要拿来看看。这又是一个偶然,他下决心出版我的论文。我不肯。觉得不是很严肃,拗不过他的诚意最终答应了。但是,我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这本《哲学与保存西红柿》。我喜欢这个标题,因为它可以让人产生那个时代的联想,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式哲学。他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若干年后,一位朋友来看我,说送我一个惊喜。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哲学与保存西红柿》已经被翻译成了西班牙文。
经过漫长的飞行,飞机终于要降落在北京机场了。当然,这是原来那个老的机场。我们当中有的人激动得不能控制自己,飞机还没落地就想站起来,想最先看看中国是什么样子。我记得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天已经黑了,但是,我还是想早点看看中国。说有点像到了月球上的那种感觉一点也不过分。所以,我对中国的初步印象是还没有落地的时候。还有10秒钟落地的时候。飞机还没落地,我发现外面的机场很暗,灯泡亮度很低。机场附近的路上也没有灯,更看不见有骑自行车的。下了飞机,我们老远就看到了一幅很大的毛泽东的画像立在那儿。在候机楼等行李的时候,我发现就在地上有一块小黑板。这块小黑板的用处或功能是什么?原来。上面写着当天的航班信息,如法航的某某航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航班。就这么一个小黑板!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很遗憾,我当时没有用照相机把它拍下来。这些就是我到北京或者说到中國后最初的印象。拿到行李出来之后,我们见到了北京语言学院派来接我们的老师。然后上了大巴车就去北京语言学院了。
几天后,我在给家里的一封航空信中写道:“亲爱的父母,我们刚到北京,旅途当中很辛苦,飞行时间22个小时,估计很快就能进城参观北京了,这里完全是乡下。这里很冷,可是天空蓝蓝的,中国人穿的衣服很合适,所有的衣服都是填了棉花的。”我想特别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北京语言学院所在的五道口是非常荒凉的。
这里要讲的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及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它还涉及如何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学习中文的动机问题。当时,不光是法国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都是有激进派的,而且有各方面的激进派。法国由于平时在许多方面就是比较激进的,所以,1968年才出现了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五月风暴,有许多罢课、罢工什么的。当时,我在高中毕业班,还没上大学。其实,大学生在这场风暴中才是最积极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游行就是在那一年。那次可能是抗议美国的游行,当时不是越南战争还在进行当中么?不管怎么说,反正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所谓的“左”派。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我们高中毕业班在1968年三四月份就开始有点所谓的“乱”。我们这个班一分为二,有两派,但其实并没有反对派。一派比较现实,说我们快要高考了,大家也不要过分地去闹,因为毕竟要参加高考,还是老老实实做准备吧。另一部分同学说,看来这个运动规模很大,有一点划时代的意义,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他们主张积极参与,高考以后再说。我就属于后一派,也就是说要参与当时的学生运动。在我看来,高考当然重要,但国家会有所调整,而运动不能错过。我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时,法国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上街游行想要干什么或者说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其实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你越过时代背景,我觉得任何国家的青年都有或者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的所谓的理想。尤其是这个年龄的人一定要有这种或那种理想,否则在他们的人生中可能缺一点东西,或者说他们的眼界不一定是足够的开放。比如说,现在西方国家虽然少了具有政治色彩的运动。可是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的激进运动还是经常发生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最激进的还是青年,而且是有一定文化的青年。所以,我说的理想就是广义上的,当时的年轻人确实有政治色彩的理想。有的是想改变所谓的生活,有的是想改变社会,有的是想反对美帝国主义。当然更多的情况是这些想法都融合交叉在一起。有的可能更特别,那就是他们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真实的,因为一般来讲他们对真实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了解。以我个人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只是抱有某种理想的,看一点毛泽东语录或者什么革命原则。有时我就在想,如果伏尔泰度过了1968年。那他肯定是亲华派。为什么?伏尔泰当然对中国的情况知道一些。可不会是一个什么汉学家。他为什么对中国那么感兴趣,是为了中国吗?不是,是为了法国。是给他的思想提供一些非常先进、非常开放的证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当时法国青年当中才有所谓的毛派,毛派就是亲华派。
现在有人攻击他们,我觉得这不太理性了。这些青年人不真正了解中国,甚至对中国根本不了解,是一种投射。可是,他们非常支持从中国过来的一些原则和一些语录。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改变法国社会,改变法国生活,可以改变什么什么等等。
到现在,很多人以为当时在大学主修中文系的学生只能是政治方面的激进派,所谓“毛派”。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来华留学的法国学生主要出于政治动机。早在几年前,经仔细的研究,我就已经意识到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一种“错觉”,可这却是非常流行的说法。这涉及如何看待60年代如1964年、1965年来中国留学的法国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再比如,像我是1969年才开始学汉语,当时五月风暴刚刚过去,中文又没有就业价值。如何看待我们学习中文的动机?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这样做只能是政治上的原因。我现在和将来都明确地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根据。不仅如此,我还会拿出相反的证据,说明主修中文学生的政治觉悟其实相对其他文科专业学生的要低得多。
我们这批法国留学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我们不是三四个人,而是30个人。我现在可以列出这30个人中大多数的名单。他们跟大部分人所想的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在这30个人中间,没有一个加入法国马列共产党、毛派组织或者其他极左组织,30个人当中没有一个真正参加了某种政党或政治组织的,一个都没有。然而,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学系、哲学系或者其他文科系,三十个学生当中说不定有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正式参加了一个极“左”组织,其他部分也可能经常是参加游行等等。可是,我们这30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是他们为什么来华留学?我可以肯定不是什么政治原因。另外,我的一些朋友在法国学生运动中是有组织的和极“左”的,但他们当中没有学中文的。不仅如此,他们知道我学中文之后,还觉得很奇怪。他们这些属于所谓毛主义的组织或其他极“左”组织的人没有学中文的,我们来华留学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参加这样组织的。其实,这些激进的学生只觉得中国好玩和奇怪,所以提倡一些同中国“文化大革命”相类似的原则,背诵毛主席语录之类。其实,他们是乌托邦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都是跟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中国古典文化等没有任何联系的。
“五月风暴”(1968年学生运动)
我们学习中文的学生则完全不同,动机是最值得研究的一个话题。我们学习中文与这些表面现象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可能要看一些内部动机的影响因素。我所说的外部因素不是指正面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可能有靠中文就业的这个外部动机,所以我们的动机只能是内在的。
那么,我们学习中文的内在动机是什么?二百多年前,著名的法兰西学院就设立了西方国家第一位汉語汉学的教授席位。出现了第一位汉学家,他的中文名字叫雷慕沙(Remusat)。雷慕沙教授的动机是什么?
1964年、1965年来华学习的法国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健在。我觉得,太值得去问他们这个问题了。可以仔细询问他们的家庭背景,小时候做什么,有没有学过别的外语,听没听过关于中国的故事等等。如果做得比较细,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内在动机可能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动机是无意识的。在1964年或1965年,中国对他们来说确实像月球一样遥远,也就是不可能去的国家。
我那时学汉语不是兴趣班,是主修。我这样做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愿意走向别人没走过的境界,追求发现探索,愿意走向远距离语言、远距离文字、远距离文化。有的与法国整个背景有关。但跟政治无关。这个背景就是汉学汉语的底蕴,汉语、汉学在法国一直就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经过最近几年的研究,我发现,在这些方面,法国一直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所以,我想知道,这个规律性的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做,我觉得才有意思。当然,这跟教育心理学有关,学习动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学术话题。对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其实我花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在我们第一批30个交换生中,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22个。现在有8个教授级的博士生导师。都是汉学家,比重相当大了。其余的统计一下,现在从事和汉语或者和中国有关的工作的,大约有7个,合起来正好是30个人的一半。他们中间有汉语老师、法中旅行社职员、研究员、书店老板等。除了前面提到的卡里诺夫斯基之外,下面我再介绍几个我印象比较深或交往比较密切的同学。
在我们同学中,有一个男生,平日一臉严肃。在语言学院学习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忽然发现他经常逃课。我好奇地问:你很长时间没来上课,是不是生病了?他说去了离语言学院不太远的圆明园。我当时并不了解什么是圆明园。那时候还没有开发旅游。他的专业是考古,经常去是因为在那里做研究。比如拓片什么的。他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集美博物馆馆长德罗士先生。因为是同辈同学,我们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我有时带学生去参观集美博物馆,常和他联系。他说:“下班的时间来,我带领你们参观。”这是大家都很梦想的参观时间。集美博物馆重修之后。就是由他带着中法领导人参观新馆的。
贝罗贝是我们那拨学生中年纪最大的,属马,当年28岁,第二年根据专业上了北大中文系。回国之后,他很快成为汉语语言的权威,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7年前继续做博导的同时,他调到法国教育部的科研部。做评估专家、国家科研中心副主任。兰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成回国以后,比我晚一点考取中文专业教师资格证,专门研究宋代淮河水利问题,也是博导。白罗(Thierry:Payrault)同学是中国经济专家。乐维(Jean:Levi)同学重新翻译过《孙子兵法》、《商鞅变法》等。勒挪(Francis RENAUD)同学在科研中心搞中国汉语语言研究,十分高深。还有三个同学也应提及。一个教对外法语专业,叫阿乐克桑德尔(YvesAlexandre)。另一个叫赫尔兹(SolangeHorz)后来成为中法很有名的旅行社——中国之家的负责人。还有一个叫欧明华(Francois Hominal)因为学的是数学。所以出了一本书——汉法双语《数学词典》,现任利氏学社社长。
于莲(Claire Julien)同学在复旦大学学中国文学,回国以后,中文水平足以考过中文专业师资合格会考。但是,她想为中法交流做些事情,很快就被聘为凤凰书店的职员。凤凰书店在巴黎很有名,主要经营中文书籍、期刊,还有中文教材。当时的书店老板是一个左翼法国人。20世纪50年代以法文专家身份在中国工作过。这个人后来写了一本《中国电影史》,很权威。
于莲后来拿到那个书店的股份,成为管理者之一。留学时代的于莲凤凰书店可圈可点,它是全欧有关中文、中国文化最大的书店,德国、英国的汉学家路过巴黎,这家书店是绝不可错过的。1979年,因为极右分子闹事,极少数的法西斯分子往书店扔了燃烧瓶。没有人死亡,但不幸的是,当时于莲正在地下室书库,她费力地爬上来,胳膊和脸都烧伤了,留下了很明显的疤痕。我去医院隔离室看望她,对于爱漂亮的女孩子来说,那次意外真是灾难。但是,她的性格很坚强,那次劫难没有让她放弃书店生涯,现在她已经是书店的老板。经常到中国,乐呵呵地给她的顾客介绍中国的_书籍。
我们这些同学,因为来中国而大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到中国来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于我个人来说,在中国的这两年,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让我的同学来回忆来中国这件事情,他们讲的都是一页值得珍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