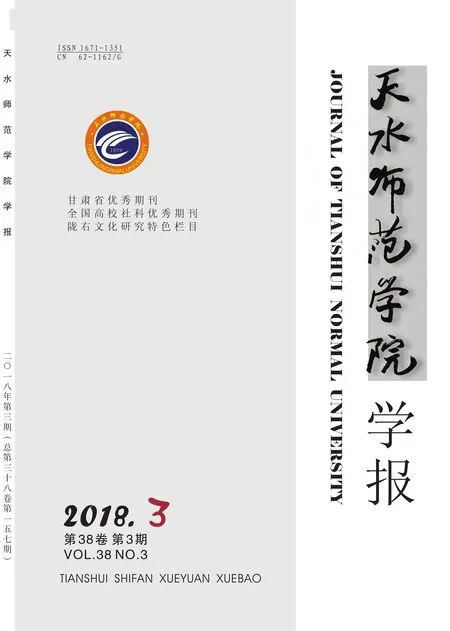白马人故事《阿尼嘎萨》中的非人形象及其意义探究
潘江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学院,甘肃 成县 742500)
白马人是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特殊民族,但在其长期生活和历史发展中流传下来的文化却异常丰富。尤其民间故事堪为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它们渗透着白马人世世代代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研究和利用它,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必定很有价值。《阿尼嘎萨》①本文所依据的故事《阿尼嘎萨》见《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14-185页)。邱雷生,蒲向明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是陇南白马人口传至今的众多民间故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在《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中为开篇之作。民间故事虽然不是历史书,口传材料在流传过程中也会掺杂一些后代的东西,甚或受某些因素影响而产生变异,但在反映本民族生存的历史时,渗透在其中的“个别”因素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据此来研究陇南白马人的文化,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这些“个别”因素会点点滴滴地、甚至以原貌的形式出现在故事中,如果综合并参考这些因素,是可以窥探到一些这个民族的文化本质的。所以,《阿尼嘎萨》是陇南白马人这个族群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它必须,也应该承载着陇南白马人的众多民族记忆因子。或者可以说,《阿尼嘎萨》不只是一个民间故事,还融会了一定文县铁楼乡白马人的历史、信仰、生产、生活、感情、文化等方面。
一般故事的典型是因其故事形象。因为随着故事的流传,群众对它不断加工,其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鲜明,并趋于定型。在民间故事中,这样的形象不但具有集体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群众的“打磨”更使其不乏艺术性。当然,在“打磨”中,有对故事中优秀因素的直接传承,也有对极个别因素做合乎审美要求的加工或变异,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并且看似矛盾的这两方面共同促成故事形象的完善。具体表现为从符合本民族的审美要求出发,使故事愈传愈完美,形象越来越突出。也由于故事艺术化的缘故,民间故事的流传形式往往兼具诗歌、散文和戏剧等艺术的传统特点,并有明显而浓厚的民族特色。口传故事者,除了口传敷演,还可能是故事的再加工者。他们不但有神奇的记忆力,同时兼有优秀的歌唱、讲述及表演能力。《阿尼嘎萨》篇幅较长,约有十来万字。故事形象有几十个,但其中的非人形象(故事中异于正常人的角色或形象)耐人寻味,文章特择其做以分析,来表达自己对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的理解。
一、《阿尼嘎萨》中的非人形象
《阿尼嘎萨》被编辑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中,它在文县铁楼乡白马人口中世辈相传,故事主人公阿尼嘎萨兼备陇南白马人思想当中勤劳、善良、勇敢的审美品质和坚韧、爽朗、智慧的民族性格。故事曲折离奇,一波三折,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创作的民间文学形式的民间故事。故事人物众多,除过群众和团体成员,掐指可算的人物有44个,其中非人形象有22个(其中一个是阿尼嘎萨的化身,严格来说是21个),现根据在故事中出场的顺序将非人形象汇总如表1.
其实,在《阿尼嘎萨》的众多人物中,像恶棍几哥比过九弟兄、恶霸七弟兄、夹石沟的铁匠扎艾哩虽以人的形象出现,但本质上都是坏人,他们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或一个阶层的恶劣者,而扎尕山的山大王色日鲁,则是阿尼嘎萨事业的支持者,属正面形象。表1中所汇总的21个非人形象,同样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但一致性是在故事中他们被塑造成动物形象或者人与动物的变异形象。它们中有些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见的动物,如青鹞、喜鹊、乌鸦等鸟类动物,青蛙等两栖动物及凶恶的狼等;有些则要么是虎,要么是蛇、花牛和野鸡等动物变异的妖怪。

表1 陇南白马人民间故事《阿尼嘎萨》中非人形象汇总表
二、非人形象的特征
《阿尼嘎萨》是白马人民间故事里头篇幅最长,人物最多,内容最复杂的一篇。故事中人物形象的非人性形象非常典型,从掐指可算的44个角色来看,其中非人形象有21个,占近乎50%,而且故事主人公也曾经历过非人形象阶段(起初是青蛙,最后变为人)。其典型性表现如下:
(一)动物化
《阿尼嘎萨》中出现的非人形象有青鹞、斑鸠、凤凰、喜鹊、乌鸦、青蛙、狼、马等动物。凡是出现在故事中的动物形象,在故事中也具有动物的行为。如鸟会飞,青蛙会跳,狼具有凶残的本性等。《阿尼嘎萨》塑造了这么多的动物形象,有没有原因呢?从《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前的概述可知,编者将《阿尼嘎萨》归在“陇南白马人神话”大类的“英雄神话”这一小类中,并说“《阿尼嘎萨》是在白马人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3既然这样,塑造形象的手法就非幻想莫属了,那么,人们在口耳相传时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尽情铺成和演绎,使这些动物形象在他们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可生出无限乐趣。回答《阿尼嘎萨》中非人形象的动物化,可以继续参考《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在概述中对“陇南白马人族源记忆与传说”大类又做“动物传说”的小类后,编者说道:“现存陇南白马人动物传说还遗留着远古观念,人和动物还没有截然分开。陇南白马人常常以自身的思想行为去揣摩动物,想象动物的生活及其性格与心理,给以人格化,形成最早的白马动物传说形态。再后来,随着白马人社会生活的发展,传说所涉及的动物范围日益扩大,尤其在更晚期形成的陇南白马故事中,动物形象常常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表现出不同历史阶段陇南白马人的动物观念和对于动物的特殊理解。”[1]8
(二)变异性
《阿尼嘎萨》中的角色,除过完完全全的人及相当一部分的动物形象,还有一部分或者人、或者动物的变异和或者人与动物的共同变异。既然是变异,所以只要细细考察,就会发现它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和动物。民间故事《阿尼嘎萨》正是通过对故事里角色的非人性变异,才导致故事曲折离奇和纷繁复杂的,读之也就有趣得多了。
具体来看,首先是由动物到人的变异。如故事主角阿尼嘎萨,就是由具有正常人身份的父母生下来的一只小青蛙(采石乃),逐渐完成蜕变的。他通过修炼,变成了白马少年,又投身从戎。当知道妻子昼什姆遭难时,曾化身喜鹊从妖魔纣娄恰尕处查看情况,并救出了自己的妻子昼什姆。后多次斩妖除魔,历经磨难,最终成为人人敬重、权高位重的白马皇帝。阿尼嘎萨起初的青蛙之身,既显示了故事的神奇性,又表达了白马人寄托在故事主角身上的诸多愿望实现前必须要冲破的一种藩篱或限制。主角冲破这个限制的过程,就是其成长的过程。就像故事中斜哦嘎萨(阿尼嘎萨)对妻子说的一番话:“从今天开始,我一天到晚修炼。我要早日脱掉身上的青蛙皮,修炼成人身,让你过上称心如意的日子,让阿爸阿妈老了有个依靠,为白马人造福,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1]108从故事的发展看,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所以,这段话可以看做故事的注脚。
其次,故事中的非人形象还有动物与动物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简单意义上两种或几种动物特征的组合,而是动物在故事中特有意义的组合。阿扎伊和茨嫚娜姆婚后多年,在极度盼儿盼女的心理下生了“一个无头无尾圆圆的肉坨”。[1]17正是这个神奇出世的“肉坨”,等到被阿扎伊用刀剖开时,“‘朴楞楞——’一对青鹞从里面飞了出来。”[1]21故事读到这,会让人想起当初茨嫚娜姆在怀孕时的那段特殊的经历,她费尽波折,生下了一对青鹞这样的“怪胎”。但“神奇出世”的高潮还没有到,直到一只“拳头般大小,翠绿的脊背,白白的肚皮,圆鼓鼓的眼睛,腮帮一鼓一鼓地喘着气,乍一看,可怜兮兮的”[1]24小青蛙从肉坨里跳出来,彼时,才达到“神奇出世”的高潮。读者也才明白:一对青鹞、一只青蛙,三个个体,类似于今天的“三胞胎”。但从故事的发展角度来看,一对青鹞所起作用相同,而且出场时间往往一致,比同同类动物的“合体”,但加上斜哦嘎洒,就是不同类动物的“合体”了。三个故事形象结合,共同铺演故事情节,为故事中心角色服务。
最后,故事角色也有人与动物的合体以及由物件到动物的变异。在故事《阿尼嘎萨》中,人与动物的合体非妖怪莫属。正因为是妖魔,其形象极尽白马人丰富的想象。仔细读来,故事中出现的妖怪有:纣娄恰尕、尼滋达、恰尕者、日叽这、介然这等。妖怪纣娄恰尕,有人的特征,也有非人的特征。正如故事所言:
这是一个离白马山寨很远很远的荒野之地,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山洞,山洞里住着一个三头六臂的妖魔,名叫纣娄恰尕。他面如黑炭,身高八尺,腰
圆膀阔,力大无穷,善于施展法术,而且有起死回生之术,即使它的肉体被剁成几截也能很快复合。[1]117
纣娄恰尕的形貌不同于人的是有“三头六臂”,跟神话里的战神差不多。另外,它会法术,有起死回生之术。但它的思维却跟人一样。第二个斜哦嘎洒与之战斗的是虎妖尼滋达:
虎妖是这一带无人不知的妖魔,眼若铜铃,吼声如雷,凶狠残暴。说它是虎,因为它是一只地地道道的老虎;说它是妖,它有七十二变,能变成石头、树木等,让人真假难辨。谁也说不清它吃掉了多少无辜的人,吃掉了多少白马山寨的牛羊,要是把尸骨收集起来,能堆成一座小山。这里四村八寨的百姓,无不谈虎色变。[1]148
虎妖如此厉害,是白马山寨人畜的公害。第三个妖怪是花牛怪恰尕者:
这个名叫“恰尕者”的妖魔,模样似牛,浑身上下一团黄、一团黑,所以人们又称它为“花牛怪”。花牛怪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专门吃人和糟蹋庄稼的恶魔,伤害无辜不计其数,糟蹋庄稼也不知有多少,令四方百姓苦不堪言。[1]154
虽然叫花牛怪,但没有一丁点儿牛的温顺。不但吃人,还糟蹋庄稼。第四个妖魔是蛇妖日叽这:
我们这里有一个金子沟,金子沟里有个蛇妖,叫日叽这,一日三餐,每顿饭都要吃一个人。蛇妖吃了好多人,我们这里的人都快逃光了。[1]158
可见,蛇妖除了吃人还是吃人,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妖魔。唯有除掉它,方能安得民心。第五个妖魔是野鸡精怪“介然这”:
这一带,有一个名叫“介然这”的野鸡精妖怪。野鸡精的嗅觉特别灵敏,十里之外都能闻到人的气息。哪里有人,它就飞到哪里,专门伤害人。野鸡精的嘴巴比鉄还要硬,专门啄食人的眼珠和脑髓,不知有多少人被它啄瞎了眼睛,有多少人被它啄食脑髓而身亡。[1]161
故事中的野鸡精怪也是害人性命,在白马人心中不除不为快。上面所述的妖怪,要么是三头六臂的人,要么直接形象就是动物,形象方面都具有非人性,但却又都有人的思维,异于常人处要么会法术,要么糟蹋庄稼或害人性命,形象上可看做是人与动物的合体,在意义上却是动物的变异。故事中还有一个情节,当阿尼嘎萨得知自己的妻子被妖魔纣娄恰尕抢走后,气愤难平,又心急火燎,拔出身上的宝刀,宝刀立马变成火焰驹。这个情节也是极有趣、又极具丰富想象力的。
三、非人形象的内涵及其意义
《阿尼嘎萨》中的非人形象的动物化较为直观,是陇南白马人农耕生活的反映;而最具变异性的“妖魔”类稍显抽象。像纣娄恰尕、尼滋达、恰尕者、日叽这、介然这等的出现,应不是偶然现象。它们的出现,一方面显示了民间故事追求浪漫主义的特色。因为故事中的妖,或者能腾云驾雾,或者善于变化,或者呼风唤雨,总之神通广大,但由于吃人、害人,与人为敌,阿尼嘎萨最终战胜并杀死了它们。这些富有浪漫主义特色的情节,在使故事曲折离奇的同时,完成了故事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也表达了正义战胜了邪恶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根据年轻学者杨永刚先生“在调查中发现白马人社会文化受附近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从语言、服饰、饮食习俗、民居建筑、日常交通、婚丧习俗、宗教和传统节日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些影响”[2]的观点,说明白马文化对周边文化,尤其是汉文化有借鉴和汲取。众所周知,我国的神话,从上古神话到《山海经》及一些散见于古代典籍中的神话开始,再到魏晋干宝的《搜神记》,唐代传奇,明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经由这些发展,神话故事的角色塑造及情节提炼,已相当成熟。尤其《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之后,更是涌现了许多神魔演义或神魔影视作品。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阿尼嘎萨》中妖魔形象跟近现代神魔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的妖魔如出一辙。另外,《阿尼嘎萨》的主要情节“进宫求婚”符合陇南师专唐海红和蒲向明合著论文《藏彝走廊“青蛙娶妻”型故事的情节生成和文化意义》的观点:“以其长篇口传故事《阿尼嘎萨》为代表的‘青蛙娶妻’型故事,是藏彝走廊多民族‘青蛙娶妻’型故事情节生成的典型,属于情节有趣而又极具幻想的神异口传文学之一。通过对比白马藏族、彝族、羌族、傈僳族、白族、仡佬族、纳西族、哈尼族、景颇族、苗族、畲族、普米族等部族‘青蛙娶妻’型故事情节生成方式的异同,可以看出,藏彝走廊多民族该型故事的形成与流播与各自族民的生活习性、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及文化心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152这些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也确实如此,《阿尼嘎萨》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白马人民间故事的脚本,记录和反映了许许多多文县白马人自身的文化要素。
(一)《阿尼嘎萨》中非人形象的塑造建立在文县白马人泛神意识的自然崇拜基础上,是文县白马人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低级的农耕生活水平、以及与之相应思想观念的客观反映
首先是故事中的动物,有青蛙、青鹞、凤凰、斑鸠、喜鹊、乌鸦、狼等。故事中的这些动物形象的出现,比较直观地描画了在故事产生的艰苦而特殊的环境中白马人对存在的这些动物的认同。文县白马人在最初或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生活与这些动物息息相关,他们从自身生活的目的出发来认同他们与这些动物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在他们的故事中反映出来了。如狼对他们的正常生活有干扰,并会对他们造成伤害,故事中就有七八只恶狼要吃砍柴的白马少年的情节。[1]160青蛙形象,是故事中最精心塑造的一个形象,也是《阿尼嘎萨》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形象。故事把青蛙当做主要角色,一是青蛙和青鹞、斑鸠及喜鹊一样,生活在山林地带,并且是白马人最常见的,也是白马人比较喜爱的动物;另外一个方面,因为青蛙是两栖类,它本身也是由卵经由蝌蚪再到青蛙的。它的多变性寄予主人公既磨难多多,又不断变化、成长的生活经历。《阿尼嘎萨》的主人公以蛙的形象出现,表明其是一部蛙崇拜意识下的蛙神话。这在我国山西大同和广西某些地方是比较突出的现象。还有鸟类形象。鸟类是一般神话里出现比较多的。白马人民间故事《阿尼嘎萨》应该是继承了这一点,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鸟类形象。鸟能飞,就可以让它做信使(如一对青鹞),又能啄,就让它们帮斜哦嘎萨去杀妖魔纣娄恰尕(如喜鹊和乌鸦)。能飞和能啄,这是鸟的特性,关键是鸟能飞始终使人类对鸟的怀有一种憧憬。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鸟类就是速度的代名词。青蛙、鸟这些形象在故事中的出场,及它们辅助完成的情节,反映出陇南文县白马人对这些动物的情感,也反映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是在深山老林中、时常与动物为伍的环境,生活水平极低、生存条件相当艰苦的。鸟形象中的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在故事中因为主人公追求三对宝翎而使之它成为一个焦点。最后自愿为主人公献出自己的宝翎,成全了主人公的美好愿望。这一系列的情节,使凤凰的形象高尚而伟大,也反映了白马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上面所列举的形象,虽然是白马人幻想所成,但不是毫无依据、十分荒唐的,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客观现实和生活斗争的反映。就如学者权新宇所言:“自然为人们的崇拜提供载体,即崇拜的对象,而且崇拜对象必须是能够满足造神者实际生存需要的某一自然物。”[4]如果这样理解,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故事主人公斜哦嘎萨由一只青蛙,经过修炼变成白马少年,充军回来后,为民除掉妖怪纣娄恰尕,因功勋卓著,经过白马皇帝的亲自问询就被推选为自己的继承人
按故事中白马皇帝的理解,新继承人应“不仅要有智慧,武艺高强,而且还要有学问,应该是一个全才”。[1]137斜哦嘎洒满足这个十分苛刻的条件,并且胜出了白马皇帝的诸种考验,于是择佳期正式继承皇位,称为“阿尼嘎萨”。这种由动物到人,最终回归到人的种种波折和磨难,预示着努力后的成功,“修成正果”式的结局及故事中妖魔等非人形象的出现,使故事具有神秘感,泛着浓浓的浪漫主义色彩。当然,民间故事对阿尼嘎萨的塑造,不仅借助了浪漫手法,更多的是依赖白马人的生活背景来突出故事形象的。坐上皇帝宝座的阿尼嘎萨,没有去享受,而是依然为自己民族的生活和发展着想。斩妖除魔,铲除恶霸,他冲在最前端;为人民找寻小麦和玉米良种,教民稼穑,研制出了新犁铧、连枷,并建石磨坊,造沓板房,尝百草找灵药,教酿蜂汤酒,……真是为民造福无穷。阿尼嘎萨对白马人功德无量,那么,“阿尼嘎萨也就成为白马人模仿和崇拜的偶像”。[5]所以,从故事的教育性这个角度来看,《阿尼嘎萨》也是成功的。它的成功是白马人共同创造的,是白马民族智慧的结晶。阿尼嘎萨不仅能斩妖除魔,还会唱歌、跳舞,白马人会的,他都会,他的本领超越了所有白马少年。正如白马文化学者蒲向明教授认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流传与歌诗歌舞群欢活动密切相关。”[6]现实中的白马人能歌善舞,喜欢群欢活动,群众文化生活活跃,因此,故事以生活为背景塑造的阿尼嘎萨,不只威武,而且细腻温暖。是一代又一代白马少年追慕、学习的对象。同时,故事所宣扬的以及阿尼嘎萨身上具有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以及对现实的积极态度,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不断激励和鼓舞着白马人。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进步的世界观。在这种观念上塑造的人物,因其进步,因而成功。
四、结 语
陇南白马人民间故事《阿尼嘎萨》塑造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其中非人形象占近乎所有形象的一半。这些非人形象或者是动物,或者是妖精,或者是人与动物的共同变异。形象外貌各有不同,本事和能力各有特点,但却都有人的语言和思维。准确地说,这些形象是一群能说人话的动物和怪物,是陇南白马人通过幻想而成的智慧成果。它们在故事中的出现,和一般故事中的人物一样,起着铺陈故事情节和渲染气氛的作用。但如果结合具体文本,参考民族文化去反复推敲,就会获得不一般的认识。这些非人形象记录和反映了许许多多文县白马人自身的文化要素,是文县白马人在泛神意识的自然崇拜基础上创造的,它们是族民们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下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与之相应的观念的客观反映。故事中动物和妖魔等非人形象的出现,使故事具有神秘感,更泛着浓浓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一代又一代白马人共同的“打磨”中,故事把族民们的对生产及生活的智慧,总结并蕴蓄在阿尼嘎萨一个人身上。“这些作品寄寓了陇南白马藏族人民的思想观念、道德诉求以及伦理考量,并艺术地传递出了他们对“正义”社会、和谐社会的向往和渴求。”[7]而此故事本身,“(它们)表达了这一区域多民族社区族民对生命延续的企盼,呈现出该区域稻作文化及民俗风情的生活态势,是人们对生殖崇拜、图腾崇拜、英雄崇拜的反映。”[3]150所以,在阿尼嘎萨身上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以及对现实的积极态度,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将会一直不断地激励和鼓舞着白马人。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进步的世界观,也是值得肯定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