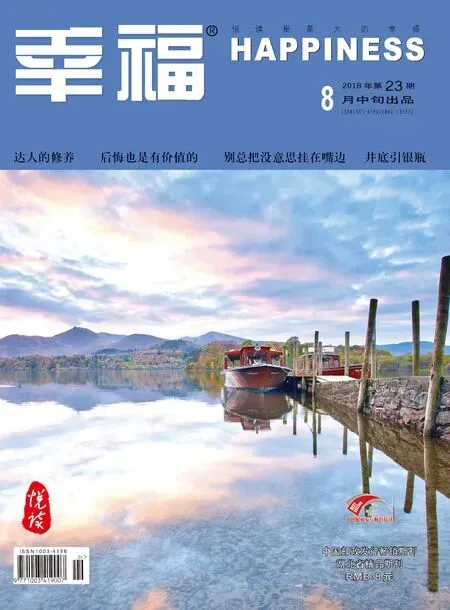走近东坡赤壁
文/日与月
长江边的黄州城里有一座东坡赤壁,从古至今,气势磅礴,如大江东去,永远翻腾着北宋历史上无法割舍的一个片断。
《史记·货殖列传》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司马迁并没有言中身后的苏东坡。苏东坡因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端,又以诗为载体讽刺新法下狱,被贬湖北黄州。正值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日,苏东坡凄苦地告别了汴京,向黄州走去。沿途,却有武侠打扮的隐人陈造、陈季常等,杀鸡宰鹅,设酒宴款待他。主客之间没有各怀利胎,相反,却有一种坦诚的默契。
我以为,苏东坡不应该承担众口一词的不幸,而恰恰应该回味别人给他带来的幸运。试想,倘曹太皇太后和若干大臣如已经退职的前宰相张方平、退职户部侍郎范缜,以及变法首领王安石和他的弟弟王安礼等人,听任御史台的何正臣上书神宗,弹劾苏东坡,恐怕苏东坡的历史就会从此中断了。苏东坡是很有气魄的,因为他曾力陈仕途正火的王安石新法之弊端,好似吃了豹子的胆;王安石也是很有气魄的,因为他对政见不同者也保持了宽容,而且,出面营救了苏东坡。太柔太优雅太大度太和谐的,恰恰使苏东坡的生命产生了一种饱满的力度。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接近东坡赤壁,便是感受北宋一段曲折而又风雨的历史。古人尚且能以不朽的山一般的骨架构筑人生,那么,今人呢?
黄州东坡赤壁有一组阁倚山而筑。细细四望树掩下的建筑群体,我便生出了一种叹喟:这些楼台亭阁之所以耸立于游人经久不息的仰望之中,是因为它建筑于真情实意的土地与根基之中。
在那长达四年之久的贬居黄州的放浪生活中,并不苍老的苏东坡持何种心态?苏东坡只会弄出汪洋恣肆、畅达明白的文学来,比如,《密州出猎》、《赤壁怀古》,但他缺乏政治权术。他并不想献身于皇冠的争夺,却被功名荣辱以外的直谏所累。
最是与酹江亭相邻的坡仙亭令人思索了。草书书写的《念奴娇》气势飞动,奇功潇洒,仿佛能力破壁背。也许,苏东坡来到黄州,无论出于何等的无奈,都是为了醉草一回。其手迹,我觉得,已得真悟。雨水把阳光挡了回去,亭内的光线暗淡了许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把自己与周围融为一体,才能触摸到苏东坡当时的心情。我不愿意用手去碰它,愿意用心,或用情去体验它,感受它。结果,我离北宋很遥远,却离苏东坡很近。苏东坡存在于我的故乡之中。

苏东坡秉烛观海棠,寄逸兴于花间;或步月赋孤鸿,泻幽怨于词行;或倚杖野游,倦眠溪桥。耕东坡,绘雪堂,泛舟赤壁……苏东坡眼望东去的大江,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踏木屐的村夫,或野老之形象,被《东坡笠屐图》展现得惟妙惟肖,可谓“须眉活现,工妙绝伦”。
苏东坡有才,才会被贬到黄州。苏东坡又因有才,才会被奉调离开黄州。黄州的出名与苏东坡有关。如果苏东坡没有贬到黄州,他能产生年岁渐老,功名事业远没有成就的体验吗?他能借周瑜在赤壁之战建立大功的事迹以勃发自己的情怀吗?大概,中国的文学史上就没有了风格豪放的“大江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