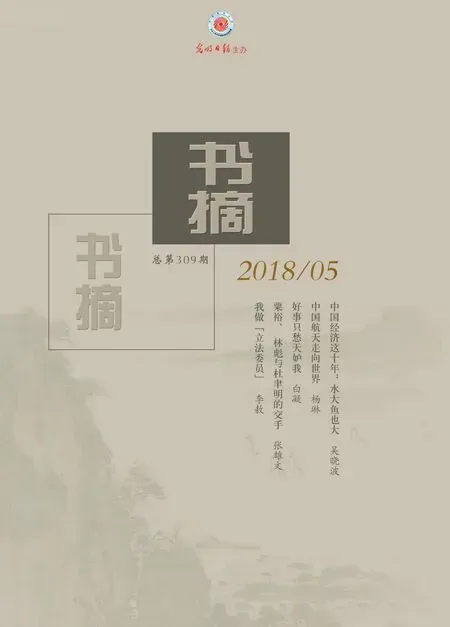画坛轶趣
☉周昌谷
陈继生掮古董
(上世纪)50年代外西湖18号国立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一般古董掮客,就简称为“华东里”。那时学院有个研究室,潘天寿先生被老区来的革命领导看做“封建画家”,不能上课,他每天来研究室上班,其实他的工作就只是收买掮客送来的古董字画。吴茀之先生记账,诸乐三先生一度被贬,到教务处抄布告。这一段时间,就是所谓对待国画虚无主义的路线(现在看来就是极左路线)。
陈继生是一个矮小的老头,留着两撇胡子,穿着蓝布长袍,活像一个戏台上的丑角、群英会上盗书的蒋干,来时必有一个蓝布包,包内或是古董,或是古画。那时古画瓷器不值钱,学校里的藏品,大部分是他掮来的。一张吴昌硕小中堂只卖八元,不少老师私人也有以三五元买件瓷器玩的,有一些现在已经值到数千元数万元的了。我那时是研究生,更穷,只能以五角钱向他买一个破掉的宋龙泉双鱼小盆玩玩。从学校现在富有的国画藏品看,陈继生还是一个有功的人呢。可惜在“文革”中研究室放在外宾接待室的古玩散失了。有一次他拿来一幅王蒙的山水,要价90元,在当时说已是一个大数目,而是否元画也不能确定,于是拿给住在栖霞岭的黄宾虹先生看。黄先生说:“画虽不能肯定,但画得很好,如学校不收,我收了。”这样研究室才郑重讨论通过,向学校申请较大款子买下了。又有一次他拿来春宫册页,说是技巧很好,潘先生看也不屑一看,就叫他拿回去了。当时收藏画的还有文管会,别的就没有单位了。一次有一张八尺中堂八大山人的老鹰,没人要,他放在茶店门口(茶店是书画古董交易的早市),被余任天先生看到,问他多少钱。他说,文管会不要,华东里去了两次,第二次吴先生说:“伪的,五角也不要!”“你卖多少?”“给三元罢!”“好!给你五元。”这张八大山人的鹰,后来我曾见到,是真的,60年代被人以800元购去,现在八尺中堂价就要在3万元以上了。
反右后期,学校搬到南山路,陈陇做了副院长,他似乎革命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不认识的人很可能是特务。他看到陈继生,问他是何许人,为什么在学校到处钻。想不到陈继生不客气地回敬他说:“我这种人,还不好找哩!”陈陇火了,一次在大会作报告,责备传达室门禁不严,让一个像特务的小老头自由地进进出出,可能窃取了学校的机密情报(?),该谁负责?自此之后,陈继生就不来华东里了。
“小扬州”吃画
解放战争前后,杭州的裱画生意是很萧条的。资本家也不拿书画装门面了,一般的人又裱不起画,艺专的学生也没有钱。只有几个书画爱好者和国画教授们,才裱几张。杭州的裱画铺,我去过的有四家。开设在岳王路的“聚珍斋”,我接触最多。主人是外号“小扬州”的陈雁宾师傅。“小扬州”的外号,据说是因他的技艺得他师傅“老扬州”真传而得名的。那时大家几乎一律地称他为“小扬州”,有时就直呼为“扬州”,陈师傅还点头哈腰说“是、是”。

两个羔羊 周昌谷 作 1954年中国美术馆藏
那时裱画生意萧条得可以,有时真到了没有夜饭米的程度。这时陈师傅除兼做点古董掮客生意之外,就到栖霞岭黄宾虹先生家去要画,回来时艺专宿舍苏白公祠是必经之途,就来找我或别的青年教员。我是1953年毕业,下半年开始有饭钱以外的钱可以买几张画。黄宾虹先生在世,许多人都去讨,黄老又是有求必应的,但我不愿去讨,对黄老和他的艺术尊重,不敢开口。这时画很便宜,小立轴只要五元一幅,册页一二元一幅。当“扬州”或沈志明、陈继生拿来时,我总不愿还价,我立轴给他12元,册页3元。他们回去后总说我的价给得最高,是个“大好佬”。我很爱这顶高帽子,后来着实地又做了几回“大好佬”。那幅12元买的立轴1957年裱好后请潘老题过,潘老题曰:“宾虹先生山水,由清溪石溪筑基,上追北苑南宫,长于运水用墨,真可谓得元气淋漓障犹湿者,此帧证之,寿题。”这幅画在黄老画中只能算中等,但经潘老一题,我更宝贵了,后抄家抄去,几经沧桑,又还到我手,现在还宝藏在我处。12元购的册页四幅,1956年黄胄来信要宾老的画,我送了他二幅。
1953年李可染先生来杭州写生,住在艺专。我喜欢他画的牛,又不好意思开口,韩光复说李可染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与他很谈得来,并为我要了一幅,后来将李先生试纸的一幅赠他的山水,也给了我,并带我去谢了李先生。这两幅画我都请“小扬州”陈师傅为我裱了。牛画方形,有上款,裱成立轴,山水是横长的,裱了个硬片。画就放在进修室的抽斗内。我们一行7人,动身到敦煌考察去了。回来之后,因北边天窗漏雨,画上有了一圈圈的水迹,于是要请陈师傅挖补。陈师博将李画重裱,挖去水迹,一点也看不出,我很佩服他的技巧。
李可染先生的那幅试笔山水,是不可多得的特别的画,因为试笔,他随意画了一些树木房子,土坡前是水,水上边有帆船,是随意点染的,一反常态是潇洒的白的山水,不是他一般厚重的黑的山水,笔墨很有趣味。他上边题着杜少陵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可染试纸,乱涂如此。”此画后来在“文革”中被抄,他日有人见画又见此文者,就知道原来是我的藏画了。
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冬天,刮着朔风,小宋和我偶然走过井亭桥,我们看见靠太平洋电影院的河边坚立的高大的广告牌上,“小扬州”和沈志明在高高的梯上贴电影海报。一个裱画名手,一个修理古画的名医,为了生活竟是什么活都干了,不禁恻然,很想慰劳他们一下。我知道他爱喝白酒,就走到对面一家糖果店里,买了一瓶西凤酒。杭州的店没有茅台酒和五粮液,西凤就算度数极高的名酒了。我们将酒放在竹梯脚下浆糊桶的边上盛工具刷子的篮子内,并向在高高梯上与朔风奋战的“扬州”师傅打了个招呼,指指篮子,走了。几天之后,见到沈志明,他说:“那天晚上,我与‘扬州’也横竖横了,本来是烧酒豆腐干的,今天西凤酒,索性就白斩鸡了,好一夜大醉!”
60年代他进了书画社之后生活就稳定下来。70年代他的子女结婚,我都送画祝贺。我说,要是你从黄宾虹赠画开始,潘天寿、吴茀之……直到现在,都不吃掉,你可能是一个藏画名家了。他说:“还是吃掉好,吃掉就没有事了。”
——早期北平艺专的国画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