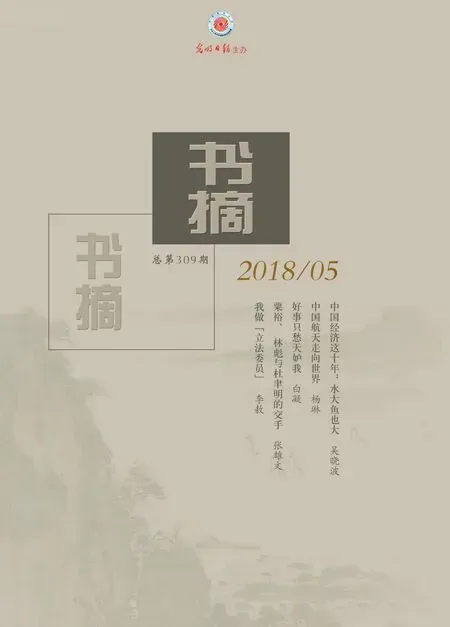农民去当兵
☉黄健 编著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旧时农村老人这样讲。解放以后,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人们的观念变了。每年冬季,欢送胸戴大红花的农村青年当兵去,每年春节,敲锣打鼓慰问军属,送春联,门楣上贴“光荣人家”。农村人参军入伍,既是为支持国防建设尽义务,也是锻炼成长、跳出农门的重要路径。
当了四年副排长
讲述:李宝贤
1956年2月16日,大年初三,我到部队去当兵。我走之后,家里没人,衣服、被子、鞋子、粮食什么的,只要弟弟需要,全部给他,锁门就走。
记得与永根一起,乘轮船到县城,先集中培训一个多月。然后再乘轮船,夜里换火车,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好像火车原来是运马的,车厢里一股马粪味。我们穿着新军装,被子铺在稻草上睡觉。车停下来是晚上,出来一看是杭州,两人真高兴。新兵中队驻在钱塘江大桥北桥头堡边的红洋瓦房子里,六和塔下面,在那儿又训练一个月。
我们属于防空军,黄军装,蓝裤子,下连后与永根分开。我在苋桥机场守卫,三营七连,配37高炮,守卫机场。他在二营五连,重炮,保卫大桥。过了一个多月,派我去教导队学习,8个月后回来当班长,也就是炮长。一个班一门炮7个炮手,一炮手负责方向,二炮手负责高低,三炮手负责航向,四炮手负责速度,五炮手压弹,一梭子五发,六、七炮手运输炮弹,自动瞄准。我训练中打靶成绩好,立过两次三等功。班长当了一年多,第三年当副排长,入党。副排长一当四年,直到退伍回来。
服役期间我回乡探亲一次,家里什么也没有,东西都入社了,折价三十几元钱,大队书记交给我。当时部队准备让我提干,照片都送上去了。他们来家乡调查,知道这事后,说我私心杂念重,怎么好拿这三十几元钱。当兵第六年底,教导员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我决定回乡,当兵不能当一辈子,迟早要走,不如早走。
1961年国庆过后回来,旧棉袄换了新棉袄。从列兵、上等兵到上士,三颗星我戴了好几年,最后一个月拿到36元,退伍费80元。团里三卡车退伍兵,一起送回县城。其他人走了,我与永根不走,因为临别时团政治部给我们开过一张证明,希望地方照顾,安排工作。兵役局一个同志是独臂,问我们为什么不走,我们说没有家。他说,怎么没有家?人民公社就是你们的家。看了部队那张条子以后,他说,那好,你们到农场去。我们俩商量,到农场还是种田,我们忠厚,容易被人欺,不能去,还不如回家。实际上当时应该去农场,因为农场拿工资不拿工分,我们去不一定下田种地,最起码管管仓库,这一招是失策的。
我在部队回家探亲时,大队支书介绍一个对象,附近地方人,见了一面,双方觉得不错。后来我们部队机动在苏北,她与姑姑一起来部队探亲。路费自理,吃饭免费,回来时可能是我买的票,记不清了。当时只说我会提干的,没想到退伍。刚回家那阵,她似乎有点情绪,不太搭理我。
我说没有关系,有什么直说,我不勉强你。她又说不出口,因为大队书记做的介绍。元旦结婚,实在困难,我通知娘舅来喝喜酒,还叫他带半斤米来,家里没有粮食啊。我家原来两间朝南屋、两间侧厢屋,因为当兵的缘故,1958年没拆掉,早已东倒西歪,墙头快倒了。
在部队的日子里
讲述:夏建
跟师傅做了两年篾匠,自觉前途无望,却又不肯死心,总想出去闯闯,不要一辈子窝在家里。1971年底因林彪事件没征兵,1972年底兵征得多,就想去当兵,多个机会,大不了几年回来,也算见过世面。
体检前让大队赤脚医生查体,说我心间杂音两到三级,体检通过有难度。头几天,其他公社的人先体检,身体合格率低。以往体检不合格卡下来的人,大多是肝下垂,据说是挑重担压的。我们那一年体检,心间杂音特别多,10个人中8个人有问题,照头几天体检情况,根本招不到预定数量的兵。晚上领导讨论,决定放宽标准,心间杂音两级就算合格。这些都是大队赤脚医生后来告诉我们的。接下来我们体检,大队里去12人,合格10人,最后入伍的8人,人数之多,史无前例。傍晚6点,天黑透了,听说体检合格,高兴得跳起来,几个人连夜从县城往家赶,十几公里路,走了两个多小时。
12月20日离家集中,当晚换军装,里外一身新,兴奋得很,说将来当新郎也不过如此。当晚写“诗”一首:激动得心咚咚跳,犹如擂战鼓,快马加鞭催征急,顿生双翅飞向前。至于到哪儿当兵,当什么兵,吃多少苦,全然不顾,就像脱笼之鸟,即将飞向无垠的天空。当晚发津贴费,每人五元,一张整票。第二天父母到码头送行,我根本感觉不到他们的担心,撩起棉衣,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钱来,告诉他们,发工资了!
刚到部队,什么都新鲜。班长说,新兵连艰苦,下连后有生产地,伙食会好些。我们说,一天三顿大米饭,还要什么菜不菜?在家一年到头吃粥,现在吃饱肚子,知足了。确实,只有到了部队,才真正吃饱肚子。一个人一顿吃十几个包子,一两多一个,满满一脸盆,装得高高的,风卷残云,瞬间一扫光,那叫一个痛快。
我们班有两个安徽新兵,一个宣城的,一个贵池的,两人一字不识,名字不会写。晚上站岗,让他去看钟,时间到了好换岗。他回来说,快到了,快到了。问他几点几分,他说一个针在5字边上,一个针在6字边上,算几点钟?他们在家从来没有见过钟,也不识得钟。班里还有两个71年安徽兵,一个休宁的,一个太平的。时间久了聊起来,才知道四个安徽兵全是孤儿,父母亲都在1960年饿死了。当时感叹,江苏苦,安徽更苦,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我们部队是海岛守备连,我当了一年新兵、三年文书、二年班长。步兵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只有平时不怕苦,战时才能不怕死。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一件是当兵第一年冬,到守备区参加教导队集训。正好海岛第一场寒潮来袭,北风呼呼,训练科目是队列基础动作,立正、稍息、停止间转法。教员边讲动作要领边示范,学员列队一动不动,脸、耳朵、手、脚都冻麻木了。没过几分钟,队列里三晃两晃,昏倒一个,又昏倒一个,接连倒下三四个。区队长一看不好,收队回营,改科目,练刺杀,一般直刺30下就大汗淋漓。刺杀前先抛枪,端起枪来,摆好架子,刺出去才有力量。练了没几下,又出问题了,抛枪时机柄刮在手上,皮肤冻脆了,一刮一层皮,不觉得痛,血慢慢往外流,枪托上红红的,好几个学员都是这种情况。刺杀也不搞了,大家绕着操场跑步。
再一件事是1978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天气最热的时候,营里组织军事竞赛,5000米越野,全副武装,各连三班参加。所谓全副武装,就是枪、子弹袋、铁锹、水壶、挎包、手榴弹、背包、雨衣、军鞋、武装带,10样东西,二十来斤。东西不算重,就是带子多,勒在胸前,透不过气来,勒得不紧,跑起来叮叮当当,既暴露目标,也影响速度。我们班10个兵,预先试过,了解每个人体能强弱,有协同方案,体力好的给体力弱的背枪。我跑在前面,压住速度,保持匀速与节奏;副班长在最后,不让队伍拉得太长。按照规定,比赛成绩以最后一名战士过线为准,终点前300米每个人的枪必须自己扛。最担心一个76年武义兵,腿很长,体质弱,平时走路就是一跷一跷的。上午9点,我们班第一个跑,烈日高照,热得不得了。跑了不到5分钟,肠胃反应强烈,早晨吃的东西全部吐掉。300米后,按赛前预案,武义兵的枪副班长接过去。我回头看,个个大汗淋漓,喘息不止,队形保持还好。再后来,脑子木了,机械地跑,经过什么地方,边上有什么人,不知道,只是不停地跑。终点前300米,听后面武义兵说“枪、枪”,他还记着要背枪。回头一看,他脸色通红,满嘴白沫,眼睛半张半闭。离终点不到五十多米,武义兵终于瘫倒,两个战士不由分说,一人一只手,拖起来就跑。一直到终点,全班人瘫倒在地,动弹不得,时间不到21分钟。其他连队的三班一看我们跑成这个熊样,都有点胆寒,而且越往后天气越热,最后我们跑了第一名。武义兵抬回营房,大腿外侧全被公路上的沙子擦破了,在地铺上滚来滚去,直说肚子疼,卫生员束手无策。他边呻吟边呕吐,吐出来的尽是黑的,想想又没有吃过黑颜色的食品。后来衣服泡在盆里,一盆红水,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那是典型的胃出血。缙云兵在床上躺了五六天,慢慢恢复,1979年春上前线,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
文书保管全连战士的档案,这才知道档案材料的厉害。卫生员是上海兵,会画画,人机灵,营长喜欢他,想提拔他,一翻档案,说妈妈解放前拜过“老头子”,算政治历史不清白,没办法,只好让他转业。一个同乡档案里,说他姐姐与劳改释放分子有生活作风问题,八竿子打不着。他是高中生,工作积极,军事技术好,当副班长,正在争取入党,突然叫他退伍,做梦没想到。指导员也是为他着想,多干几年,入不了党,不如早点走。一个75年兵,宝应人,档案袋里一张小纸条,铅笔写的,“××当兵,请关照”,对这个兵也有影响,怀疑他走后门,当时正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啊。一个76年安徽岳西兵,档案袋比别人厚得多,他高一就写入党申请书,七八份,统统装在档案袋里。几个人私下议论:这个兵入党动机不纯,名利思想重,大家不怎么看好他。不过,他十分努力,机会也好,上军校,最后官至政治学院副政委,少将,终成正果,是老连队在部队职务最高的人。
那时当兵,干部战士文化普遍不高,我会写写弄弄,领导还算器重,当兵第一年秋就去家乡外调,列为干部苗子。第二年调到连部当文书。文书是连队小秀才,主要四项工作:一是管理连部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电话员。以上“四员”,加上军械员、给养员、饲养员、炊事员,统称连队“八大员”。二是每周拟军训计划,上报营部,下发班排,起草连队各项总结、小结、动员、报告等。三是出黑板报、墙报,重大节日出专栏,制作幻灯片、写幻灯稿,教唱歌,编节目,参加会演。四是管理兵器库,防止枪支生锈、弹药受潮,定期清点,不准流失。
当文书与连长、指导员住在一起,一个桌子吃饭,星期天下棋打牌,混得熟。入伍第三年连队上山打坑道,空压机带动风钻,钻孔后装火药,洞口黄泥堵实,雷管引爆,炸后排险,然后把石头运到坑道外,安全隐患多,劳动强度大。为了抢时间、抢进度,官兵三班倒。我上半夜出墙报、烧开水,下半夜跟他们一起干,一个月下来,发烧不止,吃病号饭,粥里放两匙白糖,不久就入党。各种教导队、集训队都去过,军械管理、战术、队列、学理论等,每年一到两次,短则一周,长则三个月。最后一次教导队是培训参谋业务,学员大多是连排干部,只有三个战士支委。有人说集训一结束,我们会到作训科当参谋,集训完了仍旧回连队,此后再无消息。
1977年冬,部队野营拉练住坑道。我从报纸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连夜写信回家,要哥哥弟弟一定报名参加高考,邓小平给了我们高考的资格,考得上考不上都要去。不久,连队给战士摸底测验,准备补习文化。有个数学题目,l/4+l/3,有战士答 2/7,我跟副指导员阅卷,哈哈大笑。这个答案错的,如何计算?怎样才对?其实一时间我也愣住了。晚上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好不容易回忆起小学老师上分数课的情景:一个圆分几块,像剖西瓜一样……
就这样,真分数、假分数、带分数,分数的加减乘除,慢慢回忆出来。从1966年学校停课,到1977年底,十多年时间没摸书本,原来学的东西,差不多全部还给老师啦。

再一晃,就是1978年,当兵第六年,26虚岁。夏天,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对我说,“你提干的事,我们向上面报过几次,开始时没位置,现在年龄超过,提不起来了。如果你想继续留下来当兵,只要我在一天,你就留一天”。他见我没说话,停顿了一下,又说,“还有,回去考大学怎么样?可以试试”。这些事我都想过,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农村情况没有多大改变,回去有什么意思?连分数的加减法都忘记了,怎能考得上大学?先留下,等等再说。
国庆节放假,我到连部看报纸,《浙江日报》登载一条消息,报道1978年浙江高考文科、理科录取情况。我只知道考大学,哪懂什么文科理科、大学大专,立即拿着报纸去问指导员。他是66届高中毕业生,告诉我文科考五门: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恢复高考时英语不考。我听了大吃一惊,当年浙江文科录取分数线300分,平均每门60分,只要及格就能上大学,简直不可思议。我虽然没有好好读过中学,但自我衡量,在部队几年,语文、政治比一般学生强,历史、地理无非把整本书背出来,差不到哪里去,只有数学弱些,四门拉一门,总归可以的。
报纸上的这条消息,极其偶然地看到,重新燃起我心中的希望之火。那年冬天,到师部军人服务社买东西,喇叭里正在播放召开中央全会的消息,邓小平、陈云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隐隐约约感到,世道要变了。1979年2月底,我结束了六年三个月的部队生活,回到家乡,准备高考,实现多年来的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