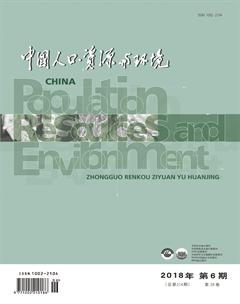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
蔡海亚 徐盈之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互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打造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显示: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存在明显的改善作用;在剔除了加工贸易后,贸易开放对改善雾霾污染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协同集聚与贸易开放交叉项对雾霾污染存在负向影响,即贸易开放通过提高协同集聚水平从而间接地制约了集聚负外部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贸易开放与协同集聚存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在初期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变得显著;贸易开放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因两者发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贸易开放下,协同集聚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雾霾污染问题,需要秉持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与渗透,破除产业发展中的棘轮效应;调整粗放型的外貿增长方式,推动外贸由规模型扩张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引领贸易结构走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路线;破除贸易开放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门槛效应,实现两者的匹配发展。
关键词 贸易开放;雾霾污染;门槛效应;产业协同;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 X5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6-0093-10DOI:10.12062/cpre.20180118
自推行市场改革与对外开放并举的体制改革以来,贸易开放释放的政策红利为地区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短期内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集聚,集聚经济产生的规模和技术溢出效应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然而,在以粗放型经济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下,空前开放的对外贸易以及产业大规模扩张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使得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愈发严重,尤其雾霾污染物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上空肆意频发,而这些地区又偏偏是产业最密集、贸易开放相对较高的场所。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阶段性的新特征,产业集聚并非是单一产业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汇聚,而是伴随着相关产业的协同集聚,尤为突出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的地区其制造业也较为发达。近年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若干意见》《中国制造2025》,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和各种外溢效应,有利于企业集中生产、治污、经营以及对环境的集中消耗,因此,产业协同集聚亦可能具有环境正外部性。显然,协同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内在关系有待检验。
1 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已有部分学者剖析了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但研究维度基本为两两关系分析在贸易开放与产业集聚关系方面,主要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方面认为贸易开放推动了产业集聚的形成,如Yamashita等[1]认为产业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指出外商投资的增加也加剧了相关产业的集聚。徐维祥等[2]的研究显示产业集群创新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外商投资有助于提升产业集群创新。Shao等[3]研究结果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服务业集聚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另一方面认为产业集聚提升了贸易开放水平,如Hilber[4]以罗马尼亚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工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能够对FDI流入产生吸引作用。李胜兰等[5]探究了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倒U型关系。Ning等[6]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的内在联系,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取决于城市内外产业集聚的强度。Simone等[7]分析了2001—2011年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发现集聚经济对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在贸易开放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面,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研究结论有较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贸易开放改善了环境污染,如Mcausland等[8]发现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产生的环境效应截然不同,前者对环境污染存在积极作用,而后者对环境污染存在负面作用。Almulali等[9]认为从长远来看,贸易开放有利于欧洲减少CO2的排放量。代丽华等[10]实证得出提高贸易开放度可以降低中国环境污染,对缓解中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作用更为显著。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贸易开放加剧了环境污染,如Baek等[11]研究发现虽然自由贸易可以改善发达国家的大气质量,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大气质量却存在消极影响。Dietzenbacher等[12]研究发现中国加工出口贸易每增加一美元收入要比正常出口贸易多排放约34%的CO2。
在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面,学术界的研究结论还未达成共识,部分学者认为产业集聚恶化了环境质量,如Ottaviano等[13]指出在技术瓶颈难以突破的情形下,产业的过度集聚非但不能改善环境质量,反而会恶化环境质量,增加环境治理成本。Ren等[14]以上海市为例,研究指出产业集聚加剧了土地资源的开发,对水体质量产生了一定的污染。相反,部分学者则认为产业集聚改善了环境质量,如Zeng等[15]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污染天堂效应。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如齐亚伟[16]、原毅军等[17]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临界值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存在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以往研究产业集聚大多集中在工业集聚、制造业集聚、服务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还不多见;二是部分学者剖析了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但研究维度基本为两两关系分析,鲜有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下,涉及协同集聚与雾霾污染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三是在测算贸易开放时,绝大多数学者未对进出口贸易与加工贸易进行区分,缺乏考察不同贸易方式对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异质性影响;四是以往研究未考虑到贸易开放与产业集聚之间的联动性,忽视了贸易开放与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因两者发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基于此,本文弥补以上不足,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的内在联系,并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建议。
2 模型建立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建立
值得关注的是,环境污染存在难以避免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在受到自身经济发展影响的同时,往往还可能受到周边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OLS回归模型假定样本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忽略了样本的空间误差与依赖性,而空间计量模型将地理位置与空间联系有机结合,解决了因忽略样本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而造成的误差。因此,本文设定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此处,参考原毅军等[17]的思路,引入协同集聚的平方项来检验协同集聚与雾霾污染的非线性关系,若影响系数为负数,则表示协同集聚与雾霾污染呈倒U型关系。同时,纳入协同集聚与贸易开放的交叉项lnOpen×lnCoagglo,进一步控制贸易开放与协同集聚的交互性影响,在式(1)的基础上将模型设定为: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雾霾污染(Haze)。雾霾主要成分是PM2.5和PM10。由于PM2.5具有小颗粒、活性强、输送距离远、分布广、空气滞留时间长、易携带有毒物质等特性,对居民生活和大气环境的危害程度远大于PM10,因此本文采用单位面积内PM2.5来衡量雾霾污染。
2.2.2 核心解释变量
贸易开放(Open)。现有研究倾向选取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FTR)作为衡量贸易开放的标准,忽视了进出口贸易与加工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了区分不同贸易方式下,贸易开放对协同集聚、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尝试对贸易量进行修正处理,即用进出口贸易减去加工贸易的差值占GDP比重衡量贸易开放。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Coagglo)。本文采用区位熵衡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Psagglo)和制造业集聚(Magglo)指数。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参照宣烨[20]的思路,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務和地质勘查业”合并为生产性服务业。目前,在测度协同集聚指数上还未有统一的方法,借鉴杨仁发[21]的做法,通过产业集聚的相对差异来衡量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计算公式为:
2.2.3 控制变量
劳均物质资本(Capital)。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也是导致雾霾污染的主要诱因。参考齐亚伟[16]的做法,采用物质资本存量与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在资本存量的计算上以张军等[22]计算出来的1995年中国各省市资本存量为基期,根据惯例令折旧率η=9.6%,运用永续盘存法将其核算成资本存量。
劳动投入密度(Labor)。劳动要素作为知识和能力的主要载体,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雾霾污染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东童童等[23]的处理方法,本文借助从业人员数量与地区面积的比值来衡量。
环境规制(Regu)。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变革,加速企业绿色产业链构建,从而实现地区雾霾脱钩。环境规制衡量的方式很多,借鉴蔡海亚等[24]的做法,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与GDP比值来表征。
城市蔓延度(Sprawl)。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扩张了城市蔓延的趋势,给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本文参考蔡海亚等的思路[25],构造如下的城市蔓延度:
式中,Sprawl为城市蔓延度;density_employment为就业密度;density_population为人口密度;employment为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总数;population为非农人口总数;area为建成区面积;δ、为待定系数,此处认为就业密度与人口密度同等重要,δ、取0.5。
市场化水平(Market)。市场化水平越高,意味着经济活动越活跃,环境污染物排放也就越多。考虑到中国没有市场化水平的直接统计数据,本文直接采用樊纲等[26]计算出的各省市2003—2009年平均市场化指数,其中2010—2014年的数据借助Matlab软件运用回归方法计算外插值得出。
2.3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国研网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库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全球PM2.5浓度图栅格数据。针对部分年份某些统计数据缺失问题,本文依照其呈现出的变化趋势进行平滑处理,在研究对象上选取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0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
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需要检验统计数据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来测度2003—2014年中国雾霾污染程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研究发现各年份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马太效应显著,雾霾污染严重的地区趋于同雾霾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高高”集聚,雾霾污染较低的地区趋于同雾霾污染较低的地区形成“低低”集聚,呈现差异显著的两大组团式环状“俱乐部”。
随着省份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也逐渐减弱,并且在地理距离大于1 500 km时,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不再显著,意味着雾霾污染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可以对周边地区进行强有力的扩散,具有输送距离远、分布广、空气滞留时间长等特性,在空间效应上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学第一定律即地理事物或属性具有非静态性,在特定空间范围上存在扩散作用,该影响随距离的加大而递减)。
3.2 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分析
由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地空间溢出效应,倘若直接用OLS估计,会导致估计值有偏或无效,对此本文借助极大似然法来进行测算。在模型选择上,通过观测SEM和SAR模型的Lagrange乘数及其稳健性来选择最优模型,若LMERR显著于LMLAG,并且RLMERR通过显著性检验而RLMLAG未通过,则选择SEM模型;反之,则选取SAR模型。
表1报告了贸易开放修正前、后的估计结果,发现主要变量的系数符号没有出现变动,但在估计系数和显著性上有所变化,这也是下文将要重点解释的地方。由模型(1)(4)可知,无论是贸易开放修正前还是贸易开放修正后,协同集聚的估计系数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协同集聚对改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内部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就越明显,制造业集聚有效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输出的人力、知识资本又反过来推动了制造业的进步,在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同时削减了企业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产业内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而贸易开放修正前和贸易开放修正后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差异较大,显著性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由负向不显著变为负向显著,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加工贸易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仍旧停滞在初级发展模式,因技术与管理不配套而无法涉及产品的高端生产环节,致使产品的实际附加值和研发设计偏低,反映了低端贸易方式对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并不理想,改变传统粗放型贸易方式、提升贸易开放质量在抑制雾霾污染上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模型(2)(5)的估计结果显示协同集聚的二次项系数符号为负,说明协同集聚与雾霾污染呈倒U型关系,但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地,由模型(3)(6)可知,在贸易开放修正后,交互项lnOpen·lnCoagglo对雾霾污染作用系数有所提升,说明贸易开放带来的规模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提升协同集聚水平,制造业的高度集聚有利于企业将污染治理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污染治理的专业化和市场化,与传统加工贸易方式相比,高质量的贸易开放对协同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有效,能够显著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水平。
在控制变量中,劳均物质资本不利于缓解雾霾污染,其原因在于政府为了实现政绩考核标准,通过大规模重复投资来刺激工业发展,但资本的實际利用效率并不高,容易造成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对雾霾污染的改善十分有限。劳动投入密度显著加剧了雾霾污染,究其根源在于中国依然处于价值链低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低端从业者大量集中导致清洁技术难以推广。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本文认为这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符,企业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经营宗旨,由于污染环境的代价低、守法的成本高,当寻租经济收益高于环境规制成本时,企业往往明知故犯,宁愿扩大生产规模来弥补环境罚款成本。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呈微弱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在于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较为粗放、发展质量还不高,出现了亚健康和冒进式的城镇化现象,环境污染已成为现代城市的文明病。市场化显著加剧了雾霾污染,其原因在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工业集聚的爆炸式增长,长期大范围集聚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不断进行自我强化,加剧了雾霾的污染程度。
3.3 分时段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将降低能源强度和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减少GDP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本文将研究时期以2006年为界,同时考虑到政策执行的滞后性,将研究样本划分为2003—2006年、2007—2014年,探析将节能减排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前后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的相互关系。全国层面的分析已经指出,贸易开放修正后的模型对雾霾污染影响的解释更具说服力,因而本文借助贸易开放修正后的模型进行测算。
如表2所示,对比两个时段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协同集聚的作用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无论是直接检验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还是分别引入协同集聚的二次项(lnCoagglo)2和交叉项lnOpen·lnCoagglo检验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就协同集聚估计系数而言,在2003—2006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在于制造业集聚发展初期大量原始资本汇聚导致产能急剧扩张,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却相对滞后,产业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较差,产生的知识或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有限,加之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存在,遵循“先发展、后治理”的固有政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相反,协同集聚估计系数在2007—2014年显著为负,表明在地理和经济的双重空间聚集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上下互通,双方的交易成本和搜索成本有所下降,当协同集聚水平上升到一定临界值后,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大于挤出效应,有助于制造业生产技术、管理水平与资源重新优化配置,显著地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就贸易开放估计系数而言,在2003—2006年为正但不显著,究其原因为在贸易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将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借助贸易数量扩张手段提升产业集聚规模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以政府为主导的集聚往往会提高排污企业寻租的期望收益,从而弱化企业节能减排的硬约束,加之在集聚区内部分企业减排意愿较低,频繁存在免费搭便车的行为,最终引发环境公地悲剧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贸易开放估计系数在2007—2014年显著为负,本文认为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为,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升,地区经济水平也在稳步发展,经济收入达到一定的门槛时进一步的收入增长将有效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或污染水平的降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提升了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诉求。就协同集聚二次项(lnCoagglo)2而言,两个研究时段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意味着在研究时期内协同集聚与雾霾污染呈倒U型关系。就交叉项lnOpen·lnCoagglo而言,两个研究时段的估计系数符号由正变为负,表明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改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来对雾霾污染产生间接抑制作用,表现在当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促使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大于挤出效应,经济集聚带来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能够显著降低单位生产的能源消耗强度,且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升,其作用程度也会随之增大。
3.4 考虑模型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若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则会致使前文的检验结果出现有偏或非一致的情况。事实上,本文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其原因可能为:一是,存在遗漏变量,模型中可能会遗漏影响雾霾污染的重要变量;二是,互为因果关系,贸易开放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会影响区域雾霾污染,而地区雾霾污染状况的差异也可能会影响到贸易开放与产业协同集聚的发展。Lee[27]指出在有限的样本下,空间GMM估计与极大似然估计一样渐近有效,因此,此处拟采用空间GMM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前文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表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4 扩展讨论与检验
4.1 模型设定
针对中国各地区贸易开放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现象,贸易开放对协同集聚的技术外溢也或多或少对雾霾污染存在一定影响,但能否改善雾霾污染仍取决于各地区自身的吸收消化能力。那么,各地区间贸易开放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又有何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是否依赖于地区的贸易开放?为了准确刻画这种非线性效应,本文引入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以贸易开放为门限变量,以双重门槛为例,最终构建的门槛方程为:
4.2 假设检验
检验1:门槛效应是否显著。以单一门槛模型为例,原假设为H0∶β1=β2,表示不存在门槛效应;对应的备择假设为H1∶β1≠β2,表示存在门槛效应。构建LM统计量对
零假设进行统计验证,检验统计量为F(γ)=[SSE0-SSE1(γ^)]/σ^2。SSE0、SSE1(γ^)依次为H0和H1假设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由于在原假设H0下,F(γ)为非标准分布,Hansen提出利用Bootstrap自抽样获得渐进分布,进而并计算接受原假设的P值。
检验2:门槛估计量是否等于真实值。原假设为H0∶
4.3 门槛效应检验
表3報告了门槛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研究发现: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Bootstrap LM值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而三重门槛的Bootstrap LM值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意味着以贸易开放为门槛变量拒绝线性关系的原假设,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
表4报告了双重门槛估计值,双重门槛估计值依次为-2.000、-1.607,相对应的95%置信区间依次为[-2.031,-2.000]、[-1.607,-1.603],由于本文最初对各变量做了取对数处理,因而其实际门槛估计值依次为
4.4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表5报告了门槛估计结果,为了便于与门槛模型进行比较,本文还依次采用SYSGMM、OLS方法来检验。门槛回归表明,在不同的贸易开放阶段下,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当Open<0.135时,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0.357);当0.135
对此可能的解释为,当贸易开放低于门槛值时,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致使协同集聚对改善雾霾污染的作用较弱,但随着贸易开放的逐步提升,且当贸易开放越过门槛值时,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正向外部性效应十分显著,一方面,贸易开放带来的技术和知识红利推动着集聚规模的急剧膨胀,随着协同集聚产业共生性的逐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上下游生产环节互通互联,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技术溢出推动企业生产和管理技术的提升,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高级要素,其所蕴含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不断集聚,通过产生竞争效应、学习效应、专业化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对制造业升级形成飞轮效应,商品环保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效率均得到显著提高。当贸易开放越过更高的门槛值时,随着人口密度、经济密度持续攀升,土地价格、房屋租金、运营成本的上涨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殆尽,极大地透支了环境的承载能力,政府采取强制性的环境规制措施倒逼企业排污能力的提升,企业面临高昂的排污费用或者被迫淘汰、重新选址,从而对改善雾霾污染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进一步分析了2003、2008、2014年各省份贸易开放门槛通过情况。2003年,有18个省份未跨越Open的第1个门槛,2008年减少至17个,到了2014年进一步减少至12个,但宁夏、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甘肃、贵州、湖南、青海和内蒙古一直低于门槛值。2003年,仅有吉林跨过Open第1个门槛,2008年则变更为黑龙江与河北,在2014年数量增加较为明显,越过门槛的省份为江西、新疆、广西、四川、安徽、云南、黑龙江。2003、2008、2014年,跨越Open第2个门槛的省份则较为稳定,一直保持在11个,虽然内部省份有所更迭,但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在上述时段内均未发生变动。其原因是虽然中国先后出台多项措施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贸易,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地理等因素的制约,目前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仍然较低,未能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因而需要进一步扩大贸易开放水平。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贸易开放水平跨过第2个门槛值,但在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下,反而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改善并不显著。其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资的引入变得更加理性化,从追求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对外资企业技术与能耗水平的进入门槛要比中西部地区高得多,同时东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的政策红利已获得较高的利用外资,众多的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在资源要素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对FDI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致使贸易开放对产业集聚释放的技术外溢效应有所减弱。
5 結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如下:①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存在明显的改善作用,在剔除了加工贸易进行修正后,贸易开放对改善雾霾污染发生实质性的转变;②协同集聚与贸易开放交叉项对雾霾污染存在负向影响;③分时段检验发现,贸易开放与协同集聚存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在初期对抑制雾霾污染促进不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促进作用变得显著;④贸易开放与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因两者发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上述研究成果蕴含的主要政策启示如下:
(1)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破除产业发展中的棘轮效应。研究表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能够显著抑制雾霾污染。因此,必须秉持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依托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与渗透,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向生产性服务业拓展延伸,引领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优化升级,不断沿“微笑曲线”两端服务业延伸产业链条。同时,变革制造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扭曲组织结构,在积极发展先进高端制造业的同时适度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吸引周边关联性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鼓励制造业进行外包服务管理,并构建跨边界的产业协同集聚模式,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助推器,培育制造与服务两位一体的多功能产业集群。
(2)调整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推动外贸由规模型扩张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研究表明,剔除加工贸易后的贸易开放对雾霾污染抑制作用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因此,需要将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进行转变,引领贸易结构走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路线。具体而言,变革“以进养出”的传统外贸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技术研发能力,对加工贸易的产业链进行前向延伸和后向延伸,提高出口产品的增加值与技术含量。同时,需要增强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积极培育与创建自主品牌,努力提升贸易标准化的研发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与颁布,努力促使本国技术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
(3)破除贸易开放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门槛效应,实现两者的匹配发展。研究表明,在不同的贸易开放门槛下,协同集聚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能为提高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而追求外贸增长方式的规模型扩张,需因地制宜,统筹地区协调发展。具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仍然较低,未能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需要进一步扩大贸易开放水平,借助贸易技术和知识溢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降低单位生产能耗,而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贸易开放已进入瓶颈期,对外开放的释放政策红利有限,FDI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应当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为抓手,为高质量的贸易结构“腾笼换鸟”,注重向贸易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YAMASHITA N, MATSUURA T, NAKAJIMA K. Agglomeration effects of interfirm backward and forward linkag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China [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14(34):24-41.
[2]徐维祥, 刘程军, 江为赛,等. 产业集群创新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动力演化——以浙江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9):103-110. [XU Weixiang, LIU Chengjun, JIANG Weisai,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volution driving force of industrial cluster innovation: a case of Zhejiang Province [J].Economic geography, 2016(9):103-110.]
[3]SHAO S, TIAN Z, YANG L. High speed rail and urba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7(64):174-183.
[4]HILBER C A L, VOICU I.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omania [J]. Regional studies, 2010, 44(3):355-371.
[5]李胜兰, 陈智武.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14,29(5): 109-118. [LI Shenglan, CHEN Zhiwu.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s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2014, 29(5):109-118.]
[6]NING Lutao, WANG Fan, LI Jian. Urban innovation, regional externaliti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4):830-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