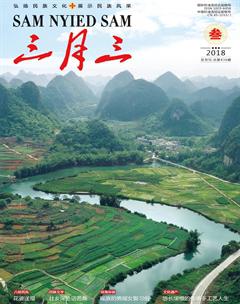马儿啊,你慢些走
廖克群

虽然很久没有听到马儿在乡间小路上“嘚嘚”的马蹄声,很久没有看到马儿在山坡上悠闲吃草、打滚的身影,更难欣赏到马儿在田野上咴咴嘶鸣的震撼之音,但是,当“马到成功、车马盈门、金马玉堂、万马奔腾、一马平川、兵强马壮、千军万马”等一大堆抒马、写马、颂马的成语出现在我的眼前时,不免又勾起我对马的思念与柔情。
我生长在广西巴马一个偏僻的乡村,在过去,在“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的穷乡僻壤里,马儿不仅是人们唯一代步的交通工具,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马儿的粪便还是非常好的有机肥。家乡人养马的历史应当追溯到祖先开山创业的时候起,一直延绵几千年。然而,随着移动通信替代了鸿雁传书,随着农业机械替代了手工劳作,随着化学肥料替代了农家肥料,农村家庭养马越来越少,甚至难觅马儿的踪影了。马儿哪去了?马儿怎么了?我在为科技发达带给人类便利而高兴的同时,更对过去那些年代的人们对马儿依赖的情景以及马儿辛苦地付出有着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记得我第一次去赶集是在三四岁的时候,虽然要去的集市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集市,但来回也要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那天一大早,当我从床上懒洋洋地爬起来时,父亲早己把煮好的饭菜端到桌上,并把要带我去赶集的好消息告诉了我。我那个高兴劲儿比过年穿新衣还开心,三口两口就把一碗饭扒拉进了肚里,催促父亲赶紧上路。由于我年纪小,父亲又是残疾人,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等来到集市时,整条街已是人头攒动。卖山货特产的、卖猪鸡鸭鹅的、卖针头线脑的……把本来就不宽敞的市场围得水泄不通。父亲赶集的目标就一个——买两头小猪回家养。可是从猪行的这头选到那一头,父亲不是嫌猪的成色不好,就是嫌卖家出的价钱太高,用钩针扎紧的装着买猪钱的口袋他一直没有动过,急得我直跳脚。父亲悄悄地跟我说,这些猪崽刚上市,喂得饱饱的,现在买的话要多付好多钱,等到快散集时,才好压价。望着精明的父亲,我只好强忍着饥饿,拖着疲倦的身体一步不离地跟在他后面,看着他跟别人讨价还价。时间大约过去了几个小时,眼看集市上的人渐渐散去,父亲才在他看中的猪崽面前停下来,经过几番你来我往的紧张“谈判”,父亲终于拿出了上衣口袋里的钱,用手指蘸着口水一张张地点来点去后递到卖主的手上,然后提着猪崽走出了猪行。此时,日头已经偏西,赶集的人也已陆续散去,父亲没有忘记给我许下的承诺,买了两块发糕、一对芭蕉递到我的手上,叮嘱我路上吃,然后便匆匆忙忙催我赶路。早上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白天又在集市上像个小跟班一样跟在父亲身后走来走去,我几乎己迈不动腿,爬上一座土坡后我实在走不动了,便靠在路边停了下来。看着不时从身边走过的骑马人,心想,要是自己家也有一匹马该多好啊,那就不用走路回家了。恰在此时,我的一个远房大哥牵着一匹马走了过来,马背上驮着他赶集买的一些杂货,看到我在路边耍懒,他便把买到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全都装到马背一边的竹筐,把我父亲买的两只小猪也一并装了上去,然后,让我坐到另一边的竹筐里,就这样,我们才安然地打道回府。
这是我第一次坐在马背上,第一次尝到了有马的甜头,我渴望着家里也能养一匹马。父亲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等到我上学时,父亲便从亲戚家买了一匹小马回家,叮嘱我小心侍候。打那时候起,我每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山去割马草,拿回家就给小马喂上,还一边和小马说悄悄话。小马在我和家人的精心料理下一天天地长大,它可以驮着我溜达了。空闲时我就两腿夹着马肚子,一手抓着马鬃毛,一手牵着马缰绳,让这个小家伙驮着我在田野上休闲散步、小跑。有一次,这个顽皮的小家伙故意使诈将我从它的背上摔了下来,而它跑了几步后又回头看着我,似乎在说:你这不中用的家伙。我和小马的感情越来越深,等它再长大一点,我求姑爹买了一副马鞍,小心翼翼地给它套上,马鞍两边还系上两个竹筐,训练它驮东西。慢慢地,我的小马长成了大马,它驮的东西也由少变多,由轻变重,它俨然是我们家的一名壮劳力了。
我们家的田地离家较远,大集体年代,靠工分吃饭,若谁家养有马,除了马粪可以换工分,用马驮运肥料、种子、公粮等都以斤论工分,就连驮运原木去供销社卖也是以原木大小记工分,马的身价不可谓不高。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马的作用更大了。那时候,马儿早上要驮运工具和肥料到田地,晚上要驮运柴火、马草回家,等到山上的旱谷收割了,马儿要承担起把全部粮食运回家的重任。久而久之,马背由于马鞍的长期摩擦、压迫,起了茧子,茧子磨破后会流血、化脓、感染。马儿要遭受多大的痛苦啊,只是它不会叫唤,不会呻吟,不会装疯卖傻,只是默默承受着。
虽然我己参加工作,但看到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乡父老渴望摆脱贫困而拼命劳作的场景,我也深受感染,加入到劳动的大军。每逢双休日我就骑着我家的马儿朝着我选定的地块进发,砍树、炼火、播种、除草、施肥。久而久之,只要我将马鞍套牢,骑到鞍子上,马儿不用指挥就能径直将我带到目的地,正应了“老马识途”这句老话。有一次,由于疏忽,在马儿走向一个土坎时,我被反弹回来的树枝横扫,从马背上重重地摔倒在马儿的四蹄前。那是一段只容得一匹马通过的险路,可想而知,如果我的马儿再往前走一步,我不是小命呜呼也要伤筋动骨,就在那一瞬间,已经迈出的马前蹄硬生生地没有往下落,我的小命也因此保住了。都说马儿是有灵性的,是通人性的,至此,我方相信“良马救主”并非虚言。
后来当看到马儿代替水牛、黄牛耙田犁地,我在为家乡父老超强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所折服的同时,也为马儿鸣不平,替它们叫屈,凭啥所有的脏活、累活、重活都让马儿干啊?但是,马儿呢,它们是那么乖巧、那么听话、那么顺从和义无反顾,竟然将两个角色都演绎得无可挑剔。小时候我总认为做马应当比当牛强,马儿至少还有人放夜草而牛没有,但后来我觉得我错了,馬儿的艰辛并不比牛少。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微耕机可以在梯田上自由操纵了,摩托车后座可以载重,可以在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上奔驰,甚至可以开到田间地头,马儿、牛儿们不再是生产的主力。
在乡下工作十几年后我就调到了县城,我那亲爱的马儿也只能交给在农村的大嫂来接管。据大嫂说,马儿尾巴上的毛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大灯笼,就像人工编织的一样,无法解开。有人说这是大吉祥的象征,但也有人说这是不祥的兆头,必须把马儿卖掉方能破解。也许是受这话的影响,也许是村里的马几乎都已经卖光,自家养一匹马也没多大意思,再加上大嫂一个人忙得顾不过来,最后只能把马卖掉了。
家里的马没有了,全村的马也己所剩无几,几乎家家养马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我想念我的马儿,想念村里的马帮,这不是我思想上的复古和倒退,不是我对新生事物的不接纳和排斥。我只是在想,所有事物的存在总有其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尤其是对人类有过贡献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心里有它,就算是过时了或消失了,我们也应当常怀于心,念其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