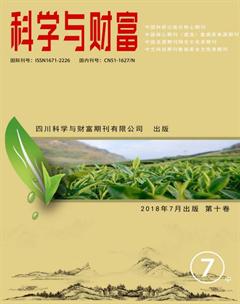朱熹诠释“明明德”的思想历程
摘要:朱熹对《大学》“明明德”命题的诠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他以孟子的心性论和宋代理学思想成果为理论工具,不断深入发掘“明德”内涵的结果。中年以前,朱熹以《孟子》的“良知良能”揭示“明德”的内涵。1186年以后,他辗转纠结于该从“性”还是从“心”的角度揭示“明德”的意蕴。直到1196至1198年间,才最终确定以揭示“心”的体用解释“明德”的思路,从而确定了《大学章句》中对“明明德”注语的文字表述。
关键词:朱熹;明明德;良知;至明不昧;虚灵不昧
我们知道,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明明德”的诠释,在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理学思想的继续演进也产生过深刻影响,是后世学者关注与争论较多的问题。如清末学者陈澧指出:朱子《大学章句》以“虚灵不昧”释“明德”,不如《语类》中所说的:“光明正大者谓之明德”准确。 不过,朱熹对“明德”内涵的思考与揭示,历经数十年,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述,是其不同阶段的思想成果的结晶。显然,这是个关系到准确理解朱熹对《大学》“明德”思想的认识及其理学思想发展进程的思想历程。我们在《朱熹<大学>“明明德”诠释的理学意蕴》一文中,揭示了朱子运用工夫论、心性论与理气论诠释“明明德”的哲学路径。本文拟根据散见于《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和《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或问》中的相关材料, 追溯这一思想历程的时间线索,以揭示朱熹运用宋代理学思想成果解释先秦文献《大学》的命题,进而发展理学的进路与思想特色所在。
一、良知良能与明德
朱熹早年已经认识到“明德”的内在性和普遍性,亦即认为人人皆有“明德”,“明德”非由外铄,而是根于人心,被人的私欲所蔽而不明。这种认识其实正是来自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他说:
明德,谓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
此条是廖德明所录,时间在1186年。朱熹又说:
《大学》只前面三句是纲领。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
此条《朱子语类》通行本作廖德明所录,但朝鲜本作窦从周录,实际上应该是窦从周所录。同卷有一条廖德明记录自己问学朱熹的话可以为证:
问:“‘止于至善,向承教,以为君止于仁,臣止于敬,各止其所而行其所止之道。知此而能定。今日先生语窦文卿,又云:‘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斋,立时止也。岂以自君臣父子推之于万事,无不各有其止?”
窦文卿即窦从周。从此条可以看出,上一条是朱熹对窦从周阐述《大学》三纲领的含义,廖德明只是旁听。这一条则是廖德明旁听后,对上一条中朱熹阐释“止于至善”有所理会,遂以自己的理解向朱熹求证。但无论上一条是谁所记录,都足以说明以上所引三条材料,都是廖德明与窦从周一起问学于朱熹时所记录的。考廖德明与窦从周一起问学朱熹是在1186年4月, 以后二人皆各自继续问学于朱熹,但未再交集。 可知,1186年,朱熹57岁时,还是以孟子“良知”、“良心”之说等解释《大学》之“明德”的。
两宋学者中,最早以《孟子》“良知”说解释《大学》的是吕居仁,在其《大学解》中,释“致知”之“知”为“良知”,认为是人人与尧舜所同者。朱熹在《杂学辨》中辩驳了吕氏的格物致知之说,但没有反对吕氏以“致知”之“知”为“良知”。朱熹《杂学辨》著于1166年,时年37岁。在成书于1172年的《论孟精义》中,朱熹选择了程颐和尹焞对孟子“良知良能”说的解释,第一条即程颐的:“良知良能,皆无所由,及出于天,不系于人。”由此可以看出,朱熹57岁以前对“明明德”的关注,实际上是根据对北宋诸儒思想的理解,认为“明德”就是“良知良能”,乃天所赋予人的。由此可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朱熹直接以孟子“良知良能”释“明德”。
但1186年以后,《朱子语类》与《朱子文集》中不再有以“良知良能”之说解释《大学》“明德”的记录。虽然朱熹仍然重视孟子的“良知良能”之说及其与《大学》“明德”之间的思想关联,但主要是从“明德”与“良知良能”都是人所固有,为天所赋予的相同特性加以考虑。显然,“良知良能”只是一个基于观察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还不足以揭示《大学》中“明德”的意蕴,更不能与精密严谨、系统深刻的佛教的心性论抗衡。还必须继续追问“良知良能”的来源,“良知良能”何以能成己成物,及其在人的心性结构中的位阶,才能明了“明德”的内涵。
事实上,以“良知”释“明德”,在训诂学上没有根据,在《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上下文语境中,义理上也滞碍不通。即使从儒家修身的工夫论上看亦显粗糙,只是孟子用来指示人性本善和人性之善的内在性的一个路头。如以“良知”为“明德”,确实是错把孟子的手指当月亮了。
二、从“虚灵不昧”到“至明不昧”
1187年后,朱熹摆脱“良知”说的纠缠,开始从孟子心性论的层面仔细分析和探究“明德”的本来义涵,力图确认“德”的含义,以及“明”字如何安置在“德”字上。1191年,朱熹在与学生讲学中指出:
天之赋予人物者谓之命,人与物受之者谓之性,主于一身者谓之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谓之明德。
显然,朱熹在这里,力图从天道性命与身心关系的角度来探讨“明德”的含义,从而将对“明德”的研究提到了宋代理学的高级位阶——心性论的层次上。其中,天命人物之性,是子思《中庸》中提出的命题;身心关系方面虽然先秦诸家皆有所讨论,但北宋理学家继承的则是由《孟子》提出的存心养性说,“心主于身”就是二程对此问题的总结;至于“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则是朱熹对“明德”的来源与本质的新认识。
从天道性命层面探讨理学命题,是朱熹早就熟悉的方法,例如他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就选了《二程遗书》中的一条:“在天为命,在物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朱熹显然也是按照二程将同一层次的概念进行类比而指出其联系与区别的方法,通过与“性”、“天命”、身、心等概念的类比,明晰“明德”的理论位阶,然后从儒家的思想史与学术史两个层面揭示“明德”的内涵。
《朱子语类》记载:
问:“‘天之付与人物者为命,人物之受于天者为性,主于身者为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为明徳否?”
曰:“心与性如何分别?明如何安顿?受与得又何以异?人与物与身又何间别?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曰:“此两个说着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是非之心,更细思量。”
这是门人直接以朱熹的原话求证于朱熹,表明该门人对朱熹将“明德”与心性相类比,以区别“心”与“明德”有所质疑。因为朱熹1189年所修定的《大学章句》中,对“明德”的注释,是不判分心德,从心德一体的角度进行解释的。
问:“《大学注》言:‘其体虚灵而不昧,其用鉴照而不遗。此二句是说心?说德?”
曰:“心、德皆在其中,更仔细看。”
又问:“德是心中之理否?”
曰:“便是心中许多道理,光明鉴照,毫发不差。”
本条是徐寓于1190至1191年之间,在漳州问学朱熹时所记,其中《大学注》指朱子1189年修订的《大学章句》,1191年刊刻于漳州学宫。 显然,《大学注》中,“其体”之“其”是指“明德”,“虚灵不昧”是对“明德”的本质特征的描述,也是对“明德”之“明”字内涵的揭示;“鉴照不遗”是言“明德”之用。在这条注释中,朱熹实际上是言心以释“明德”,而不是直接揭示“明德”含义。因为“虚灵不昧”、“鉴照不遗”实际上就是心之体与用。但以“虚灵不昧”言“明德”之“体”,等于直接说心就是“明德”之“体”。而既然心是“明德”之“体”,那心之“体”又是什么呢?所以门人进一步质疑,“德是心中之理否?”朱熹在接下来的回答中,回避了徐寓的正面质疑,指出“明德”是人心中“许多道理”,将门人的“一理”转化为了“众理”,而回避了门人的问题实质:即心、理与“明德”的关系。
显然,虽然朱熹回避了门人的问题,但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注释中心、德不分的问题,所以他力图再回到天道性命、身心关系的层面检讨明德的内涵,而提出“天之赋予人物者谓之命,人与物受之者谓之性,主于一身者谓之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谓之明德”的解释。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天所赋之命与人所受之性,在思孟一派的思想体系中,显然都被認为是光明正大、纯粹至善的,而主于人身之心则比较复杂,可以说在历史与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昏昧是常态。那么,“天命”、“性”与“明德”是什么关系?这三者与心的关系又是如何?当门人再以此质疑时,朱熹不再回避,而是道出了自己的问题意识所在:“心与性如何分别?明如何安顿?受与得又何以异?人与物与身又何间别?明徳合是心?合是性?”连续五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涉及到北宋以来理学的精深之处。如果从正面的角度,从本质上进行回答,都意味着必须重新检讨先秦以来儒家的心性理论,特别是北宋五子的心性论思想。所以,朱熹在此重新反思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是非之心”,总是兼心言性,兼性而言心,总是将心性放在一起谈的现象。
“明德”是心还是性,是朱熹晚年一大问题所在。本来朱熹在61岁(1190年)时觉得自己已经彻悟,曾说:“某觉得今年方无疑”。而62岁时,朱熹又叹息:“…自觉无甚长进,于上面(道理)犹觉得隔一膜”,“于上面但觉透得一半”。
此后,1194年,朱熹入讲宋宁宗经筵时,于进呈宁宗的《经筵讲义》 中这样注解“明明德”: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当有以明之而复其初也。
在这里,朱熹以“至明不昧”替换了原来的“虚灵不昧”,显然是为了去掉原来以心言德的思路,而直接以“至明不昧”解释“明德”,强调德之“明”。又,与早年解释“明德”之所以不明,是为人欲所蔽之说相比,这里更强调了先天的因素,即还有排在第一位的“气禀所拘”,显然这里对“明德”不“明”的原因的阐述,已臻于完备。
在接下来的讲解中,朱熹则又进一步阐明了人物化生,人物之“间别”等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三年前五个问题的回答,他说:
臣窃谓天道流行,发育万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为此身者,则又不能无所资乎阴阳五行之气。而气之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浊,有纯有驳。以生之类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以人之类而言之,则得其清且纯者为圣为贤,得其浊且驳者为愚为不肖。其得夫气之偏且塞而为物者,固无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体矣。惟得其正且通而为人,则其所以生之全体无不皆备于我,而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粲然,有以应乎事物之变而不昧,是所谓明德者也。
朱熹指出,人物皆有“主于一身者”,即其得之于天的“所以生者”;又指出,人物的“间别”源于所得之阴阳五行之气的偏正与通塞的不同;进而指出“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粲然,有以应乎事物无穷之变而不昧”者为“明德”,则是以“方寸”指心,以“万理粲然”指德,以“应乎事物无穷之变而不昧”安顿“明”。可见,实际上朱熹这番论述是对北宋周濂溪的宇宙化生论、张载的气质之性论与二程心性论的高度精炼的综合与融汇,基本解决了当年的五个问题。
三、从“至明不昧”向“虚灵不昧”回归
《经筵讲义》中对“明明德”的解释清晰而简洁,每个字皆有安顿,从解经的角度看,已经没有问题。但从朱熹的讲解中可以看出,还有一个问题不甚明确,那就是“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身之主”中,这个“所以生者”究竟是什么?
而我们注意到,大概在1196到1198年间,朱熹完成了对于《大学章句》“明明德”注释的修订。朱熹于注中说: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
这是《大学章句》通行本中对“明明德”的完整阐释,共67字,与《经筵讲义》中的注解已有极大地不同。首先让人瞩目的是,朱熹又以“虚灵不昧”阐释“明德”,显然又是回归到了以言心而言德的思路。其次,又加入“以具万理而應万事”8字,从功能或者说从用的角度直接解释“明德”。再次,进而指出“本体之明,有未尝息者”,强调了人心不会终昧,人性之善不会终泯的事实,为对《孟子》的性善论的信仰,建立了坚实的学理基础。最后,增加“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一语,显然是阐述“明明德”的下手着功夫处,指明“明之”的具体途径。
从《朱子语类》中,我们发现,朱熹和门生们谈论到这个注释,最早在1197年。
问:“‘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是如何?”
曰:“人固有理会得处,如孝于亲,友于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热,不可谓他不知。但须去致极其知,因那理会得底,推之于理会不得底,自浅以至深,自近以至逺。”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此条是朱熹晚年的门生辅广所录。辅广,字汉卿,1194年始问学朱熹。1197年,庆元党禁最严时,朱熹门生纷纷避散,辅广则在其时往建阳求教,停留二个月左右,给了朱熹巨大的安慰。这一条显然是辅广建阳问学朱熹时所录,正以注释中的“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为问。考朱熹庆元二年(1196)《答孙敬甫》中说:“《大学》亦有删定数处。”可知朱熹在1196年左右,应该对“明明德”的注释有所删改。所以,1197年,辅广才能读到此条注释而发问。
《朱子语类》还有一条: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禅家则但以“虚灵不昧”者为性,而无“以具众理”以下之事。
这一条的记者沈僩,字庄仲,温州永嘉人,1198年问学朱熹。本条语录是朱熹以“明德”的内涵判分儒、释之别。
而这次修订后,直到朱熹去世,朱熹虽然仍在对《大学章句》进行修改,但关于“明明德”的注释再也没有修改过,可见,这的确是朱熹的晚年定论。由上可知,朱子晚年,也以这个注释教导学生。
四、讨论:明德是心还是性
我们已经指出,孟子的“良知良能”与《大学》的“明德”不是同一位阶的概念,“明明德于天下”不能解释成明“良知良能”于天下,虽然使天下人皆有以明其“良知良能”,也是“明明德于天下”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不学而能、不习而知的能力是孟子基于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观察做出的描述性解释,以证明人性本善,而《大学》的“明德”,是与人性同一位阶的概念,是对人的整体判断。朱熹放弃以“良心”、“良知良能”解释“明德”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朱熹《经筵讲义》中的注释“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当有以明之而复其初也”的确臻于完善,以“人之所得乎天”释“德”,以“至明不昧”释“明”,可谓句意俱到,为何朱熹晚年还要做如此大的修改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朱熹的《经筵讲义》中,有一个问题不甚明确:“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身之主”中,这个“所以生者”究竟是什么?而体现在注释中,就是“人之所得乎天”者,究竟是什么?这应该是朱熹晚年修改“明明德”注释的问题意识所在。比较两个注释,我们不难看出,最后定论中“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正是对于“人之所得乎天”的说明和限定。也就是说,朱熹认为,天所赋予人的不全是“明德”,只有“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那部分才是。在朱熹晚年修定的《大学或问》中,他详细阐述了人所得乎天的,他指出:“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也就是说,人与物所得乎天的有理有气,和以理为依据的“健顺仁义礼智之性”,以及以气为依据的“魂魄五脏百骸之身”。那么,“明德”肯定是指“性”的部分。可是,朱熹为什么又要用“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来加以限定呢?所谓“虚”,是指物体中空而能容纳事物,“灵”是指物体能流转、通贯,不滞碍,诚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虚灵不昧”是朱熹用来指称“心”的词语,且“具众理”也正是对“心”的容纳收藏功能的描述。这样看来,“明德”又似乎是指“心”。但朱熹曾明确指出:“心是动底事物,自然有善恶”,普通人的心是“气质有蔽之心”。而“明德”是纯粹至善的。又,在《大学或问》中,朱熹更是指出:“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显然,这里“方寸”就是指心,而“明德”是指心中“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的部分,“虚灵洞彻”可以说是指人心“正且通”、流转通贯的“气”,而“万理咸备”则指天赋之“理”。
可见,在朱熹这里,“明德”既不是性,也不是心,而是一个与心、性不同位阶的概念,主要是指人的规定性和人自我实现的依据而言,即“所以异于禽兽者”与“所以可为尧舜而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但“明德”的内涵又与心、性紧密关联,要阐释“明德”的内涵,显然要兼心性而言。《经筵讲义》中将“明德”解释为“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问题就出在直接以“性”释“明德”。这个解释还有一个缺陷,即会让人误认为“明德”或者“性”是实有一物,会光辉闪烁。因而,在最终定论中,朱熹在宋儒理气论的层面,揭示“明德”的内涵,更强调“明德”是“理”的特性,即“具万理”而能“应万事”的特质。
辅广所记的朱熹的一个比喻,也许更能说明朱熹的“明德”概念,朱熹说:
“心与理一,不是理在面前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因笑云:“说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经函,里面点灯,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灿烂,但今人亦少能看到如此。”
可见,“明德”便是指心包蓄众理,如“藏”里点灯,四方八面都光明灿烂。所以,朱熹有时直接指出:“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许多道理在这里。” “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许多道理在里,其光明处,乃所谓明德。”
由此看来,朱熹对《大学》“明德”内涵的探究,在如何确定和表述心、性与“明德”之关系上,颇费思量。而其认识“明德”,揭示“明德”的思想进路,实际上一直未曾离开孟子的心性论。但顯然,又超越了心性论的层次,最终沿着二程的理气论的思路才得以解决。实际上,程颢早已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 即以“理”指称“明德”。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朱熹反复修改“明明德”的注语,主要集中在晚年,前后持续近十年。这并非意味着朱熹对“明德”的思想认识直到1196年或1198年才成熟。因为朱熹深知注解经书,其目的是要为后学掌握经典的意义,以求得圣人之心,进而明得天地之理指明道路,实际上是起指个路头的作用,所以下注语决不能遮蔽或穿凿经文之意,也不能完全说破,而代替后来学人自己的思考。这十余年的修改,朱熹下语字斟句酌,也颇费了一些时间。
参考文献:
[1]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九.陈澧集(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1-172
[2]朱汉民,周之翔.朱熹《大学》“明明德”诠释的理学意蕴.哲学研究,2012(7),34-39
[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40
[4]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8
[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第442-443页
[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第442页
[7]窦从周时年五十,慕朱子之学,于淳熙丙午(1186年)4月5日至武夷精舍?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四,第3621页
[8]参见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58-59,101. 陈荣捷.朱子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1-252
[9]朱熹.杂学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第3493页。
[10]朱熹.论孟精义.朱子全书.第802页。
[11]游敬仲录于1191年?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第432页
[12]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9
[1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五.第222页。
[14]徐寓录于1190年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第438-439页。
[15]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10
[16]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3页。
[1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〇四.朱子全书.第3441页。
[18]《经筵讲义》可视为朱子1194年以前的《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的重要版本?
[19]朱熹.经筵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第692页。
[20]朱熹.经筵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第693页。
[21]这一段引文也正是朱子1194年前,未修改的《大学或问》的原文?朱熹.经筵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第693页。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
[2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第439页。
[24]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94页。
[25]朱子在给吕祖俭的信中说:“风色愈劲,精舍诸生方幸各已散去?今日辅汉卿忽来,甚不易,渠能自拔?”朱熹.答吕子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第2243页。
[26]朱熹.答孙敬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3065页。
[2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第439页。
[28]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06
[29]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9页。
[3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五.第220页。
[31]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508页。
[3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五.第219页。
[3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第435页。
[3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第442页。
[35]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二版,136
[36]朱子常说的解经下文字最难?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第449页。
作者简介:周之翔: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贵阳孔学堂入住学者,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黔学、湘学。
基金项目:贵州省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行动心学”课题成果,课题编号:TS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