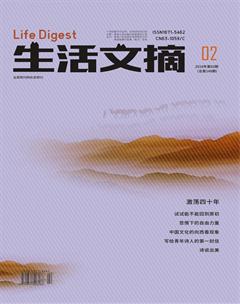汉唐精神的当下意义
张渝
当汉唐精神作为一个板块被我们倡言与标举时,汉与唐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短命的大隋王国却在很多人的视域里失联了。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汉之风骨、唐之气象,无论是在审美经验,还是在世俗情怀上,都有其相近之处。但是,倘若没有汉唐之间多个朝代将近四百年的艺术努力,哪怕是被人讥讽的风花雪月式的努力,汉之风骨、唐之气象,不仅很难独立成篇,而且还会有各式各样的残缺。因为,这样的努力,对前面的汉代是润色;对于后面的唐朝是提示。故此,谈论汉唐精神,谈论汉唐精神的当下意义,便不能不从汉唐精神的概念及其关联的文化现象来考量。非此,便很难真正领会汉唐精神。当然,也就谈不上汉唐精神的任何当下意义。
一、汉唐何以成为精神
当我们以各种词汇提纯古人审美精神时,最长气的是“汉魏风骨”与“唐人气象”。“风骨”也罢,“气象”也罢,其得以胚胎、萌芽、生成多与长安一地有关。故此,即便相隔将近四百年,“长安”一地作为地理文化的纽带,还是把两个意气风发的年代,以“同乡会”的形式串在一起。因为,汉之风骨,唐之气象,都与长安有关。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老乡”关系,让我们很容易地把这两种审美关系聚合在一起。于是,有了我们以为的“汉唐精神”。
“汉唐精神”中的汉之“风骨”,曾被很多学者诂笺,考证、解析,其概念的演艺谱系也大致如下:东汉时,人们用“风骨”这两个字来品藻人物,形容人的体貌、风度。南北朝时,“风骨”一词已被移用于书画评论。齐梁间的刘勰著《文心雕龙》言及“风骨”时曾说:“《诗》总六义,凤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由此,学者陈伯海推断说:“‘风属于文章情意方面的要求,其征象是氣势的高峻与爽朗;‘骨属于文章语言方面的要求,其显示为言辞的端整与直切。”①这样的解释没有错,而且很多学者都持类似看法。但是,如此解释,还是让人似懂非懂。所以,本文尝试从另一维度做一阐释。
从文化谱系的角度说,很多人都知道《周易》乃是“群经之首”,可是,却极少有人从易经中去寻找一些我们一时难以知晓的意义。即使有人去找,也由于学易不精,而陷入人云亦云之中,比如诸葛志先生在《中国原创性美学》一书中,注意到“风骨”一词和易经有关,却是从“大畜”一卦入手。他说:“《易·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按,‘大畜由乾艮二卦重叠而成,乾下艮上,乃‘天在山中之象。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向秀曰;止(静)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也。天为大器,山则极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这样看来,‘大畜乃是一个坚固如山石,开阔如苍天的‘大器卦象。这个卦象的根本特点,《易经》作者用‘刚健、笃实、辉光六字来说明。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刘勰形容文章之有风骨,一则曰‘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再则曰‘文明以健,终则曰‘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诸如此类的说法,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大畜之象。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刘勰所谓‘风骨可以用‘刚健、笃实、辉光六个字来概括。”②
原谅我如此不厌其烦地抄录专家说法。因为,我想让读者们知道一个朴实的词汇是如何被专家解释得失了本来面目。“风骨”和《易》有关,是事实,但它不是和大畜,而是和巽有关。巽卦卦象随风。在这里,风是邪恶、阴性、无立场、阿谀奉承之象。如墙头草一般,随环境改变,是多元的;而骨则是一元的。风骨一词中,“风”和“骨”两个字是阴和阳、一元和多元的对立。“风”意味着环境恶化、多变,而“骨”意味着阳刚、正气、稳定性。“骨”如同暗夜之中的一盏孤灯,又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因此,同样采用比喻性说法,“风”在这里就是暗夜、污泥之类的负能量,而“骨”则是灯、莲之类的正能量。一句话,由于环境险恶,我们需要骨的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在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骨”的精神和意味,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会强调“风骨”。
初唐之时文化环境虽不能说险恶,但绮碎积年以致“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基于此,初唐四杰开始接续汉之风骨,终于有了“以汉魏变齐梁”的口号与局面。不过,唐之风骨与汉之风骨还是有着些小差异。这一点正如陈伯海先生指出的那样:“建安诗歌孕育于动乱的年代,尽管因社会的变动促成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强烈的事业心,但面临着残破的山河与凋敝的民生,总不免引起重重哀感,致使慷慨任气的歌唱中时时伴有悲凉的音调。如当时居于文坛领袖地位的曹操,一方面在抒写‘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壮怀,一方面又要发出‘人生几何、‘忧思难忘的感慨。……相比之下,唐代社会的变革,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政治的相对开明,促使一般士子对前景抱有坚强的信念,诗作也充满青春活力。比如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③基于此,陈伯海先生又说:“这种唐人固有的乐观情绪,与建安文学中的英雄性格以及屈原以来的理想精神的传统相结合,就构成了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的风骨。它扬弃了‘汉魏风骨中感慨悲凉的成分,而着重展开其豪壮明朗的一面,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特有的素质。”④
在豪壮明朗的精神维度上,唐人形成自己囊括万有的气象。也正是在这里,汉人风骨穿越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重新生长在唐人的精神世界。我们也有了“汉唐精神”的说法。
其实,所谓“精神”,其释义有二:第一,指人对事物的感知与表意;二,表现出来的活力。本文所说的“汉唐精神”中的“精神”主要基于“活力”这一义项。也就是说,本文指称的“汉唐精神”指的是博大、雄浑、深远、超逸的时代风貌所涵括的激情与活力。
吸纳了汉之风骨的唐人气象为何充满激情与活力?除了其所吸纳的对象充满活力之外,还在于唐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唐代文人特别喜爱游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桑弧蓬矢,射乎四方”的志向。他们长期漫游在外,生活阅历空前丰富,所见极远、极多;所思极富、极深,眼界与心胸都堪称极大。游历之外,唐人还积极从政。从政的一个最大的好处便是可以深入社会的内部与底层。一个有为的时代加上唐人积极从政的主观能动性,唐代文人的内在能量便很容易地释放出来。
我们知道,唐代是个大气磅礴的时代。除了崇尚漫游、强调入世的生活方式外,其文化结构筑基于儒、释、道、侠之上。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来说,崇儒、崇释、崇道、都不鲜见,但真正任侠的却不多。唐代之所以任侠,原因有二:其一,大唐一统天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尚武习气被吸纳、发扬;其二,唐代经济生活繁荣,为侠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侠风日盛后,侠客们昂扬奋发的主观精神成了唐代文化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唐书》说李白“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即是一证。也是这个原因,陈伯海先生说:“任侠的风气大大激发了唐代文人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帮助他们在仕进时树立起强烈的功名事业感,而在退隐中的保持着‘不屈己,不由人的傲兀不平的气概。……唐诗倡导‘风骨,崇尚宏大的气魄和刚健的笔力,抒写英雄的怀抱,追求个性解放,跟任侠思想是一脉相承的。”⑤
通过以上的粗略梳理,我们大致理解了汉、唐两代如何因为“长安”这片热土以“老乡”的名义,跨越四百年,最终结为联盟,并生成一种新的精神,垂范后世。
二、汉唐精神的当下意义
对于传统,我们一直强调两个方面:继承与重建。谈论继承,我们必须明确“继承”二字不仅仅是态度、口号之类的问题,而且,可以说,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是一种能力,其次才是态度与方法。各种中国功夫都需要寻找传人。对传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素质和能力。否则便可能败了祖业。这一点,本来只是常识,却被很多人在“继承”这一伟业时给忽略了。这也是我在谈论汉唐精神的当下意义时不得不首先亮出的底牌。在明了这一切后,我才更想说,目前,最为急迫的不是重建,而是传承。因为,重建之事,非一日之功,需月积年累。这也是“汉唐精神”给予我们的最直接的启示之一。此外,“汉唐精神”的当下意义还体现在方法与思想诸方面。而以此切入当下中国画坛,我们便会发现,当代中国画创作,能够让人满意的作品少之又少。如此事实引来了许多批评家的反思。反思之中,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却在具体实践中缺乏有效性。那么,当代中国画创作究竟缺失了什么?这是个吓人的问题,也是个大得让人不着边际的问题。好在古人有盲人摸象的典故,我也只能就着自己摸到的象腿谈谈所谓的“象”吧。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画创作主要有以下两个缺失:
第一,有“物”无“事”。“事物”一词,“事”在“物”前。如果我们的日常创作中,仅有“物”而没有“事”,我们的创作如何才能完整?当我在大大小小、热热闹闹的各类展厅中,看到艺术家们的众多作品只有一个“物”——无论是否是写生所来的——时,我便感到死寂、感到匮乏。当我们将客观存在的事情和物体称为“事物”时,我们当然关注物体之“物”,比如柴米油盐,可是我们为什么关注?你可以说是“本能”。但仅仅有“物”是不够的。我们离不开“事”。关于“事”,哲学家的表述较为为全面。他说“意志的行为是事”。如果存在的一切是“物”,那么,意志的行为是“事”。一次创作、一件作品,仅有“物”而没有“事”,这件作品又如何从主体上体现艺术家的能动或说创作?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或说中国艺术讲究经验。日常生活中,中医、厨师、国画家等越老越吃香,不是因为他们年龄大,而是因为他们经验丰富,阅历宽广。读万卷书后,之所以还要行万里路,说得也是“经验”二字。而这众多的经验恰恰就体现在“事”里。我的一位搞诗歌评论的朋友某一天突然劈头盖脸地和我说,他终于想明白了“存在”。他说,所谓的“存在”就是“做事”。如果此言不虚,缺事或少事的创作是否是没做事?倘若没做事,是否就是不存在?缺少事情的作品之所以感动不了我们,之所以让我们在偌大的展厅视而不见,是不是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的不存在?
赵望云作品《陕南秋日小景》1973年
1936年,诗学家盛成在为画家赵望云的作品写评论时,曾有这么一句让我震撼的话:“白石翁画中有物,不爱摹古,望云画中有事更进一步。而且,这个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也是这个世界的事”。作为诗评家,盛成没有从哲学层面谈论事与物的问题,但其已经以诗人的敏感揭示出了“事”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说,事物之中的“事”之一维恰恰是艺术创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维,它包容了我们太多的艺术想象与艺术经验。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之所以优秀,并不在于他畫了什么人、什么物、什么地方,而在于他是否在作品中呈现出了自己的艺术想象与艺术经验。
当我强调艺术家们应该关注“事”时,并不意味着我不重视“物”——客观存在,我只是希望艺术家们让自己的创作时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世界关联起来,关联之后,我们才能有事可做。也只有做了事之后,我们的存在才会被证实,我们的作品也才会具备人性的温暖。否则,所谓的作品就是一尊石膏像,像则像矣,只是没有温度。
第二,黔驴技穷。黔之驴的故事,众人皆知,黔之驴的结果——被吃掉——也是众人皆知。由此可见,方法的重要。当我们在唐人气象中自叹不如时,我们是否思考过唐人于书画一道所创方法之多是其立世、传世之本呢?
唐诗的辉煌不必多说,单就书法与绘画来说,唐代书法家之多,书体之繁富,均离不开“法度”或“方法”二字。至于绘画,则更是博大。唐代的人物画成就曾令宋代美术史家郭若虚掷笔长叹:“今不如古”。有唐一代,无论宫廷画家,还是民间画师,皆具宗师气象。李世民的御用画师阎立本如此;出身下层的吴道子亦如此。其他如韩干、张萱、周昉、韩滉、孙位等皆可垂范后世。唐代人物画之所以有“吴带当风”之说,当然离不开“方法”。
同样是唐代,不仅人物画独立成科、山水、花鸟也各自成篇,王维是公认的的山水画南宗。同时,青绿山水也在大、小李将军的笔下成形。倘若缺少方法的多样性,不说唐诗,即以偏重形象的绘画言,所谓的“外师造化”便难以施行。因为,“方法”不仅仅是处理事物的办法,而且还是观念,是观照万物的一种态度。
反观当下,绘画名目之多,画家级别之高、人数之多,其创作却不令人满意。如果走进近几年的全国美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招式以及凝聚于这些招式中的巨大工作量。但却很难说其是“方法”。因为真正的方法往往就是一种观念。没有观念,或者换用古人的话说,没有能够有效得到心源的“方法”,即使是一种小“方法”,也终究是把戏,是黔驴的叫声以及吓唬人的尥蹶子,长久不了。很多画家的创作之所以昙花一现之后,就开始自我复制,正是因其缺少带有观念的“方法”而致。
由于方法、观念的缺乏,汉唐精神中的“风骨”、“气象”也就难以在当下画坛着陆,所能有的大概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绮碎”——看似繁富,实际却只是热闹。
事实上,汉唐精神所包孕的“风骨”、“气象”都是在“诗言志”这个平台上展开的。游历、出仕中,唐人的社会生活中处处闪现出志气的光辉。而当下的画坛,已经远离“言志”传统,惯性创作,复制自我,不一而足。
古人说:“诗言志”。可是,由于“诗无达志”的存在,所以前人对于“志”的理解也主要有以下三种:记忆、记录与怀抱。由于怀抱之不同,艺术也就有了百花自放的局面。当我把“诗言志”的“志”主要理解为“怀抱”时,那么,我问艺术家的是:在程式化的笔墨构成中,“怀抱”在哪里?当代多数国画创作不感人的原因之一,便是其创作有技术、有符号、有程式,却缺少“怀抱”。徐渭、八大、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大写意花鸟之所以感人,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怀抱”在。同样,徐渭,尤其是吴昌硕之后,大写意这一谱系里,之所以会出现一些有大笔而无真意,终至草率,粗疏甚至野鄙的画家及画风,就在于“怀抱”的缺失。
八大山人作品局部
“怀抱”之所以会缺失,当然与艺术家们的阅历有关。当我们都说“生活就是艺术”时,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在生活之中的“怀抱”,而不是油盐多少钱一斤的问题。当我们过多地或说斤斤于油盐多少钱一斤类的问题时,我们具有日常生活的细节,却不具有日常生活的艺术。因为,那些生活的“细节”淹没了我们的怀抱,它让我们迷失。
当我们强调“诗言志”必须有“志”可言时,还有一个相关话题,那便是“诗画同源”。自王维起,许多文人画家往往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来标榜。但是,如果认真研究王维的诗歌,这个命题其实是個伪命题。也就是说,王维诗歌中,那些真的可以画出来的诗歌,并不是王维诗歌中的上品,而是等而下之的。王维留下来的诗歌作品中的大部分好的诗歌都是不可画或者画不出来的,是“只可意会”的。
故此,当我强调“诗言志”在今天的意义时,作为艺术家,我们首先要养育自己的“怀抱”,否则,便会缺少叙说的目标。那么,如何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有我们所不能的,我们必须远离那些我们不能画的东西。当一个画家知道什么不能画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怀抱”,他也基本上可以“言”了。
“汉唐精神”以其博大、雄浑、包容、开放的气度成就了诗歌、书法、绘画的辉煌。那个时候,很少地域画派,而是以一个时代的形象和力量推动历史。如果说要有启发,这也应该是我们最应反思的一个方面,它以团队的形式强调个体,以个体的姿态守护团体的博大,进而辉映了一个时代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化星空。因此,“汉唐精神”不完全是汉、唐两个朝代的概念,而是一种恒久的审美精神、审美品格。对于我们,它的意义不是某个久远的历史朝代,而是一种永恒的精神标高。蕴于其中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强大的凝聚力以及自由奔放的精气神或许正是当下画坛最最需要的安神补脑液。
徐渭作品
注释:
①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东方出版社重心,2007年8月第2版,第6页
②诸葛志《中国原创性美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214页
③④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东方出版社重心,2007年8月第2版,第9页
⑤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东方出版社重心,2007年8月第2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