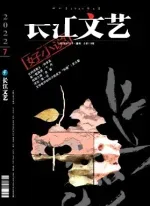通俗的美(8首)
□宋 尾
隐喻
那段时间我疲惫不堪,
为一些不擅长的事。
受困是痛苦的,
为欲望工作也是。
那些日子,有条鲫鱼
寄养在我的阳台上。
我喂养它,一周换一次净水。
它活了下来,鳞片
渐渐透明。有时我能
从那种空洞里看见自己。
某天早晨我发现
它失踪了。
除了一些水渍
留在地板上。
窗外一只红尾鸟
在树林里掠飞。
这是真的,那天
我看见一条鱼飞了起来,
一支喙啄着它。
告别
一个六岁的男孩
躺在病床上,两年来
他从病痛中理解
自由是什么,
失去又是什么。
怜悯则是另一件事。
应当说他懂得的不少了,
但不包括告别。
他躺在床上,像晚饭结束后
不得不返家的朋友那样,
他伸出手说:
爸爸妈妈,再见。
陌生
父亲去世后,我从
废弃的衣柜
翻出一张黑白照片:
一个比现在的我
年轻十几岁的青年人
在失去背景的旷野
凝望我。
这理应是我最亲的人,
这曾是我最憎恶的人,
这是一个比他本人
生动得多的我从不知情的人。
阴影
我一直在找一首诗。
它栽种我,让我生发,
我的气味吸引附近的蝇蝶;
而我的脚跟滋养蛆虫。
我展示极尽的我:
一边美好,一边恶臭。
我是我的镜子。
我是自己的季节。
但不会成为河流。
我仍然渴望因它流经
使我拥有湿润。
当我死去,还有
树桩和根茎留在这里:
它的一部分会被发现
另一部分陪我站在泥里。
失眠者
又睡不着了,干脆
泡一壶熟普,边喝
边兑上点果酒。
事物复杂一些兴许会更好呢?
对睡眠而言,你失去
它往往不为
什么特别的事,
只是你对自己失去了控制。
活着没啥大事,
他们说,除了生死。
等着衰败,等着
人生慢慢堆积起来,
再等它们自个儿消逝。
窗外,槐花圧满了枝条
也就这几天的命。
可这样的夜多甜呀,
四月真香!它提醒你
一月倏忽如一日。日子
就是客厅的地板,
注意时它脏
不关心它就变得干净,
但总归是平整的。
这个年纪,睡不着
是可以想象的。
适应了生活的褶皱,
接受了原来不能接受的。
我为我干一杯,能够
活到此处是侥幸。
婚姻我有,孩子我有,
与庸者比邻而居,
一个成功的失败者
是完全可以容忍被忽略的。
端午夜归
朗诵会结束后
我们在北碚的酒吧附近消夜
可一些念头在返程路上
仍不会有定论
这才合乎逻辑
你看看,我们
一边拒绝统一
一边按标准活着
这大概是我这么些年
头一回这么晚回家
你们在车上议论某事时
我望着窗外开阔的黑暗原野
紧紧抱住自己的禁锢
自由是多么狭小啊
这晚真是爽静啊
小区里,雨后的树木
如同一条路
逻辑
这里的人习惯说
自己是江的子女。
他们这么说时似乎就将
那条江挽在手上。
在我出生的地方有许多湖泊,
不大可能数得清。
离家不远有一条人工河,
一条县河,全部连向汉江。
可我觉得我从未得到
也不可能得到它们。
拥有一条江是奇怪的。
我是说,
拥有是奇怪的。
这样一个年纪
我已经不大可能得到我想要的事物。
就像我再也不可能青涩
我也不愿再重复。
但我一遍、一遍地重复更多的事情:
买菜,擦地,关窗,冲洗碗碟
有些时候越是无用的重复
就越是必需。
我出门时,带着家的气味
我一边走,一边
窥视着前面的女人
我越来越喜欢那些通俗的美。
我和其他人不会靠得过近。
我发现一些污秽
但可以不清扫。
在白天我被出租到某处
傍晚,我抱着我返回。
我的欲望降低
我惧怕情感。
在公交上我见到许多人的脸,
我深刻记下他们的特征
凌晨时他们站在窗口,鱼贯进入我:
我拥有如此之多。
但我不会再年轻,也不可能更成熟
事实上我从未得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