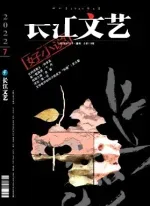二十岁书(8首)
老狗之死
在父亲不经意的描述中
这几年,它越来越害怕响声
那是一个雷雨大作的夜晚
父亲已记不清听到过什么
很多细节只能靠想象来补充:
它在颤抖的雷声中挣脱了铁链
一跃而起,从院墙头俯冲而下
正如我多年前见到的
它年轻时迅捷有力的模样
可这一次,石头绊住了链子
也绊住了那条不再坚硬的命
在这个漫长的秋天,我常常梦见它
梦见它悬挂在院墙头,就像
一个不堪老病而上吊的人
就像一个秋风怎么吹也吹不落的
野柿子。指着那个空荡荡的窝儿
在日落后越来越浓的黑暗里
父亲又一次提起它,还是那句话:
“十三年了,都没给它取个名字。”
四季断章
一
一觉醒来,金属窗外,鸟鸣在城市上空升起
我从梦中抽出四月的柳枝,那些环形和空白
依旧柔软。像从未折下过。吹开你的眼睛
吹开一扇虚掩的门,春风回旋于清晨的广场
“有什么正在降临?”香樟树的叶子光亮如新
小雨过后,我的渴望绵薄而消瘦,一如昨夜
“直到宁静的日子成群,结队走出霜和灰烬。”
二
让我们领受月光的雕刻,“寂静,如此完整”
用手指缠绕一片吉祥草,反复松开,而你
诞生于彼岸的路灯下,正练习七月里的蝉鸣
在夏夜,类似的游戏总是充满了原始的诱惑力
“回到从未出世的孩子,让我们长出星辰的翅膀。”
当慢跑的人群游入灯火,我听见体内有潮汐应和
三
阳光透过来,黑暗敛进空壳,面对偶然的晴天
最好的交谈莫过于鸣叫,用很大的声音,说出
很小的意思——我们的夏日短暂而自由,我们
昼夜喧哗,栖身于同一棵树的两面,却不必忍受
失语的折磨。而十月易碎,穿过连日的荒芜
我看见,这个秋天,翅膀和落叶的脉络那么相似
四
黑夜长于白昼,玻璃窗的水雾记载消失的秘密
我开始频繁地惊醒,每晚被墙壁上的黑洞窃听
就像一个农夫,在阴影里用力抖落身上的尘土
我多想告诉你,入冬以来,我一直关心着天气
“你会不会从一片空无中,踏雪归来?”
十二月已过,总有一些事物我们不能亲手埋葬
冬日何其漫长,我这里一片白茫茫的,还是没有下雪
清晨的楼道
寒假的最后几天开始失眠
先是听到凌晨五点半的脚步声
父亲的旧皮鞋沿着楼梯一路下去
每隔一层他就吹一声口哨
仿佛能够吹去额头上的皱纹
然后是对门的男人六点出门
每隔一层他就咳嗽一声
仿佛能咳尽多余之痰
最后是七点一刻
母亲在楼道遇到另一个母亲
两个人各提一袋垃圾下去
没有发出其他声音
K1848爱情故事
在火车上,和一位朋友
聊起爱情,她说,她爱上了
她们乐队的一个男生
是那种挥之不去的爱,那种
从未在别人身上点燃过、印证过的
爱,那种这个年纪
一旦溜走,再不会卷土重来的爱
她说,那家伙的小提琴呀
拉得比她还好。她说
那家伙,是台湾来的交换生
她顿了顿,很平静地补充着:
两个月前,已经回去了
“爱情啊,真他妈像这火车。”
我俩都笑了,仿佛在笑另一个
不相干的人,笑言情小说里
一个用滥了的不值一提的桥段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她不再说话了,目光躲向车窗外
当火车驶入隧道,寂静的黑暗中
她又说起平安夜,她送给他
一个刻着自己名字的,苹果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苹果!”
她像小孩子那样骄傲地向我宣称
“哇,后来呢?”“后来啊……”
“他说——谢谢,谢谢。”
二十岁书
这一年,父亲在工厂上班
还没收获母亲贫瘠的爱情
这一年,祖父在田间劳作
向地下发狠的锄头隐喻了某种命运
这一年,一根火柴,在我身体中
擦亮,我依旧无法理解,黄昏时分
他们朝向窗口抽烟的姿势
这一年,飞逝的旧照片排列有序
昨夜的雨,顺着屋檐没入今天的草丛
一个人在雨水中现形——清晰而疲惫的肉身
这一年,隔着空无,我和我的敌人
握手言和,并互相祝福
房子或废墟
找到一所房子,一张床
合上窗帘,最后是轰然一倒
窗外的大风大雾都睡着了
最高的那截树枝戳痛了星星的眼
灯火在人间,鬼火也在人间
那么多的生死在夜里发光
我想要的,只是在黑暗中
指出每一件家具的位置
只是给空荡荡的身体
塞一颗不大不小的魂魄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所房子
只有一次出现在这一首诗里
好像有人在说,真遗憾啊
他一直在找的那所房子
不过是一片遥远的废墟
雨在途中
雨在途中而我已经来了
来到那棵谜一样的树下
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
和一切期待无关
和那场还在途中的雨无关
我来了,爱惜羽毛的白鸽没来
我来了,赞美晴天的游客没来
雨在途中,公园空荡荡
一个人站在那棵谜一样的树下
一边担心着雨不期而至
一边担心着雨,永远在途中
左手边的抽屉
熟悉的地方布满了陷阱
比如香樟树下,比如一座
阴天的广场,比如此时此刻
我正缓慢地打开左手边的抽屉
仿佛雷雨之夜听见有人敲门
你说,多么日常的战争啊
时间像堡垒一样轰然倒塌
你说,这浑身的淤青该如何收拾
在我还没染上任何坏习惯之前
我也曾火急火燎地打开过另一个
左手边的抽屉,那些小纸条
那些从学校小卖部买来的小玩意儿
那些一分五分的小硬币
都在一片仁慈的黑暗中发着光
那时我还年幼,还不知道
那个左手边的抽屉有多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