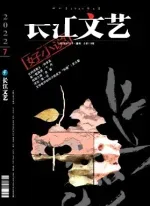忧伤的夏小姐
1
高中毕业后,我在小城里开了几年的士。
在等待放榜的那段日子里,父亲突然走了。面对惶恐不安的母亲和妹妹,我收起了三流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跟着师傅跑起了出租。
师傅是我家远亲,对我不薄,别人每天交两百二十元的租子,我只用交两百,不过,这依然改变不了那个即将沉底的家的命运。我害怕看到母亲哭泣的眼睛和眼看就要学坏的妹妹,每天踩着点回家,迅速溜进房间,关上房门。
这个夏天,父亲的出走成了整个小城的一个笑话,他和一个流浪到本城的东北女人走了,而那个女人大他十七岁,对于一个少年来说,这不是什么让人感到光彩的事。我主动跟所有的同学切断了联系,他们都上了大学,无论是985、211,还是其他什么野鸡大学,都无一例外的在朋友圈晒起了新生活和新朋友,我每天都会看看,但从不点赞,也没回应他们的问候,就这样,我几乎不再与人说话。我每天游荡在大街小巷,有时候烈日炎炎,街道空无一人,有时候突然飘来一片云,下起倾盆大雨,我在树下躲雨或歇阴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胸中的忧伤和过盛的荷尔蒙就要喷涌而出。可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发泄的对象。
直到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遇到了S。
S是我的一名乘客。我是在夏天遇到她的,姑且叫她夏小姐吧。
八月底的时候,小城依然很热,太阳把街道都灼伤了,整条整条的街道寂静无声,偶尔驶过的一辆小车也都是悄无声息的,我绕着小城跑了两圈,都没有遇到一个顾客。等我再次经过东寺街的时候,远远看到那棵大泡桐树下站着一个女孩,戴着炫彩的大蛤蟆镜,穿着吊带衫和短裤,正低头摆弄手机。出于职业本能,我远远地踩了一脚刹,车子慢慢溜过去,女孩看了看我的空车,又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大街,漫不经心地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室里。
到哪里?我偏头问她,看到那一片白花花的大腿。有点炫目。
她嘟噜一声,报了个地名,仍然头也不抬地玩着手机。
她多大了?干什么的?车子右转的时候,我又趁机瞟了她一眼,那两条腿上的胶原蛋白像是要胀破皮肤,我怀疑捏上一把的话,挤出来的很可能会是蜜桃的汁液。她等车的那块,基本上都是民房,可民房后隐藏着几个洗头坊,进进出出的都是些年轻女孩,同门师兄弟有几个固定的客户在那里,晚上不方便的时候,一个电话来,师兄弟们多远都要赶去,穿过大半个城市,把小姐们送往各大宾馆的软床上。至于她们是怎么结算包车费的,我从来没问过,但从他们嗤嗤的笑声中,我体会到了一股带着汗液的暧昧不明气息。她是干什么的呢?会不会成为我的固定客户呢?
我正胡思乱想着,她的目的地到了,趁她下车的时候,我又贪婪地看了一眼,齐屁小短裤连屁股都没盖住,露出两个半月形,更让人想入非非,脖子扭酸了,我只好把目光收回来,转动方向盘的那一刻,我看到她朝一个高档小区走去,苗条健美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绿树丛中。
从那以后,我多次路过东寺街,不同的时间,早晨,中午,傍晚,午夜,不同的天气,晴天,下雨,刮风,我再也没遇到S,直到那天,整个城市突如其来地下了一场迷雾。
那天晚上十点多,高中学生正下晚自习,我送了两个学生回家,又路过S去的那个小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下雾了,但还没有显现出异样。我下意识放慢车速,希望在路边看到S的身影,还真巧,在车子即将要开过去的一刹那,我看到漆黑的树影下站着一个女孩,她穿着短裤长靴,外面套着一件雪白的羽绒服,如果不是白色的羽绒服引起了一丝反光,我真有可能错过她。我把车缓缓停在她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装作休息的样子,摊开四肢,降下车窗,从后视镜里悄悄观察着她。她仍在低头玩手机,看上去不太开心,微蹙着眉头,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划动着,对停在不远处的我浑然不觉。过了几分钟,她突然抬起头来,向四周扫视了一眼,——那紧锁的眉头依然没有打开,她朝我的车看过来,我连忙心虚地低下了头,用左手不自然地挡了一下额头,——可这一切都是徒劳,她根本没有看到车内的情形,她那一瞟是茫然的,就又继续玩起了手机。她在干什么呢?等人吗?这么晚还出去?一连串的问题从我脑海里冒出来。不一会儿,她抬起头来,一辆小车驶入她的视线,她拉开车门,坐了上去。来不及思考,我已发动了车子,悄然向前面驶去,从后视镜里,我看到那辆车正在掉头,看不清车牌,但庆幸的是此刻街上的车并不多,而这样白色大个的豪华越野也并不多见。为了避免惹人怀疑,我没有跟着掉头,而是加速向前面开去,三十米后,我猛地右拐,那是一条不太宽敞的单行道,但此刻应该会畅通无阻,出了这条路后,再右拐,如果够幸运的话,我或许可能会碰到左拐的那辆越野,当然,它也有可能会右拐,但我当时就是那么判断的,它应该会左拐。果然,当我抢先一步到达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看到后面缓缓驶来一辆白色越野,正是S刚上的那辆车。
我的心开始怦怦跳动起来。我才意识到,自己会在一刹那作出准确的判断,完全是因为这是开往东寺街的路,她会去那里吗?她真是小姐吗?突然我全身的血液都涌向了下体,等自己意识到时,双手已在屉斗里翻找起来,——今天的运气不佳,现在才一百多块,连交师傅的租都不够!可她真的是小姐吗?她的价码是多少?一千?两千?还是两万?我没有过这方面的任何经验,可凭借一个少年的热情,如果我有两万块,我真会全部揣上找她去,我会把那两万块砸在她脸上,一边抽她耳光,一边跪在她的脚下。
我双手扶在方向盘上,神经质地抖动着,多少年来,我一直有这个毛病,每次考试要作弊就手抖,结果总是还没下手就被老师发现了。我紧紧盯着红绿灯,开始倒数了,三、二、一……可我没有马上启动,我慢悠悠地踩住脚刹,然后慢吞吞地挂上挡,果然那辆越野车从我旁边超了过去,——我依稀看见里面有一个穿白色羽绒服的身影。我的心又开始怦怦跳动起来,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坐立不安了。我轻轻踩了一脚油门,悄没声息地跟了上去。果然,S又到那棵大泡桐树旁下了车。她打开车门,从上面轻盈地跳了下来,径直走进了一条小巷里。
那个男人把车停好,也下了车,他一边锁门一边朝四周看了看,我只好把车慢慢朝前开,——在心里已把他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个遍!可那个男人朝四周看了看,见四下里无人,就走到那棵泡桐树下,解开裤子,掏出自个儿的家伙,对着泡桐树撒了一泡尿。难道不是一伙的?不进去了?我把车停在斜对面不远的地方,看到那个男人提起自己的裤子,抖了抖——挂在上面的钥匙叮叮当当一串响,然后,穿上裤子,回到车里,发动车子,一溜烟开走了。
原来只是个专车司机!我长舒了口气,立马原谅了他抢了我生意的事实。
我把车子缓缓掉头,停在斜对面的树荫下。不知为什么,我决定等她出来,要等多长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要到凌晨?我不能想象凌晨回到家的时候,连两百块的租子都拿不出来时母亲会是什么表情,但我还是决定等下去。
没有那么久,半个小时后,S出来了,这回她没有玩手机,她背着双肩包,心事重重地从巷子里走了出来,我的心又怦怦乱跳起来,我手忙脚乱地发动车子,又拼命按捺住兴奋和焦急,慢吞吞开过去,装作路过的样子,在她身后五米远的地方按了一下喇叭,她漫不经心地回过头来,——脸上带着疲倦,似乎又神游了一下,——然后缓缓朝我招了招手。
2
去哪儿?我一边按下空车牌,一边趁机大大方方扭过头看她。不得不说,她比我那些同学晒的新女友漂亮得多。但她可能比我们大一点。不要紧,现在不是流行姐弟恋嘛。我一边开车,一边没有一刻耽误地想入非非。
朝前开吧。她伸出手指往前指了指,然后转弯,转弯,再转弯。她在半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我听明白了,绕老城区转一圈?我问她,不外乎是想展现一下自己的智商。
她没有点头,也没有微笑,只是扭过头来看了我一下,——这是她第一次看我,我在心里比划了一个“yeah”,——我猜这一眼的印象应该不坏,我长得不丑,而且年轻,干净整洁,看上去应该有异于其他的的士司机。但她的眼神冰凉,像是拿冰烙了我一下似的。
她似乎是在找人,车子开出一百米后,S坐直身子,看到有一闪而过的行人,便努力扭过头去辨认。可惜这时候,街上并没有什么人,一圈转下来后,才看到三个人影,其中还有两个是一对中年夫妻。
车子绕老城区转了一圈后,她没有要下的意思,于是我把速度放得更慢,又转了一圈。就是这时候,雾突然下大了,越来越浓,十米之外,便什么也看不清了,起初我以为是室内外的温差造成的,把空调扭大了些,可是渐渐连五米之外也看不见了,我突然意识到是这城市下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大雾。浓雾使对向的车辆只能看到两只模糊的大灯,抹去了两旁的建筑、树木,更是抹去了路上所有的行人。整个车辆如同行驶在古龙小说的神秘氛围中。
我打开双闪灯,摸索着开了一段后,只好放弃了,我把车停在一个新建的小区旁,那儿道路宽敞,还有新修的高大的路灯,看上去是比较安全的。我扭过头跟她说,还是等一会儿吧,这会儿实在是不安全。她脸上的疲倦没有丝毫减轻,但神色似乎安定一点儿了,她点了点头。
看见她的表情稍微松弛了些,我鼓起勇气,试探着问,怎么,你是来找人的吗?要不,我待会儿帮你找?——一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这不是我,太多嘴多舌了,但她却没有多想,点了点头,继而又摇了摇头,你又不认识他,怎么帮我?不过,你可以开得再慢一点。
或许,你可以给我看看他的照片?由于内心的窃喜,我又往前试探了一句,可她还没来得及回答,窗外有个男人的身影一晃而过,突然间,她就推开车门追了上去。
男人个子很高,身板笔直,走起路来有一股洒脱不羁的风范。路边残雪未化,他却披着冲锋衣,露出格纹状的米色围巾,寒风吹动他的衣襟和一头灰色的头发,很是有几分迷人,可他却似乎浑然不觉,双手正插在口袋里低头疾走,一边走路似乎还在一边思考什么。发觉身边多了个人,他吃了一惊,但不得不说,他吃惊的样子也挺迷人的,当看清是S时,他小跑起来,显然想甩掉她,但S也跟着跑起来,他一边跑一边扭过头来对S说着什么,脸上的线条依然那么柔和,但几米之外,我依然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冷峻和坚决。——S似乎又焦躁又伤心,她一边申诉着什么,一边想去拉他,但男人连连甩掉她的双手。
两人拉扯着很快消失在浓雾里。只留下我目瞪口呆地坐在车里,我沮丧地坐了一刻钟,需要花点儿时间理清关系,和平复一下我的心情,还要去追吗?照这么看来,她不是干那行的,可谁知道呢?谁说小姐就不能有男朋友呢?我的心情一瞬间像从塔吊上跳了下来,要死不活地躺在地上,我不希望她是干那行的,直觉也渐渐告诉我不是,可如果真不是,就我这么个的士司机,要想跟她发生什么是不可能的。我狠狠踢了两脚车门,恨不得把这破车踢垮,心里对这世界的恨意再次燃烧起来。
我驾驶着车,心烦意乱地在大街上游荡着,连有人拦车也不想理。突然一转弯,我扭头瞟到了副驾驶座上放着的双肩包,我差点没捡起来抱着痛哭一场——S的包掉在车上了!我终于有理由找她去了!
此刻,我的心情就像一个瘪了的气球,正被气筒滋滋地打着气呢。什么也别说了,开着我的小破车,找她去。我在前面第一个十字路口找到了S,那男人不见了,S正一个人孤单往前走着,我冲她按喇叭,大声说,你的包!她扭头看了看我,又回到了我的车上。
带上你去找他吧?看见她一脸的忧伤,我忍不住说。
好。这次她又扭过头来看了我一下,好像在心里已把我当成了同盟军。我不由得又在心里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我尽量把座椅调前,眼睛都快贴到窗玻璃上了,硬撑着慢吞吞往前开。
刚才,那个十字路口,本来已经追上他了,可他突然小跑起来,我有哮喘,我故意说你别跑了,我跑不动了——其实我也真跑不动,但他却突然加起速来,我看着他的身影,以为他会停下来,或者会回头望一望,但他没有,他的背影很快消失在雾里了,就像被浓雾吞掉了一样。我走到他消失的地方,以为他会在某个角落等着我,以为我一转身,就看到他在某个角落冲着我笑……但是没有,他彻底消失不见了。
她又接着往下说,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以为往前走十米、二十米、五十米,就会找到他,但是都没有……街上没有人了。雾太大了。
你们吵架了吗?我小心问道。
没有,我们没有吵架,只是,她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缓缓说道,只是我怀疑他有了其他女人。
啊,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还找其他女人?那该碎尸万段了吧。我看着她。
她冲我失神地笑了笑,说,他是个编剧,一个才华横溢的编剧。
所以?编剧就该和其他女人……我皱紧了眉头。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去喝一杯?她偏了头问我,说着就要拉开车门,我当然没有理由说不,不是每个夜晚都会有艳遇的。
3
我们在路边不远的地方,一排杉树林后,找到了一家小酒吧,一进门,她就在不多的几个顾客脸上搜寻起来。看来,这也是他常来的地方。
我们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来。她熟练地给自己点了一份“红粉佳人”,很快用花式手法点上了女式香烟。我则看了半天酒水单,给自己点了一杯“教父”。可上来后,却发现很烈。
怎么样?不好驾驭吧?她看着我,像是看到了我隐隐皱了皱的眉头。
嗯,不太好喝。我只好老实回答。
她点了点头,把面前的“红粉佳人”推给了我,接着便端起“教父”一饮而下,休息了片刻,她打了两下响指,酒保又给她送了两杯“教父”过来。然而她却不喝了,只是低头把两只盛满酒的杯子碰来碰去,有些许酒水洒了出来,汇集在一起,映照出一张美丽却失神的脸。
你常常四处找他吗?坐得太久了,而酒吧里仅有的几个顾客也陆续走掉后,我试探着问。
不,她摇了摇头,长长吐出一口烟雾,那口烟雾也跟着她的头晃动起来,像是一只在摆尾巴的鳗鱼。大多数时候,他是在家写作的,埋头苦干的那种,你知道吗?我也正是因为如此才爱上他的。
她窝到沙发里,陷入了回忆之中,也许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她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有一阵子,我姑妈家拆迁,租了东寺街的一套民房过度。他正巧也住那栋,他住的是一楼,我常看见他在院子里画画、读书,或者和他的朋友聊天。三楼的露台上,有他种的葡萄,他常上去浇水,我们在楼梯上碰到过几回,在侧身而过的时候,他会冲我笑笑。他笑的时候鼻梁会微微皱起来,眼睛里流露出温和的光,他略显灰白的头发在风里飘动着。
他是才华横溢的,但他,或许生不逢时,你懂吗?她在烟灰缸里摁灭了烟蒂,用涂着黑色指甲油的指头失神地拨弄着里面的烟蒂,已经有七八支之多了。
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才能准确无误地明白他的才华呢?
有时候我在楼上看他们聊天,看着看着就入迷了,一坐好几个小时,姑妈端水果来都忘了吃。他们毫不在意多了我这么个迷妹,旁若无人地争执、大笑,连荤段子也照说不误。
有时候他们会产生分歧,对他的作品或某个剧作家的作品,有时候他听着,抽着烟,间或点一点头,有时候眉头一皱,眼中流光一闪,说,不,然后缓缓吐出一口烟,把眉头舒展开,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慢慢地说,但每个字都很有力,开始还有人反驳他,但他把他们一一都驳倒了,最后,就只有他一个人说了,他们都打起哈哈,喝茶或者逗起了烟斗。烟斗是他养的一条拉布拉多犬。
天晴的春末,或者夏天的傍晚,他常在院子里画画,除了偶尔抽一支烟,他几乎一动不动,那时候的他是那样的深邃和孤独,仿佛天上最亮最寒冷的那颗星,产生了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只有烟斗,靠在他的脚边,在太阳光里打盹,它和他一样,深邃、孤独、帅气、迷人。
——我以为他的朋友会越来越少,但他们常来常新,老朋友带新朋友来,有时候还带来年轻漂亮的女孩,有一两个是出演过某个小角色的小明星,每次来,都是一场盛大的聚会,从中午闹到午夜,喝酒、唱歌、跳舞、论道——他们是那么快活不羁的一群人,幽默、洒脱、睿智、特立独行,是我向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的中心,——在此之前,甚至到现在,父母是把我管得很严的——而他是他们的中心,灵魂人物,这么说你明白吗?你相信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编剧吗?
她的闪着光的黑眼睛看向我,我正要回答,却见她眼里闪过一丝羞怯的笑意,突然说,他最讨厌别人用这个词了,弥漫着一股淫荡的味道。
啊?我一愣,紧接着又笑了起来,说,被你这么一说,似乎还真有点这种味道。
她笑了,笑容转瞬即逝,但苍白的小脸似乎慢慢恢复了一点血色。她又点燃了一支烟,夹在枯瘦的手指尖,再次冲我笑了笑,然后又开始了讲述。
很快,我迷恋上了他,一天看不到他就觉得坐立不安。于是,我找各种借口频繁地往姑妈家跑。有一天,我们再次在楼梯上相遇的时候,他突然猛地把我按在墙上,抱住我的头,狠狠地亲吻了我。——而姑妈就在走廊上浇花,她乒乒乓乓地把铝制铁桶弄得响,而花盆里漏出来的水滴滴答答滴到了楼下,她再往前走两步,就有可能看到正在亲吻的我们,可我们都是如此地忘我,不愿松开彼此。也许,我眼里流露出的仰慕,早就被他一网打尽。
从这以后,我的心像长了翅膀似的,无时不刻不在欢呼雀跃,走路轻盈得像是在跳舞。我找更多的借口更加频繁地往姑妈家跑,可他再也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举动,有时候我在楼上看到他和一帮朋友在一起,他冷冰冰的,没有表露出认识我的样子,只是聊着聊着,他会突然冲我眨一眨眼睛,轻微到你以为只是不经意间眨了下——只是不知为何单单眨了一只。但我知道,那是我们之间的暗号。
可是好景不长,姑妈很快搬走了。我没有理由再往那里去了,如坐针毡般地过了三天后,我做出了一个惊人地决定。她吐出一口烟圈,看了看我,眼里没有丝毫的羞怯,而是大大方方的坦诚,不得不说,除了爱慕,一股敬佩之情从我心底升腾起来。
我把那套房子租了下来,姑妈的那套,还有他隔壁的那套,只留着顶楼的,我想,不能太空了,生活在这么破旧,而又空空荡荡的房子里,一定特别无趣吧。我猜测,他是喜欢热闹的。
很快,我们在一起了,他的妻女在国外,几年前已办过手续,我也甩掉了我的那些小尾巴,起初,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非常。她又强调了一下,然后像是对自己的话表示肯定似的,点了点头,说,是的,非常快乐,非常快活……她像是神游了一下似的,明显地陷入了短暂的回忆中,我随着她那大眼睛里消失了的光,跟着她神游了一下,想象他们早晨、黄昏、夜晚纠缠在一起,在晨光熹微的早晨,坐在便床上,他搂着她,唱歌或是讲话……我不由得在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醋意。
我在黑暗里捏紧了拳头,想以此压抑自己翻腾起来的醋意和就要凸显出来的生理反应,可是我却又是如此地渴望她继续讲下去。
整个夏天,整条街道都摇晃着栾树的枝叶,那美好的夏天呀,真教人心旷神怡灵魂出窍。然而说出这句话时,她语调里的甜蜜在迅速消失了,她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瘦削的手,像第一场秋风吹过夏天的街道,我预感到,那些灰色的片段来了。
大多数的傍晚,我会坐在楼顶的葡萄架下,看一本书,打个盹,或者仅仅只是享受夜晚即将到来的清凉。然而很快,我发现不对劲了。有一天,我俯身在顶楼的栏杆上,看向小巷纵横交错的里弄,发现那里有一栋半新的楼房,怎么说呢?它为什么引起了我的注意呢,因为它完全有异于其他半旧不新的房子,一看,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有点花里胡哨的。我开始站在那里看,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这么一栋房子,它是用来干吗的呢?我一直站在那里,悄悄地观察起来。太阳开始慢慢收起了它的暑热,光线暗淡起来,我看见各个窗前有女人活动的身影,她们打着哈欠,洗漱,或伸懒腰,我好奇怪,为什么只有女人没有男人?但就在那一瞬间,我马上明白了,这是那种场所!我不禁笑了,没想到自己生活的小城也有这种场所,而且就和自己的住处隔得不远,真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当时,这句话就那么从我的脑子里迸了出来,我记得我还笑着抬头看了看那片蓝天。
夜色降临了,那栋房子亮起了灯,里里外外都闪烁着柔和暧昧的灯光,我看到有三五成群的男人进去了,也有一个一个的女人出来了,有一个女人,穿着素雅的旗袍,手腕上插了一朵红花,一步三摇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了,我的目光一直跟着她走到我家楼下,她突然抬头朝上看了看,——不知她是发现我在看她,还是怎的,她朝上看了看,我本能地闪了闪身子,躲到暗影里去了。这时,烟斗跑了出来,它围着她撒着欢,打着转,摇着尾巴,吠吠地吐着舌头喘着粗气,我虽看不清,但可以想象那大舌头上一定还流着哈喇子——烟斗是一只右后腿被人砸伤了的老狗,它患有轻度的自闭症,一般情况下,看到陌生人它是会狂吠的。
恰巧,编剧回来了,街上的路灯照着他的背,把他的影子投射到女人身上——我心里突然升腾起一种不能形容的妒火——他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样子,但那女人的脸正在光线里,——她正在笑,嘴巴斜挑着,眼角飞着,像一群飞蛾一样,扑闪着扑闪着,这里飞一下那里飞一下,——是那种风骚的女人被还看得上眼的男人撩动了的样子——我虽然年纪小,可是我懂!
我一刻也没有停,扔下手中还握着的水瓢,就冲了下去,可他已经回来了,已经躺在藤椅里看报纸了,脚边的地上就躺着那只要死不活的老狗,这个畜生,好像它刚才不曾对别的女人摇尾巴一样!
烟斗?烟斗是一只公狗,你也知道的,公狗会发情的,对一个浑身散发着荷尔蒙的异性,它冲上去摇尾巴流哈喇子是很正常的。
狗老了怎么了?狗老了还是有正常生理反应的。
他毫不掩饰自己知道她是妓女。你能看出来她是个妓女,我看不出来?我是个编剧呀。
我是个编剧呀,编剧当然要跟不同的人接触,跟不同的人做朋友,不然我怎么写作,怎么写出世间百相,写出伟大的作品?
他的话句句在理,可怎么听都像狡辩。
她停下来,头伏在桌上,把头埋在胳膊肘里,我问她,所以你们就吵架了?她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就为这个?——你看到他跟一个陌生女人说话?
她惨淡一笑,说,编剧有个习惯,每每上街看到陌生男女说笑,就喜欢编排他们,他会猜测他们是什么关系,正说着什么,打算去干什么,有时候他一边编故事,还一边捏着嗓子设计他们的对话。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把那些对话镶嵌在那些神态动作里严丝合缝,丝毫没有不妥帖的地方……这个习惯,终于也在这一刻传染给我了。
我开始想象潦倒编剧和落魄妓女的N个版本的故事。
也许那一眼只是个开头,把我和他之间的不信任给调动出来了。
可是我仍然离不开他,是自由对束缚的吸引?成熟对青涩的吸引?逾矩对禁锢的吸引?或许还有别的?对爱,对知识,对才华?我感到那吸引是致命的,是难以抗拒的,从脑海里钻到身体里,再不容分说地命令我的四肢。
有一天,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又从家里溜了出来,跑去他那儿。院门虚掩着,他正在客厅里赶稿子,屋角里燃着檀香,烟斗在他脚边打盹,一切显得是那样的静谧和美好,我特别喜欢看他安静做事的样子,那样子很迷人,也很能给我安定。那时候我们已经吵过很多次了,对于这段关系我已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不打算进去,只在门口站着,静静地看他做事。他时而皱着眉头抽烟,时而用脚逗一下烟斗,时而面色平静舒缓地敲击着键盘——我知道,那是他写得顺畅的时候,那时候他笔下的文字,一定像宽阔的大河那样,平静舒缓,从容不迫地向前奔流。
这样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的腿站酸了,走到隔壁房子里,之前跟你说过,我顺带也把这间屋子租了下来,这一带的房子建得很简陋,墙壁很薄,躺在里屋的床上,贴着墙壁,能听到他的呼吸声。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一声鹧鸪的叫声,那是他的微信声,我听到敲击键盘的声音停下来了,过了一会儿,鹧鸪又叫了一声,我听到拖鞋在地板上走动的声音,大衣架晃动,打火机脆响,拖鞋趿拉到门口,皮鞋摔在地上,紧接着铁栅栏院门吱呀一声,脚步声已经在巷子里响起来了,——我连忙从床上跳起来,扑到客厅里,透过院墙上的镂空,我看到他一边低头看手机一边笑了,——叼着烟,嘴角斜斜往上一挑,笑了。
这个笑容,我不想再诠释,我很熟悉,我想你也应该很熟悉,如果你谈过几次恋爱,如果你曾心仪过某人,并认真观察过的话,你会得出结论,这个笑容,只会给予异性。
我能想象得到,如果他面前有这么个女人,那么他下一步就应该会凑过去,在她脸上亲一下。
嫉妒之火再次点燃了我。我用还保留着的那支钥匙,打开了院门,电脑还没关,他正在创作那幕话剧,我无心光顾那波澜起伏的剧情,一心只想查看他的QQ和微信,可密码被修改了,恰巧此时,一封邮件来了——邮箱开着,我的手不禁颤抖起来——我可以看到他所有的来往邮件,也就是说可以窥见他内心深处的几乎所有的秘密,特别是他所钟爱的事业上的。
她停顿下来,像是用完了所有力气,头趴在胳膊肘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右手把香烟举在耳侧,烟雾在头顶缭绕,乍一看,脑袋像个横放着的香炉,呼呼冒着香烟——我猜,那一刻,她的脑袋里肯定冒出了什么可怕的念头。
她把烟夹在耳畔,像是忘了它的存在,没有再吸,香烟燃尽时,烧着了她的手,她哆嗦了一下,掉下一串烟灰来,她像是才从回忆中惊醒,在眼前的烟灰缸中摁灭了香烟,用迷惘的大眼睛扫了我一下,接着说,那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没错,我打开了他的邮箱,整个浏览了一遍,不得不说,他是幽默的,是迷人的,他的幽默风趣、洒脱不羁在信件里得到了更多体现,在阅读信件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开始,我坐在楼上,看着他跟许多朋友聊天。
他与出品人的往来邮件最多,看得出来,他对新剧满怀期待,那人我认识,夏天的时候,他到画家这儿来过几次,每次都带着不同的女人,少女,妙龄少女,他毫不掩饰他对不同女人的喜好。他常跟编剧说,去他那儿吧,然后冲着他促狭地眨眨眼,不用说,鬼也知道他在暗示什么。
我眼前再次浮现出编剧脸上挂着的笑容,那个风骚的暧昧不明的笑容,是那人带给他的女人吗?我知道,出品人正在竞争一个要职,我想都没想,就把我手中的照片——那人跟女孩们的照片,不是床照,但也足够亲密——申请了个邮箱,寄给了他们单位的公共信箱,我甚至都没为能引人注意而多写两句什么。但结果是,这封信真的给了他致命一击。
也许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吧。看到他潦倒的样子,我有一点点内疚,可还没等我把内疚平复,编剧就发现举报信是我写的——我甚至都没想过要抹去电脑上发邮件的痕迹。
你知道你毁了我,你知道吗?他坐在靠椅里,双手无力地支撑着头,我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你知道吗?得奖,成名,一举成名天下知,车子,票子,房子,女人……所有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你知道吗?
我惊诧地瞪大了眼睛,女人?
他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像是才发现我是个女人似的,不知是因为连夜的酗酒熬夜,还是因为梦的破碎,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眼角布满了血丝和皱纹,风度顷刻荡然无存,原来一个男人的精神支柱倒塌了,会带来这么可怕的后果。我害怕了,后悔了,想走过去,给这个软弱的人一丝安慰。
他却咆哮起来,我不能接受出卖我朋友的女人!你!你,教我如何……在世人面前立足?最后,他竟呜呜地哭起来了,你毁了一个有着卓越才华的编剧,你知道吗……
他的哭声让我心碎了,曾经我是一只小猫咪,现在却把狮子弄哭了,又痛又骄傲地情绪在我内心交织翻滚着……
说到这里,夏小姐停住了,袅袅烟雾后,她的双眼闪了一下,放射出一道怪异的光芒,小猫咪在舔嘴角的血吗?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但也只是模糊地一闪,是什么?我没理清楚,因为那让我心疼的忧伤又回到了她脸上。
你们就这样分开了?我问。
没有,她弹了弹烟灰,眼神又暗淡了,陷入了回忆之中,我终于还是没能抵御得了心中的爱,走过去,抱着他的头,眼泪很快滴落在他的头上。
可以想象后来发生了什么。我的喉结上下滚动得发疼,心里的那份孤独和爱恋鼓动着我,在我的身体里上蹿下跳得厉害,我强迫自己尽量不去想象,然后努力清了清嗓子,说,你们和好了?
和好了,可是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回不到从前了。
说完这些后,她抬起眼睛来看着我,希望我说点什么,可我该说什么呢?我想到了她眼里闪过的怪异的光,想到了哭泣的编剧……我把嘴唇嚅动了两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她失望地垂下了眼睛,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了浓黑的阴影。
走吧。说着,她就站了起来。
我们走到街上,雾依然很大,两三米外就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高大的树木、车子、房子,都影影绰绰,让我怀疑这整个晚上都不是真的,而我惟愿这一切继续下去,——我害怕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我的心一紧,紧走两步,拉住她冰冷的小手,她侧过脸来,我看到了她脸上挂着的泪痕,我再也忍不住,突然一用力,死死抱住了她。她在我怀里挣扎着,却激发了我从来都不曾退场的荷尔蒙,我抱住她的头,在她脸上狠狠“咬”了一下。
我陪你找他去吧。她渐渐平静下来,像一只用完了力气的鱼,在我怀里温软下去。
这天晚上,我们又手拉手围着小城走了一圈,当然没找到他,最后走累了,站在十字路口,我们不约而同地问对方:去哪儿呢?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去编剧家里。
吱呀一声,院门打开了,我问她,要是编剧回来了怎么办?
她说,你怕了?
我摇摇头,说,我不怕。
她说,那你怕什么?
我顿时就不怕了,因为我看到她像一只小鱼,褪光了衣服,光溜溜的钻到了被子里。
就这样,在这个迷雾滔天的迷茫夜晚,我献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声呻吟。
第二天早上,当太阳的光芒照到小屋里,照到我脸上时,我醒了过来,当我意识身处何处时,马上跳了起来,S早就不见了,我一边慌张地扣着衬衣上的扣子,一边扑到窗边看窗外的的士还在不在,那辆薄荷青色的的士正惬意地停在那棵大泡桐树下,一阵微风吹过来,树叶翻飞,我仿佛感受到了来自车子的愉悦。同时,我也看到床头的墙上贴着一张便签,上面写着:
夏天17
这应该是夏小姐早上贴上去的。这不是日期,也不是门牌号码,那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