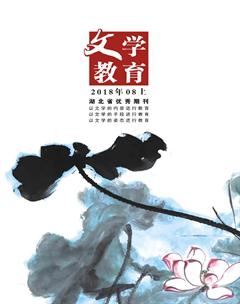僧人笔下的僧人:《徒然草》中所见僧人形象简析
内容摘要:日本虽然与中国一样,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但佛教在日本的存在形态与中国颇有不同之处,进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这是值得注意的。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作为一名僧人撰写的小品名著,其中对佛僧也做了许多记录,颇有助于认知当时日本佛教僧人的生活样态与佛教文化氛围,并进一步了解作为僧侣的吉田兼好自身的思想状态,值得关注。
关键词:日本佛教 吉田兼好 徒然草
古典文献是了解古人生活形态与古代文化氛围的最直接依据,而这种风貌的传达,又会因文献著述者身份、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随机性。即如古代佛僧的形象记录,在中国主要来自佛教内部的僧传史料,而此类作品为凸显其宗教立场,往往流于板正,缺少生活气息。而地域、国族的不同,也会影响到相关信息的传递,例如同受佛教的深刻影响,日本与中国佛教的历史形态就存在较大差异。日本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僧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中就记录了不少与佛教僧人相关的逸闻趣事,使得当时佛教界的众生相跃然纸上,较为直接生动的反应出当时日本佛教的历史形态,值得引起注意。[1]
一.僧人的生活日常
《徒然草》中记述了许多僧人生活世界的片段。与一般印象中整日吃斋念佛的枯槁形象不同,吉田兼好笔下的僧人生活与世俗世界并未决然分开。在第六十段就提到一位嗜吃芋头的真乘院盛亲僧都,该僧不仅平日爱吃芋头,在身体不适时也以大吃特吃的方式疗疾。其所有的钱财也都用来购买芋头。[2]这看似有违佛门禁欲节制的理念,却被视为是率性而为,非世人之常态。而法显思乡的故事也显示出日本佛教对情感世界的认可,法显西游天竺,见到中国来的绢扇,内心悲伤而病倒,想吃汉地饭菜。世人认为这是多愁善感,而日本僧人则认为这是“可亲的真性情”。[3]
在这种肯定感性生活的氛围中,也出现了沉溺于酒色财气的情况,第五三段有载,仁和寺一名童子在饯别宴席上喝醉酒,“将身旁一只三足鼎取来往头上戴”,由于鼎口太小导致无法取下,最终想尽办法才将“头拔了出来,但耳朵与鼻子都残废了”。[4]吉田显然对醉酒之事是心存反感的,认为烂醉如泥是“不堪入目的恶俗样”,不过现实中却常常见到“身着袈裟的年长法师,扶着小童的肩,满口胡言、步履蹒跚,看着让人心生怜悯。”[5]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佛教的戒律是十分松弛的。
在戒律松弛的情况下,僧人做出世俗化的行为就难免了。书中提到僧人攀附权贵的活动,其云“世间权门,声势显赫,遇有喜事、丧事,则众人皆趋之若鹜。但以佛门高僧之身分,也随俗流而登门求见,甚不可取。或者事出有因,但出家之人,实宜远离众人。”[6]除奔走于世俗之外,也存在僧人改换门庭的情况,如第一六五段提到:“离开本寺、本山去加入其他显教、密教之僧人,凡此种种背弃了自己原有的习俗环境,而与他人交往者……”[7]
甚至于情色、命案等事件在僧人的生活世界也有出现。如第五四段提到,仁和寺的法师们为邀请某秀色童子外出游玩,费尽心机而落得败兴而归,[8]以及第九〇段写大纳言法印的童仆乙鹤丸与贵人相往来,都暗示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男色之风,侵染到佛门,僧徒亦不能免俗。[9]而第一一五段则讲述了一起僧人间的命案,一群僧人聚集在宿河原念佛,有僧自外而来寻访名为色押者,指其杀害了自己的师父,故来寻仇。二僧就在河边对刺,最终双双殒命。兼好感叹许多僧人虽舍俗出家但执念依然深重,故争斗时常发生,但其重义轻死刚毅果敢也值得称赞。[10]另外,僧人也与俗人一样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受害者,第四六段就提到,柳原的某位僧人曾多次遭遇强盗,以至于得了“强盗法印”的别号。[11]
不过,吉田也记录了僧侣虔诚修行的事迹。如第四九段转述了《禅林十因》中所记一位高僧两耳不闻窗外事,分秒必争一心念佛最终往生净土的事迹。[12]第一二四段还介绍了净土宗高僧是法朝夕精进的事迹。[13]此外,第二二八段提到如轮上人于文永年间(1264—1274)在千本(在京都地区,有大报恩寺)开创的的释迦念佛活动,反映了当时佛教净土修行的流行情况。[14]
二.僧人的多样化形象
通过对僧人生活片段的记录,僧侣这一群体在吉田兼好笔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往往只是寥寥数笔,就活画出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
第一〇段提到,西行法师看到后德后德大寺大臣在寝殿中拉了绳索,不让野鸢飞到庭院中来,认为不妥,“就算野鸢飞进来,又有什么关系?这位大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心胸呢?”从此以后不再造访。[15]虽然可能是对用意的误会,但也刻画出西行法师对动物的怜悯之情,及其对权贵者任意妄为的不以为然和自身的清高自持。而其筆下的良觉僧正则与前者颇为相反。因此僧房门前有棵榎树,众人遂呼之为“榎树僧正”,其嫌称谓不雅就砍掉了树,众人便呼之为“残株之僧正”,其更为恼怒,又将树根拔起,于是落得“掘坑之僧正”的名声。由此生动地变现出其人的性情之暴躁。[16]
与之相类的还有遍照寺的承仕法师,该法师常去池边喂鸟,后来却将食物撒在法堂内,等池鸟飞进屋内后,法师竟然关上门大肆扑杀,群鸟凄鸣扑腾之声大作。幸而为人发觉,将之押入了监牢。[17]由此可见,此僧是蓄谋已久意欲谋害池鸟,先前的投食实为圈套,其恶毒不免令人发指。
而第四七段所记的老尼则表现为慈心但痴愚的形象。有人与一老尼同往清水寺,尼一路喃喃自语“嚏哉”,同行者不解,屡问而不答,后来老尼才生气的告知原因,是其养君在外,担忧其打喷嚏,才不听念诵“嚏哉”,以期为之消灾。[18]老尼出家而不忘其养子,可见其慈母心性,与世俗为母者无异。而其深信“打喷嚏时如果不反复念诵这个(嚏哉),就可能死去”,则稍显痴愚可笑,但也进一步深化了其慈爱的形象。
第一〇六段提到名证空的高野山僧人,因为在路上被马挤入沟中,故怒斥对方的马夫,告知对方比丘的身份极为尊贵,对方冒犯实为大过。马夫不明所以,该僧不禁口出恶言怒骂其缺乏教养,“骂完即省悟出言太不逊,牵了马转身就向来处逃去。”[19]起初的指责,活画出证空上人的矜骄和盛气凌人,而后的唾骂更显示了其人内在的粗鄙一面,但随即省悟的奔逃,又显示出其具有高度的自我反思与自我修正的能力——以其能够反省自新,故吉田也略带戏谑的称此为“庄重的争吵”,显示出一位僧人修行尚有待进步圆满的形象。
在第二二段则记有东二条院和日本净土大德法然上人的弟子乘愿房的对谈。作为净土宗的代表人物,当东二条院问哪种方式为亡者祈福最好时,乘愿房回答:“光明真言。宝箧印陀罗尼。”众弟子问他为何不答以“念佛”。乘愿房回答说从宗派的立场确实应当如此,但对于所问之事存有经典依据的是真言和陀罗尼。[20]寥寥数笔,刻画出一位不拘泥于宗派立场和利益,而严谨、庄重、开放的高僧形象。
类似的高僧形象,在书中还有不少,如一位名叫心戒的僧人,认识到世事无常犹如火宅,无可安初,故“平常静坐之时,双膝从不落地,只是蹲着。”[21]再如由武士而出家,看似言辞粗鄙,实则能够弥平他人心中纷争之念,心中充满祥和之气的尧莲上人。[22]以及见多识广的弘舜僧正等。[23]
通过以上各种类型人物的刻画,吉田兼好为后人提供了当时佛教僧人的众生相,使今人能够直观、生动的认识到当时作为生活世界而存在的佛僧群体其中的千姿百态,高尚与低俗并存,超脱与市井同在。
三.吉田兼好的佛教信念
除了反映出当时佛教的现实形态之外,这些相关记述同时也曲折地传达了吉田兼好自身的佛教信念及其对佛教的理解。吉田在其年幼时就对“佛”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对之有所追问,[24]这似乎预示了其后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虽然最终出家为僧,但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其对佛教有真诚的信仰,但又绝非如迷信之徒那样一味宣扬或维护信仰。
吉田认为,死亡是随时会来临的,人却很容易忘记这一点,陷入对现实的贪欲和无穷期望,这些其实都是内心迷乱导致的妄念,很多人一生追逐,最终只是浪费了生命,因而应该放下贪求,一心向佛。[25]潜心于佛道的修行才是最有兴味的大事,世间的一切都不能与之相比,[26]而“心中不忘来世,日日不离佛道,是我最赞赏的态度。”[27]他似乎颇为向往山中隐修的生活,认为在山中虔诚修行佛法,能够祛除内心烦恼,洗涤心灵,[28]“就算无法彻悟佛理,只要能了断俗缘,让此身清静;澄清俗务,让此心安宁,也还可以暂得此生之乐。”[29]这些说法都反映了他对佛教的虔诚态度。
但与此同时,吉田兼好对一些流于形式的佛教内容也存有不以为然之意。如第一段说到:“法师一辈子高座说法,俯临众生,似有无上的权威,但对他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增贺上人似乎说过,一心求名,是有违佛陀教义的。”[30]在佛教传统中,讲经说法是度化世人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修行内容,但吉田认为这不免落入对名声的追求,有违佛教的本意。而针对世人从外在评判佛教内容的做法,其也有所揶揄。如第一五二段提到,西园寺内大臣见到静然上人,因其身躯佝偻、须发浩然,就称赞其相貌令人尊重,于是遭到他人以年老脱毛的狮子狗为比附的嘲弄。[31]这里作者显然并没有对老僧的不敬之意,但对此做出记录就已经隐晦地表明了作者对此种玩笑的认可,言外则不免有提醒读者超出外面以看问题的意味。同时也说明作者对佛教并不是一味的维护和鼓吹,而是以平常心对待之。
另外,佛僧群体在吉田兼好笔下还承担了另一个任务,即使作者能通过佛事来讽喻人事,抒发人生感悟等。如第四一段提到一位蹲踞在楝树树杈中的法师,手扶着树枝打瞌睡,十分危险,众人认为僧人愚蠢,吉田就借机发表了自己的感叹, “我等又怎知死期不近在眼前呢?还不是整天在这儿观看赛马,比那法师,岂不更蠢?”[32]第四二段讲述了出身名门的行雅僧都,因病导致面部肿大犹如恶鬼,为避免给人带来恐慌,就避居室内不外出,直至命终。[33]另有高仓院法华堂的三昧僧,因为觉得自己面容丑陋,就闭门不出。[34]这都表现了故事主人翁懂得自知,不给他人增添麻烦的告尚品德,并借机批评了世人好于揣摩别人心机,而缺乏自知之明的风气。此外如第五二段提到仁和寺老僧參拜石清水未果,则是为了表明即使是小事也需要有人指点的观点。[35]第二三六段圣海上人看到因顽童玩耍而错位的石狮狛犬,认为大有深意而感动得落泪,则讽刺了牵强附会故作深沉的做派。[36]
本文略具数例,可见吉田兼好笔下的僧徒故事,丰富的展现了当时社会的言情风貌,因而不仅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凭借此,也可以窥探到当时日本社会文化的许多历史细节,特别是佛教与社会互动的场景,应值得重视。
注 释
[1]《徒然草》的研究情况可参见杜冰:《中国的<徒然草>研究现状》,《名作欣赏》2010年03期,第110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日]吉田兼好著,文东译,《徒然草》,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
[28][29][30][31][32][33][34][35][36]参见谢立群:《从<徒然草>看兼好的隐遁观》,《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6期。
(作者介绍:段霞,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化、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