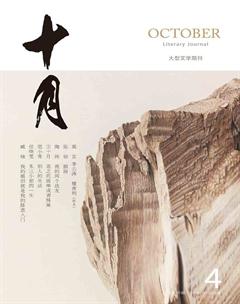偏移与乡愁:安德洛玛克的故事
吴雅凌
1
安德洛玛克我想起你
今年冬天贾非留在巴黎。
我们相约去看一场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的很长的老电影。1969年的黑白片《狂爱》(Lamour fou)。四个小时以后,重新走出巴黎大堂广场地下的电影馆,夜幕降临。天色是一种冬日才有的深不可测的深蓝。新建的大堂广场顶着巨型玻璃天幕,金属支架涂成暧昧的乳黄,远看如一片太厚的荷叶,没能如愿以偿在夜空中翻舞,反而泄了气似的沉向大地,压在路灯和往来路人的头顶。
我们穿过人群,走到无垢泉的街角才站住。那座有六层石阶的白喷泉静静淌着水。浮雕的水仙让人想起远古的年代。
贾非在这时打破沉默,淡淡地念道:
——“安德洛玛克,我想起你!……”
和多数老巴黎人一样,贾非不喜欢重建的大堂廣场,这个与老街区格格不入的新建筑。只是,有什么办法呢?巴黎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避不开这个市中心最大的地铁中转站。贾非又是电影馆的常客。来一次就小小抱怨一次,这渐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一点乐趣。我们有一回拿坐在埃菲尔铁塔餐厅里的莫泊桑揶揄他。
波德莱尔也曾惊叹奥斯曼改建中的巴黎变了。他走在罗浮宫前,想起安德洛玛克,那个国破夫亡的古代女子站在他乡的小河边长久哭泣,以此哀悼回不去的故乡的那条河。
安德洛玛克,我想起你!这小小的河
如哀矜的镜子在当年映衬
你寡妇的殇痛里的无边庄重,
这骗人的西莫伊斯河水被你哭涨,
突然浸润我变纷繁的记忆,
在我穿过那新的卡鲁索广场时。
把一条陌生的小河命名为西莫伊斯,假想它就是故乡的同名河。让自己深信不疑,自从丈夫赫克托尔战死那天起,时间已然停顿,自从特洛亚亡城以后,生活不再有继续行进的意义。由于对某个逝去的时空心怀执念,与现实生活的转变被动错开。安德洛玛克是乡愁的化身,代表“那些丧失了就永远找不回的人”,那些无力应对时代和命运的转变的人。
贾非很慢很慢地念着《天鹅》开篇的几行诗。我对他会心一笑,没有接话。我了解他身上的老巴黎人情结。我不必安慰他,也安慰不了他。贾非的乡愁和波德莱尔一样没有过多伤感泛滥。而且,他在这时提起安德洛玛克还有原因。里维特的电影用了四个多小时讲述一对夫妻排演拉辛的戏剧《安德洛玛克》的故事。随着拉辛笔下跌宕起伏的剧情展开,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也平行遭遇一连串变故。
我说:“在里维特拍《狂爱》的时候,‘大堂这片街区里真的还有大堂吧。”
法语里的halle指非露天的菜市场,有高耸的屋顶盖,通常坐落在城市中心地带。1969年,长久以来作为“巴黎的胃”的大堂中央集市停止运行,商贩们被撤离迁往郊区,但那些庞大的玻璃加钢铁结构的建筑尚在。它们在让人怀旧的老照片里显得明亮,通透,坚强而轻盈。这些地标性建筑一度见证此处的人们与别处不同的生活方式。随着城市更新计划启动,它们很快被拆毁,很快被取代为全世界千篇一律的商业购物中心。
贾非讲过,当年他们一群二十来岁的小年青曾在拆迁以前的大堂街区整夜游荡,不为什么,就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重点是不要睡着,睡着就会错过。转眼近半个世纪,这一带拆拆建建,却不知为何让他有物是人非的感觉。
“是呵……难以接受的很可能不是建筑本身,而是某种值得珍惜的生活方式的无情流逝。”他眯着灰色的眼,若有所思。附近的圣梅里教堂敲响了晚祷的钟声。在悄悄聚拢的夜色里,我努力揣摩这句话从六八年一代人口中说出的分量。
2
偏见与孤挺花
不久前我去找贾非。
下雨天,临近黄昏,旧书店里倒有三五人在那儿翻书。贾非站在里间的老木书台前整理一批七星文库全集本。我随手抽出一册,1931年的拉辛戏剧全集初版,坊间已不多见,伽利玛出版社后来又有新的修订本。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他说,如今的法国人好像不怎么读拉辛了。我说,至少如今法国人说起费德尔或者安德洛玛克,首先还能想到拉辛。
倒是少有人还会提起维吉尔,更不必说荷马和欧里庇得斯。经典在法语中的影响所幸还强大,却搁浅在古典主义,没能追溯至更古远的年代。
“就像中世纪人不识荷马而熟知特洛亚战事,他们通过一些拉丁文和法文的改写本了解古代世界。我们也一样。”贾非拿起那册书,信手翻起来,翻到一页停住,轻声读起来:“怎么!你竟会设想安德洛玛克如此不贞…… ”那是《安德洛玛克》第四幕的开场,她决定在与皮洛斯举行婚礼之后自杀。
书台上摆着一盆当季的孤挺花,没有叶子,大朵大朵的红瓣向高处肆意张大,好不寂寞。贾非读罢那一长段念白,轻轻合上书,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无以伦比的法语!”
我对拉辛的文风自是无话可说,却不知从哪里生出的不服:“卢梭说过,古希腊悲剧从来不在舞台上表演谈情说爱,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似乎不表演男女相爱的情节就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贾非想了想说:“有道理的说法,”他把那册书轻轻摆在那盆花的旁边,转头看我,脸上的表情温和而坚定:“不过,问题没这么简单。”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基里柯(Giorgio de Chirico)的小小的画。安德洛玛克和赫克托尔在画中紧紧相依,站在特洛亚城下。听说那是贾非多年前机缘巧合得到的珍品。个中经过如何,没有人知道,贾非自己是从来不说的。
那天为了招呼买书的顾客,贾非和我的讨论不了了之。他约我一起去看里维特的电影,还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堆拉辛手稿的影印资料,让我慢慢翻看。这些资料中,最让人在意的莫过于两部荷马史诗的阅读笔记。1662年,年仅二十二岁的拉辛注释完品达的《奥林匹克竞技赛歌》,开始分卷评注《奥德赛》,总共写出了第一至第十卷内容。稍后他还在一部《伊利亚特》的希腊原文书上做了大量页边注,特别是卷三涉及海伦和帕里斯的段落,以及卷六涉及赫克托尔和安德洛玛克的段落。写《安德洛玛克》时,年轻的拉辛心里满满当当地装着荷马的故事:“高妙的手法,荷马做到了融合笑与泪、沉重与温存、勇气与恐惧,以及一切打动人心的东西……”
我独自坐在昏暗的光里,旧书店总给人恍如隔世的错觉。我辨认着那些写在三百五十年前的手稿上的字迹,某种穿越时空的让人心醉神迷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不得不承认那一刻在我内心发生的震撼。我之前的一点轻慢心思仅仅出于无知。
3
荷马当时惘然
荷马之后,没有哪个诗人敢重写(遑论改写!)赫克托尔和安德洛玛克。《伊利亚特》卷六里的夫妻诀别场面打动最挑剔的听故事的人。单单一场戏就够了。短短一百三十来行诗足以传世,千百年来留在人心里根深蒂固。后世所有诗人的笔力无可能为荷马的故事增色,而只能轮番尝试去化解荷马惊起的颤动。
在整部《伊利亚特》里,安德洛玛克只出场三次。卷六之外,另有卷二十二(闻耗)和卷二十四(迎丧)。三次均围绕赫克托尔之死展开。
赫克托尔难得离开战场,急忙忙赶回家,为见妻儿一面,走遍特洛亚大街小巷。他没在家里找到安德洛玛克。她带着孩子出了城探听战事,像个疯子一样站在望楼上哭泣。他们互相找寻半天,终在斯开埃城门下相遇。她迎面向他跑去,把手放在他手里,流着泪唤他的名。他默默望着孩子笑。
这是《伊利亚特》中极罕见的温存时刻。荷马把这个时刻安插在两次热火朝天的战事之间。前一场狄奥墨得斯与格劳科斯不战而和,后一场是埃涅阿斯与赫克托尔的势均力敌的恶战。赫克托尔全身铠甲,头戴让小儿子惊怕的战盔,手上沾着杀人的鲜血还来不及洗去。他以这副骇人的战士模样去安抚妻子搂抱娇儿,对他们微笑,为他们祈祷诸神,满心满眼的怜惜。即便在这样的时刻,赫克托尔首先是城邦的保卫者,其次才是安德洛玛克的丈夫。他拒绝妻子让他留在城里的哀求:
人生下来……逃不过他注定的命运。
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务,
看管织布机和卷线杆,打仗的事男人管,
每一个生长在伊利昂的男人管,尤其是我。(伊6:489-492)
赫克托尔看重荣誉和责任胜过别的一切。因为这样,甘愿把生命托付给他的安德洛玛克注定是这场战争里最惨烈的受害人。正如拉辛早就看出的,与这对情深义重的夫妻形成对比的,正是卷三里的帕里斯和海伦。
帕里斯打输给墨涅拉奥斯,回家向海伦求欢:“我从可爱的拉克得蒙把你弄到手。”(伊3:443)倘若不考虑帕里斯华丽地释放自然爱欲,我们几乎要像赫克托尔那样以为他只是无耻下流的小丑。帕里斯没有责任感。他不对战争负责,不对特洛亚人负责,甚至也不对海伦负责。帕里斯不求荣誉,也就没有羞耻心,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被全特洛亚人“如黑色的死亡来憎恨”(伊3:454),却兴兴头头,活在当下,比赫克托尔自由太多。他受了赫克托尔的责骂,依然兴高采烈地出城迎战。荷马把他比作一头漂亮的种马兴高采烈地奔向母马常去的牧场(伊6:511)。他常做逃兵,连身上的甲胄也是借来的。然而命中注定他会杀死全希腊最出色的英雄阿喀琉斯。此等荣誉,城邦的保卫者赫克托尔却是拼死也没能得到呵——事实上,正如《云林遗事》记载有洁癖的倪瓒要受污秽之灾,最重荣誉的赫克托尔偏偏死后遭到再恶毒不过的羞辱。
在普里阿摩斯王的五十个儿子和十二个女婿(伊6:245-250)里,赫克托爾处处与众不同。他在战场上最是卓越,常常单打独斗,他的兄弟们不是遇敌伤败就是远离战场,特洛亚的其他出色英雄如埃涅阿斯或萨拉佩冬,要么是表亲要么来自盟军。赫克托尔的婚姻生活在特洛亚王室同样是特例。他带着无数聘礼前往埃埃提,郑重其事地迎娶安德洛玛克(伊22:471-472)。他忠诚顾家,进城也坚持要回家看家人,“我的妻子和我的小儿子”(伊6:366)。他为独子向宙斯和诸神最后一次祷告,心愿始终不离传世的荣誉,希望“我的孩子和我一样名声显赫,孔武用力,成为伊利昂的强大君主”(伊6:476-478),“日后有人会说,‘他比父亲强得多”(伊6:480)。相比之下,帕里斯不负责任更像是得了父亲的真传,普里阿摩斯本人也不是好战士,更像一个情种,姬妾成群(伊21:85,8:305),子嗣众多。他的五十个儿子中,“十九个正室赫卡柏所生,其余出自宫娥”(伊24:495-496)。他在处理帕里斯和海伦带来的危机时不分是非。比起荣誉德性等理性要务,特洛亚王室显得更有一种崇尚自然爱欲的传统。普里阿摩斯的父亲拉奥墨冬当年亦以不负责任著称,不但敢对神们食言,哄阿波罗和波塞冬白干活,还因骗了赫拉克勒斯而导致特洛亚第一次亡城之灾。
安德洛玛克(Аνδρομχη)这个名字由νδρ(男人)和μχη(战斗)组成,大致意思是“像男人一般作战”,或者“和男人一起作战”。人如其名。安德洛玛克是特洛亚最优秀的战士的妻,她像赫克托尔一样战斗,和赫克托尔一起战斗。她与他保持一致,夫唱妇随,彼此般配。她没有参与赫卡柏带着特洛亚妇女向雅典娜的祈求(伊6:237起)。她甚至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赫克托尔的死讯,因为“没有哪个忠实的信使前来禀告她丈夫留在城外的事情”(伊22:438-439)。从某种角度看来,这对受人尊敬的模范夫妻在特洛亚没有能出其右者,也因而显得相当孤立。
赫克托尔,你成了我的尊贵的母亲、
父亲、亲兄弟,又是我的强大的丈夫。(伊6:429-430)
这是身为人妻的安德洛玛克的最动人又最无效的表白。阿喀琉斯在同一天里杀了她的父亲和七个弟兄。阿喀琉斯还将杀死她的丈夫,她仅存的亲人,并当众羞辱他的尸体。安德洛玛克哀求赫克托尔不要赴死。他是她的全部依靠,失去他等于失去整个世界。“你得可怜可怜我”(伊6:431)。然而,相爱的人在共同展望生活时发生意见争执,一味掏心掏肺的表白总是顶无用的。赫克托尔心不在此:“这一切我也很关心”(伊6:441),但他更关心“为父亲和我自己赢得莫大的荣誉”(伊6:446)。赫克托尔欲求声名不死,安德洛玛克的女性本能的自然爱欲若无所克制,反像是一种负担。卷十四中,赫拉与宙斯这对意见不合的神王夫妻做出有趣的示范,与赫克托尔和安德洛玛克形成鲜明对比。先是赫拉用美色诱惑宙斯,有效地让希腊人击退特洛亚人。宙斯醒来后以威权震慑赫拉,有效地阻止她继续搞阴谋破坏自己的计划。神王夫妻之间发誓赌咒,自我标榜“心心相印”(伊14:50),把动人的话说尽了。但这么些“掏心掏肺的表白”显然是各取所需的政治计谋。
安德洛玛克对赫克托尔不具备这样的政治素质,这因而成就了希腊文学里的一段极动人的爱情故事。临别时分,她频频回头顾盼,泪流不止。她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相见。她回到家和女仆们“一起哀悼还活着的赫克托尔”(伊6:500)。等她下一次撕扯着头发冲出城门迎接他,他已躺在骡车上断了气。她只能双手抱住他的头,在特洛亚婦人中领唱挽歌(伊24:710-724)。这对夫妻在特洛亚城门下两次相见,一次生离,一次死别。她和海伦不一样。海伦不执着独一无二的爱的对象,也就不为欠缺所伤。一场战争因她之名而起,谁赢谁输海伦都是受益者。而她,安德洛玛克,她是在所有战争中最受伤害的那群人的代表。海伦一边甜蜜地怀念前夫墨涅拉奥斯(伊3:139),一边与新夫帕里斯享受“为甜蜜的欲望所占据”(伊3:445)的欢乐。而她,安德洛玛克,她独守空房,一边哭悼随时可能传来死讯的丈夫,一边架起三角大鼎生起火,为他烧好洗澡水(伊22:442)。
只有一次,荷马用“疯狂的酒神伴侣”(μαινδι,伊22:460)来形容端庄的安德洛玛克。她赶到城墙上,看见快马拖曳着赫克托尔的尸体在战地上撒欢,扬起一片片尘烟,死人的脑袋沾满厚厚的灰土(伊22:395-405)。就像是最后一次夫唱妇随,倾力与丈夫般配,成就一对模范夫妻的形象。她当场昏倒,如死过一回,美丽的头饰散落一地,头冠、发带,还有那条赫克托尔送作定情物的阿福洛狄特的头巾(伊22:467-470)。
即便在哀悼赫克托尔的两次挽歌中,安德洛玛克也几乎不提自己,只提她的丈夫和儿子。她大声哭诉赫克托尔的死之悲惨和阿斯提阿那克斯的生之艰难。至于她自己的不幸命运,早已被赫克托尔的预言所规定:安德洛玛克将被希腊人带走,在异乡过奴隶的生活,并且终其一生没有停止对赫克托尔的哀悼。
有人看你伤心落泪,他就会说:
“这就是赫克托尔的妻子,驯马的特洛亚人中
他最英勇善战,伊利昂被围的时候。”
人家会这样说,你没有了那样的丈夫,
使你免遭奴役,你还有新的痛苦。
(伊6:459-463)
赫克托尔声称,比起全体特洛亚人,比起父母弟兄,他“更关心安德洛玛克的苦难”(伊6:453)。他情愿早早被人杀死也不忍心听到安德洛玛克被俘求救的喊声(伊6:464-465)。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在忧患安德洛玛克的不幸未来时,赫克托尔也把关注点放在世人对他的哀悼上。正如他身边的亲人们那样,赫克托尔生前就已开始哀悼他本人的英雄之死。赫克托尔看重声名不死胜过一切,乃至他死后,安德洛玛克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在成全亡夫的心愿。
——“等等,等等。”贾非打断我。
我们朝着塞纳河的方向走,穿过好些迄今保留中世纪商贩名的小街,卖酒的隆巴尔街,卖针的埃吉尔街,卖鞋的古尔塔隆街。旧时商人今安在。如今这一带汇聚着好些有名的爵士乐酒吧。我们从那家名叫“咸吻”的店经过时,贾非不紧不慢地对我说:“你看,你现在是在用欧里庇得斯的方式理解荷马。”
4
就起了乡愁
欧里庇得斯的传世诗剧中有两部写到安德洛玛克。
《特洛亚妇人》从老王后赫卡柏的眼光出发,讲述特洛亚妇人们在亡城以后的悲惨遭遇。第二场专写安德洛玛克。她被发配给阿喀琉斯之子皮洛斯做妻妾,“到那杀害我丈夫的凶手家里去做奴隶”(安660)。她乘车进场,带着小儿子,车上堆满赫克托尔家的财富。表面看去,安德洛玛克好似带着一车亡夫的家产去改嫁。归根到底,赫克托尔的妻子是一件物,一件战利品,和赫克托尔的铜甲同一性质,“叫阿喀琉斯的儿子从特洛亚运回家去装点佛提亚的庙堂”(特573-574)。单从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之争就不难看出,战胜一方的将领分配荣誉礼物,再没有什么财物比从失陷的城池宫殿里被赶出的王家女俘更有分量。
我和这孩子变成战利品。叫人运走,我们由高贵的身份降落到奴隶的地位,这变迁真不小啊!(特614-615)
享过福又落难,思念过去的幸福更使我伤心。(特639-640)
老王后奉劝儿媳忍辱负重,嫁与皮洛斯,把赫克托尔的孩子养大,他日恢复特洛亚王权。她切切地多叮嘱一句:“不要再理会赫克托尔的命运,你的眼泪再也救不了他。”(特697-698)一味掏心掏肺的表白从前救不了赫克托尔,哀悼和眼泪如今也不能拯救特洛亚王族,老王后的提议与赫拉对付宙斯的政治手段相仿:“奉承新主子,用你的丰姿诱惑他。”(特700)政治手段足以拯救特洛亚王族吗?无论如何,安德洛玛克沉浸在丧夫的殇痛里,无力担负此等使命:“亲爱的赫克托尔,论门第,论才智,你是我最得意的丈夫,你家资富有,为人又英勇。当你从我父亲家里把我迎接过来,配成亲眷时,我正是一个白璧无瑕的女儿。”(特673-676)
这时传来更坏的消息。希腊人决定把赫克托尔的独子从塔楼摔死,以免那孩子将来长大复仇。反抗没有用:“你最好默默忍受这命运,不至于使他的尸首不得掩埋。”(特735-736)安德洛玛克大哭一场,“才丧失了孩儿,又要去举行那美丽的婚礼。”(特779)她的不幸打动了阿伽门农的传令官:“那女人竟惹出了我许多眼泪,她离开海岸时大声哭唤她的祖国,还向赫克托尔的坟墓道一声永别!”(特1130-1132)甚至来不及亲手埋葬早夭的孩子,安德洛玛克就这样匆匆永别了故乡。
5
欧里庇得斯讲古
夏特莱广场正对塞纳河。对岸即是古监狱。广场两边的剧院始建于奥斯曼时期,东边的市立剧院,西边的夏特莱剧院,都依次临到了闭门修复的时候。每次经过,我总会想到里维特的另一部黑白电影《巴黎属于我们》(Paris nous appartient)。男主人公站在市立剧院的屋顶上,转头俯瞰广场和河上的桥。巴黎就在脚下。那真是意味深长的一幕。在那一刻,男主人公(以及电影里的所有年轻人)还存有“巴黎属于我们”的一点念想,他执导的戏即将在首都的戏剧殿堂上演。他不知道他后来失望了,放弃了,他也不知道他本人还自杀了。又或者,他是知道的,他只是不知道自己知道,这让他眼底总带有一抹忧郁。
我们站在广场上,继续一路走来的话题。我说:“至少在《特洛亚妇人》里,欧里庇得斯写安德洛玛克没有跳脱荷马诗中的设定。”我举《伊利亚特》最后一卷结尾处为例。安德洛玛克的挽歌里准确说及她和小儿子的悲惨下场——
这些人很快就会坐着空心船航海,
我也是其中一个。孩儿啊,你跟着我同去
做下賤的工作,在严厉的主子面前操劳,
或是有阿开亚人抓住你的胳膊
把你从望楼上扔下去,叫你死得很惨。
(伊24:731-735)
贾非说:“是的。不过我们常常难免忽略一个事实。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特洛亚英雄诗系无不写过这些故事,只不过仅有荷马的诗传到今天。《库普利亚》(Κπρια)交代战争的缘起和前九年战事,很可能写到安德洛玛克在战乱中失去父母兄弟以及嫁给赫克托尔的经过。我们从后人援引的一段残篇知道,《小伊利亚特》( Тλιμικρ)中肯定写到皮洛斯带走安德洛玛克并杀死赫克托尔的儿子。因此更准确说来,欧里庇得斯没有跳脱古代英雄诗系传统的故事设定。”
我抬头,圣雅各伯白塔高高耸立在夜空。我明白贾非不是在计较某个更准确的说法,他有意强调的细微分别与刚才打断我的话有关。我试着纠正自己:“虽然如此,在《特洛亚妇人》里,安德洛玛克有典型的欧里庇得斯式的心理斗争,这在荷马诗里不可能有。”
我自己沽名钓誉,虽攀得很高,可是啊,我何曾达到那圆满的幸福?凡是一个妇人所应得的贤淑德行,我在赫克托尔家里全然无缺。(特643-646)
在欧里庇得斯笔下,安德洛玛克声称虽有妇德的美名,却未享受实在的幸福。她谨守妇道,顺从丈夫,终日“照料家务,纺线织布”(伊6:491),“抑制欲望,长久待在家里,不让女人家的花言巧语进我的门”(特650-651)。安德洛玛克对赫克托尔言听计从,“用缄默的口舌和安详的眼光来对待丈夫”(特654)。如此赢得的美名却招来最坏不过的耻辱和灾难。皮洛斯听闻她的美德,选中她,要拿她去做妻子。皮洛斯原该是安德洛玛克最有理由惧恨的敌人呵!且不说他的父亲阿喀琉斯杀了安德洛玛克的至亲(父母、兄弟和丈夫),皮洛斯本人还在神坛上杀死普里阿摩斯王,又亲手把阿斯提阿那克斯摔下望楼。“我这点好名声传到希腊军中竟把我害了。”(特657-658)在欧里庇得斯笔下,安德洛玛克通过苦涩的告白对从前在特洛亚过的那种模范夫妻生活方式发出自省。从某种程度上赫克托尔追求荣誉的英雄理想似乎也一并受到质疑。显然,这在荷马诗中不可能有。
贾非说:“荷马诗中没有人物的心理斗争,也绝无可能像欧里庇得斯那样让安德洛玛克公开恨海伦:‘你真该死,你那太漂亮的眼睛,竟自就这样可恶地毁灭了特洛亚闻名的郊原(特771-772)。这就像圣经的好些叙事,让我们以为是脱离某个特定年代的,也因此而适用于所有年代。隐约,若有若无,向一切可能开放。简约到极致,简约到让人非要用‘现代来形容。”
我尝试推进我们刚刚达成的共识:“欧里庇得斯对荷马做出的理解,正是让公元前415年的雅典人可能引发共鸣的东西。”
贾非赞同地说:“欧里庇得斯表现从前的故事,心里想着现实的问题。所有传世作者莫不如此。就在《特洛亚妇人》头演前一年冬天,雅典人就像当初希腊人摧毁特洛亚城那样无情摧毁了一个名叫墨洛斯的小国,他们屠杀了当地的所有成年男子,将妇孺沦为俘虏。雅典人坐在剧场里听着特洛亚妇人的哭声,很难不去想新近发生的那场战争。我想,基于某些相类似的原因,萨特在二战期间搬演《特洛亚妇人》也大受欢迎。”
诗人借安德洛玛克之口发出谴责:“你们希腊人啊,你们曾发现残忍的行为不合希腊精神,为什么又要杀死我这无辜的孩儿呢?”(特764-765)在开场中,海神波塞冬也发出警告:“你们这凡间的人真愚蠢,你们毁了别人的都城,神的庙宇和死者安眠的坟墓:你们种下了荒凉,日后收获的也就是毁灭啊!”(特96-98)不难想象如此意味深长的话在彼时雅典人心头激起的震撼。同样,在《安德洛玛克》里,针对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严厉批评也真实反映了雅典人反感斯巴达人的心情:“你们在一切人眼里的最可憎的人,斯巴达的居民们……你们不正当地在希腊占着势力。”(安445-450)
我们穿过夏特莱广场,从兑换桥过河,在西提岛向右拐,沿着斜斜的钟表河岸,一直走到太子广场。这个呈长长的三角形的广场嵌在西提岛最西边的尖角上,下雨也好,晴天也好,总带着那么一股超乎现实的安静气息,就像一幅马格利特的画,与岛上另一头的圣母院判若两个世界。
我们在树下小坐。夜归的鸟飞回花园里的树上。我揣摩贾非的话,犹疑地问:“你是想说,既有欧里庇得斯理解荷马的方式,也就有后世其他作者理解荷马的方式……比如拉辛?”
一只鸟从我们右边飞过。与此同时,贾非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神情:“别急!让我们先看看欧里庇得斯接着讲安德洛玛克的故事。”
6
多少旧愁新恨
《安德洛玛克》换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安德洛玛克已经远在他乡,在佛提亚地方做了皮洛斯的妾,生下一子。斯巴达公主赫耳弥俄涅是明媒正娶的妻,不能生育,趁着丈夫外出,意欲加害那母子二人。安德洛玛克两度落难,都可说是海伦的干系:第一次是因海伦而起的战争,第二次则因海伦的女儿。她无处求助,只得藏起孩子,一个人躲在忒提斯女神庙避难。
第一场戏即是发生在两个女人之间的争辩。对峙的双方远非势均力敌。一个是合法婚姻里的主母,一个是战争中分配到的女奴。一个是从特洛亚生还的显赫英雄墨涅拉奥斯和海伦的独生女儿,一个是希腊人惧恨交加的仇敌赫克托尔从前的妻。赫耳弥俄涅不能忍受丈夫把床席分给别的女人,何况这女人是“一个女奴和用枪尖获得的女人”(安155),一个蛮夷种族(安173):“因了你的法术我为男人所不喜欢,因了你使我的肚子不生育。”(安157-158)赫耳弥俄涅骄纵跋扈,一张口就教训安德洛玛克,百般轻辱,这不仅因为她身份尊贵,年轻貌美,还因为她有显赫的斯巴达娘家做后盾,她甚至连佛提亚夫家也不太放在眼里。安德洛玛克据理力争,反驳她令丈夫讨厌怪不得别人,全因本人欠缺德性(安208),不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克制自然爱欲的冲动,不肯隐藏“无厌的枕席的欲望”(安218)。
安:你不肯沉默地受着恋爱的苦痛么?
赫:什么!不是每个女人把这放在最先头的么?
安:是的,若是和女伴们要好,否则就没有光彩。
赫:我们不用蛮夷的法律治理这城市。(安240-243)
本是两个女人争宠的爱情戏码,在欧里庇得斯笔下很自然地升级为政治事件。墨涅拉奥斯出场,以孩子作为要挟,迫使安德洛玛克主动走出神庙。他执意杀安德洛玛克,不仅是为女儿撑腰,更因为“这是一件很大的糊涂事:去留下敌人里出来的敌人”(安519-520),唯恐“蛮夷种族的人将来做了希腊人的王”(安665-666)。皮洛斯的祖父佩琉斯赶到,救下安德洛玛克母子,并赶走墨涅拉奥斯。赫耳弥俄涅恐怕丈夫回来怪罪,跟随表亲俄瑞斯特斯逃回斯巴达,殊不知俄瑞斯特斯在德尔斐埋伏杀死了皮洛斯。老人佩琉斯一连失去儿子和孙儿,仅剩一个私生的重孙摩罗索斯(Μολοσσ)。他的海神妻子忒提斯在终场时现身,预言家族的未来——
他乃是埃阿科斯家系唯一遗留的人了。从他生出来降有许多国王,一代代幸福地统治摩罗西亚,因为,你的和我的各族不该断绝,而且特洛亚的也是如此。因神们还是顾念着它,虽然因了帕里斯的愿望它已经陷落了。(安1246-1252)
依据女神预言,安德洛玛克要再嫁给特洛亚人赫勒诺斯。他们要带着两族共同的独子,世世代代统治某个希腊城市摩罗西亚(Μολοσσα),字面意思是“摩罗索斯的国”。安德洛玛克大难不死又一次活了下来,尽管她羡慕那个被希腊人杀了献在阿喀琉斯坟前的特洛亚公主(特630-631),情愿当初不必活着走出山河破碎的故国,但命中注定她是本族最后幸存的人。男人们在特洛亚战争中遗留下的问题,要在安德洛玛克这个女人身上得到解决。
7
记忆停顿时
我们过了新桥到了左岸,沿着太子街,笔直进入拉丁区的心脏。
在碧西街角,有人坐在那家名字就叫“碧西”的老咖啡馆前,低头唱一首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在1970年代写的老歌《溺水的女人》(La Noy e)。
你改道走了,在记忆的河上。
我跑在岸边喊你回来。
可你渐渐远去。我一路狂奔,
一点点追赶丢失的地盘。
你不时陷进不安的水波,
偶尔被绊住,犹豫,你在等我。
你把脸藏在撩起的裙间。
生怕被人看穿羞涩,还是遗憾。
你一个飘零水上的可怜人,
我做了你的奴隶,跳入河,
在记忆停顿时,一切都碎了,
遗忘的海洋让我们重逢。
一个人在岸上追赶心爱的人。她浮在水上,依着河水而去,身上裹着那条最美的裙子。那人眼看就要追丢了,因为河流总有偏移和改道,还因为河水要流进大海,而河岸总有尽头。如何可能挽回一个正在失去的爱人或者,更重要的,如何可能挽救一段正在忘却的记忆?乃至于一个过去的时代,一种过时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人群中停住脚步,侧耳倾听。歌者是个小个子男人。他倚墙而坐,一身黑衣,络腮胡子,眼皮有些浮肿,挺丑的脸上流露出伤感,竟有一丝让人动容的温柔。这一带曾经有林立的小酒窖和咖啡馆,号称左岸精神的发源地。如今露天集市还在,蔬果铺加书店画廊,从来是时髦快乐的地方,到了夜晚愈发地热闹起来。
一曲唱罢,人声依旧喧哗。人群里总是最有情也最无情。
贾非说:“甘斯布是真正的诗人。他用情歌的方式探究最为严肃的问题。”
我应声说:“是呢,好一首安德洛玛克的歌。”
我突然地想起在蓬皮杜中心看见一幅马格利特的小画。一片海,沙滩上支着一个画架。画布上的风景与现实中的风景连成一片,只有画框在提醒我们那里有一幅画(并且,从技艺而言,那是模仿真实的完美无缺的作品)。画架的左边有一块石头,右边升着一堆火。火光映照在画上,犹如柏拉图洞穴神话。那真是有关属人的认知的再贴切不过的譬喻。那个画框明明白白地标注着属人的限度。我们几乎不可能做到无可指摘。而即便做到了,也只是截取到真实的一个片段。属人的认知并且永带着引为自诩的火光。那火光的影子如同风景上的一点污迹,让我们再也看不见画框以外的乌云所孕育的风暴,看不见真实的天空和海洋本没有边际。站在那幅马格利特取名为“美丽的女俘”(La belle captive)的小画前,我一度受彻底的震撼,想要大喊大哭出来。现在突然在人群里听到一首歌,溺水的女人,犹如美丽的女俘的孪生姐妹,那么温柔那么酸楚地说起人的认知(或记忆)限度,让我有难以言喻的心情。
我们一直走到圣日耳曼大街的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贾非说:“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意思很好。荷马通过赫克托尔的预言界定了安德洛玛克的一生,也以此界定了后世诗人的想象。安德洛玛克的故事里只有一个男主人公就是赫克托尔。她多次改嫁,从来把赫克托尔当成唯一的丈夫。另一方面,荷马诗中有关这对夫妻的故事接近完美,后来诗人几乎无人敢重写赫克托尔在世时的安德洛玛克,也无人敢不写安德洛玛克对赫克托尔在世时的记忆。欧里庇得斯如此,维吉尔如此,拉辛同样如此。这构成一个悖论。书写安德洛玛克无疑是历代诗人的一大挑战。”
8
何必机器降神
在歐里庇得斯笔下,安德洛玛克开场时就坐在祭坛的台阶上哭悼赫克托尔,并且直到退场,安德洛玛克都在绝望无助中反复不停地哭悼赫克托尔。
【开场】亚细亚地方的精华,忒拜的城市呵!我以前曾从那里带了许多金饰华贵的妆奁到普里阿摩斯的王家,给赫克托尔做生儿育女的妻子。在从前时候是被人钦羡的安德洛玛克,但是现在乃是最不幸的女人,在一切曾经或将来存在的女人中间(安1-6)。
【退场】啊,我的丈夫呵,丈夫呵,我多么希望得你的手和枪做我的帮助呀,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呵!(安523-525)
虽系标题女主人公,安德洛玛克在第三场戏开头早早地退了场,把舞台让给别的人物和别的故事。这是因为,哭悼赫克托尔是一个没有发展前途的故事。安德洛玛克自比为死去之人,永远停滞在某个死去的时代:“正当佛律癸亚人的不幸的城市和我那有名的丈夫被毁灭时,我已经毁灭了”(安454-456)。一个死去之人如何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欧里庇得斯要继续写安德洛玛克,就要让她的生活继续下去,让她面临新的生存危机,有新的恐惧,新的威胁。
拯救摩罗索斯即是让安德洛玛克活下去的动力,哪怕那是不情不愿的第二次婚姻生下的孩子。即便在前两场戏里,推进情节冲突的也不是失去赫克托尔的往事,而是安德洛玛克作为母亲即将失去孩子的灾难。她心甘情愿为他赴死(安414):“以前我也受着种种忧患,总有一个希望引着我,只要我的小孩健在,我可以找到什么对于忧患的解救和援助。”(安26-28)她暗中去找帮手,也就是皮洛斯的祖父,本地真正掌握王权的佩琉斯。她说服使女想办法报信:“你可以找到许多方法,因为你是女人。”(安85)她在赫耳弥俄涅面前假意“信托”(安269,270)那个注定信托不得的皮洛斯——他未曾从祖父手里正式接过王杖,他从一开场就不在家,并且永远也回不了家。
特洛亚之后,整个希腊世界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这直接表现在三大英雄世家欠缺继承人的共同隐患。阿喀琉斯之子皮洛斯除女奴所生的私生子以外没有子嗣。墨涅拉奥斯只有独女赫耳墨俄涅。而阿伽门农的独子俄瑞斯特斯被迫与赫耳弥俄涅解除婚约,也就失去唯一可能的联姻对象,因为他犯了弑母的罪,神谕指示他只能从亲戚中间娶妻(安974-975)。欧里庇得斯的前三场戏似乎有意模拟古典时期雅典人的法庭辩论。第一场,原告赫耳弥俄涅不敌被告安德洛玛克的自我申辩。第二场,墨涅拉奥斯代女出场迫使安德洛玛克屈服。而在安德洛玛克退场的第三场,匆匆赶到的佩琉斯与墨涅拉奥斯针锋相对,分别代表应对危机的两种不同姿态。从妇人之争到王者之争,欧里庇得斯一步步地阐明整部悲剧的内在问题。
斯巴达王坚决反对让“蛮族”进入希腊文明。βραρο一词反复出现在斯巴达人口中,用来贬低安德洛玛克,墨涅拉奥斯如此(安650,665),赫耳弥俄涅如此(安173,243),赫耳弥俄涅的乳母亦如此(安870)。赫耳弥俄涅对安德洛玛克的辱骂很有代表性:“你竟自这样荒唐,敢去和杀了你丈夫的人的儿子去同床,给那凶手生下儿女来。蛮夷种族都是如此的……这些事都是没有法律制止。不要把这带进我们这里来,因为这在我们算是不对的”(安169-177)。雅典法庭采取民主方式,原告被告在辩论中各正申诉,陪审的市民在公平听讼之后投票表决。但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三场辩论更像是徒有其表。安德洛玛克在第二场束手就范,乃是迫于墨涅拉奥斯的威吓,“没有法律的裁判”(安567)。佩琉斯虽在第三场让墨涅拉奥斯败下阵来,不料还有第四场戏,俄瑞斯特斯杀死皮洛斯,带走赫耳弥俄涅。民主法庭的公正裁决终究没能解决整部悲剧提出的内在问题。
究竟是在持守传统中走向自我消亡,还是以异己力量补充垂老的生命?正当佩琉斯为孙儿的死讯痛心疾首:“再没有我的种族了,再没有子孙留在家里了……再没有我的城邦了,这王杖我抛在地上!”(安1177,1222-1223),忒提斯女神从天而降,解决人间的问题。这是欧里庇得斯的惯常做法,肃穆的转为诙谐的,戏谑里带着无奈:“神们做出的许多事出于人的意外。我们以为应有的并不曾实现,所不曾期待的事神给找着了出路。”(安1284-1286)
9
埃涅阿斯问路
欧里庇得斯遇到的困难,维吉尔同样遇到了。
《埃涅阿斯纪》卷三讲述了两群流亡的特洛亚人在异乡重逢的经过。埃涅阿斯在旅途中经过赫勒诺斯统治的希腊城市。他上岸后,先看见安德洛玛克——
她在一条也叫西莫伊斯的河边向亡夫赫克托尔供献祭品和牺牲,在他的衣冠冢旁召唤他的亡魂,这空墓上铺着绿草,墓前还设了一对祭坛,以表达她的悼念。(埃,3:301-305)
维吉尔笔下的安德洛玛克同样从头哀哭到尾。她虽嫁给了赫勒诺斯,依然在哀悼赫克托尔。她看见埃涅阿斯远远走来,一身特洛亚人的甲胄,以为看见了特洛亚故人的亡魂,昏死过去,并在醒来时急忙打听起赫克托尔。“她泪流满面,整个地方充满她的哭声。”(埃,3:313-314)“她不住地流泪,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但又有什么用处呢?”(埃,3:344)
有别于欧里庇得斯,维吉尔笔下的安德洛玛克不仅哀悼赫克托尔,也哀悼他们共同生养的儿子。尽管她顺带提到“受皮洛斯轻侮,在奴役中给他生儿子”(埃,3:327),但她一心只挂念当初从望楼摔死的阿斯提阿那克斯。临别时,她送礼给埃涅阿斯的儿子:“你是这样像我的孩子阿斯提阿那克斯,现在只有你能使我想起他的容貌。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脸,和你一模一样,他现在要活着也跟你一样岁数,快成人了。”(埃,3:488-491)
维吉尔绝口不提安德洛玛克为第二个丈夫所生的孩子,而着重说起一个新人物,也就是安德洛玛克的第三个丈夫,特洛亚人赫勒诺斯。他是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尔的亲弟,阿波罗的祭司,和孪生姐妹卡珊德拉一样通神谕。在短短的诗文里,维吉尔两次提到赫勒诺斯在希腊重建特洛亚城,一次借安德洛玛克之口,另一次则是埃涅阿斯亲眼所见:
【安德洛玛克】赫勒诺斯为了纪念特洛亚人卡翁(Chaone),把这片田野称为卡翁之野,把他的全部领土称为卡俄尼斯,又在这山脊上仿特洛亚王宫而造了这座宫殿。(埃3:334-336)
【埃涅阿斯】我一面走着,一面认出这竟然是小小的特洛亚城,有一座仿雄伟的特洛亚王宫而造的宫殿,有一条干涸的小河也叫克珊托斯(Xanthi)。我在斯开埃城门下亲吻门柱。(埃3:349-351)
在古代英雄詩系传统里,赫勒诺斯可谓特洛亚人的叛徒。依据普罗克洛斯援引《小伊利亚特》的残篇,奥德修斯一度抓住他,让他和盘托出特洛亚终将失陷的神谕。他向希腊人告密,帮助他们找到攻城办法。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忒斯》有两次提及此事(菲606,1340)。特洛亚亡城之后,赫勒诺斯成了皮洛斯的亲信。有别于欧里庇得斯,同样也有别于拉辛,维吉尔给予他非同一般的关注。恰恰是这个特洛亚的叛徒在亡国之后造出新的特洛亚城,也恰恰是这个新特洛亚的建城者成为给埃涅阿斯指路的人。他领着他去阿波罗神庙,为他转达神谕,向他预言前往意大利的征途(埃3:374-462)。
与赫勒诺斯重逢出自埃涅阿斯本人向狄多女王所讲的故事。维吉尔笔下的主人公身为流亡的特洛亚人不得不面临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特洛亚代表一个死去的时代和一种死去的生活方式,究竟要像安德洛玛克那样在余生中哀悼故国的逝去,还是像赫勒诺斯那样在异乡重建一个新的国度?我们不难理解埃涅阿斯的选择。他最终狠心离开狄多,正如奥德修斯在七年之后离开卡吕普索的孤岛。事实上,他初见狄多已讲过,就在特洛亚失陷的当夜,赫克托尔的亡魂托梦给他,劝他赶紧逃离,漂洋过海在异乡重建伟大的城邦(埃3:268-297)。
10
拉辛跑题否
一个异邦女子所生下的移民后代对深陷传承危机的希腊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个流亡的特洛亚人如何在外乡重建一种合理有效的生存方式?从某种程度来说,欧里庇得斯和维吉尔讲安德洛玛克的故事,讲到一半都“跑题”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跳脱出个体的自然爱欲冲动,转而关怀共同体的政治生存危机。
我问:“那么拉辛呢?拉辛似乎是做出根本性转向的那个人。他更关注个体自然爱欲的生发进程,他似乎只对谈情说爱感兴趣。”
没有戏的晚上,奥德翁剧院一带格外冷清。我隐约想起1962年拉辛的《安德洛玛克》在这里上演。那是在巴洛尔(Jean-Louis Barrault)担任剧院院长的十年间。他不但上演埃斯库罗斯、拉辛和莎士比亚,也积极介绍尤奈斯库和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乃至热内的备受争议的《屏风》。他在1968年支持学生攻占这座“资产阶级戏剧大本营”,被马尔罗罢免丢了职务,奥德翁剧院成为与索邦大学齐名的学运重镇。
贾非笑答:“我想我们现在可以让拉辛正式登場了。谈拉辛无疑有好些进入方式。就我们的话题简单说来,拉辛的安德洛玛克故事关注爱的没有回报。归根结底,这是基督宗教传统里的老问题。”
我们站在拉辛街和高乃依街的十字路口,背后是那个排列着七根大圆柱的剧院门廊。不得不承认,这是谈论拉辛的好地方。
11
四角关系
“俄瑞斯特斯爱赫耳弥俄涅,赫耳弥俄涅爱皮洛斯,皮洛斯爱安德洛玛克,而安德洛玛克只爱那死去的赫克托尔……”拉辛的《安德洛玛克》以一条四角关系的爱的单向链,为后世的爱情叙事开创了某种情节套路。每个人物均陷入自然爱欲中无法自拔,并且不可能从爱的对象身上得到回报。每个人物均身兼两种身份,一是身为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身份,一是发端于个体天性自然的有情人身份,这两种身份之间毫无例外地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俄瑞斯特斯是希腊派来的使者,要求皮洛斯交出赫克托尔的遗子阿斯提阿那克斯,与此同时,他还深爱着被婚配给皮洛斯的赫耳弥俄涅,想把她伺机带走,尽管这有悖出使的使命。在俄瑞斯特斯心中,希腊人的国家利益远不如赫耳弥俄涅的个人意愿更值得效忠:“全希腊的赞美于我又有何用,倘若我沦为伊庇鲁斯的笑柄?”(拉769-770)
皮洛斯从特洛亚回乡已一年。眼下要么交出孩子,与他不爱的赫耳弥俄涅成婚,遵守与希腊的盟约;要么听从他对安德洛玛克的无望的爱,保护那个孩子,公然与希腊为敌。在政治与爱情之间,皮洛斯同样选择爱情,为了换取安德洛玛克的“一个稍微和缓的看待”,他情愿被整个希腊所怨恨(拉290-291):“就算希腊人又一次漂洋过海,派千百只兵船来索取你的儿子,就算海伦让人流过的血还得再流,十年战后我得亲见王宫化为灰烬,我也毫不犹疑。”(拉282-287)
至于赫耳弥俄涅,她本该奉守斯巴达公主的本分:“顺从才是光荣”(拉822),却为情所困,对皮洛斯爱恨交加,以至于“放弃希腊,斯巴达,我国的疆土和我的全家”(拉1561-1562)。
在拉辛笔下的人物身上,政治理性在与自然爱欲的冲突中一次次无条件地落败。
安德洛玛克也许是个例外。她在流放地哭悼亡夫赫克托尔已整整一年。“我是个女俘,终日哀伤,我对自己都生厌”(拉301);“我那爱的火花从前被赫克托尔点燃,如今已随他深埋在坟墓中”(拉865-866);“请容我远离希腊人也远离你,哭悼我的丈夫”(拉339-340)。但安德洛玛克还有阿斯提阿那克斯。这孩子是“赫克托尔和特洛亚留给我的唯一宝贝”(拉262);“他活着像给我换了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拉279);“这孩子活像赫克托尔,是我仅有的快乐,是他留给我的爱情的证物”(拉1016-1017)——
赫克托尔的名从她口中喊出千百次……
她总吻着那儿子说,“这是赫克托尔,
这是他的眼他的唇连同他的勇敢,
这是他本人。亲爱的丈夫,我是在吻你哪。”(拉650,652-654)
安德洛玛克把对丈夫的全部哀思寄托在儿子身上。为了这孩子,“苟延着我的性命和我的悲惨”(拉377)。然而,希腊人想要这孩子的命以绝后患,而皮洛斯提供的保护是有代价的。安德洛玛克陷入两难:究竟要忠于亡夫至死不渝,还是为挽救孩子屈从皮洛斯的求婚?
女仆劝说安德洛玛克,不要顾虑死去的赫克托尔——“把贞洁看得过高反而让你有罪,就是你丈夫本人也会劝你心软”(拉982-983),而要去争取眼前的皮洛斯——“你秋波一转足以使赫耳弥俄涅和全希腊乱作一团”(拉889)。女仆的见解与欧里庇得斯笔下的老王后赫卡柏相仿,安德洛玛克应该使用政治手段完成赫克托尔的心愿,“让特洛亚复兴,在你保全下来的这个儿子手里复兴”(拉1050-1052)。皮洛斯确乎承诺过,成婚之后要协助安德洛玛克母子恢复特洛亚王权——
你的特洛亚还能在灰烬中重生。
用不了希腊人攻城所用的时间,
我能让你儿子在新起的城登基。(拉330-332)
然而,比起重建特洛亚王权,安德洛玛克显得更在意儿子的人身安危和灵魂救赎:“如此宏图再也不能让我们动心。”(拉333)她始终难忘特洛亚亡城之夜,“那惨酷的一夜,那对一个民族来说永恒的一夜”(拉997-998)。她也始终难忘皮洛斯在那天夜里“两眼放光,浑身是血”(拉999,1002)的杀人模样。但她小心翼翼不让孩子知道皮洛斯是家族仇人,恐怕仇恨连累了他(拉1030),情愿他将来“不要考虑为特洛亚亲人报仇”(拉1119)。她在赫克托尔的空冢前下了决心(拉1049)。为了救孩子,她将与皮洛斯成婚结盟,但在行婚礼之后自尽。她决心以死偿还对所有人的义务(拉1095-1097)。这就是安德洛玛克的“无罪的计谋”(innocent stratag me,拉1097)。无论对死去的赫克托尔,还是对危难中的阿斯提阿那克斯,安德洛玛克的爱毫无保留并且不求回报。
赫耳弥俄涅怨恨皮洛斯负心,责令俄瑞斯特斯为她报仇。在拉辛笔下,赫耳弥俄涅的戏份比安德洛玛克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瑞斯特斯以为赫耳弥俄涅回心转意,决心不顾国家利益挑起战争:“让我们再一次让希腊燃起战火,你来做海伦,我就做阿伽门农,在这个王国里重现特洛亚的灾难,让世人讲我们和父辈们相提并论。”(拉1158-1162)在婚礼上,皮洛斯宣誓与阿斯提阿那克斯结盟,承认他为特洛亚王(拉1511-1512)。在场的希腊人狂怒不已,抢在俄瑞斯特斯之先杀死了皮洛斯。赫耳弥俄涅承受不住她所深爱的皮洛斯之死,在发狂中自尽。俄瑞斯特斯特也在绝望中发疯。
在基督宗教传统教诲里,“爱是不忌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林前13:4-5)。拉辛笔下虽是一则异教传统神话故事,着意展现的恰是基督徒内在灵魂的撕裂问题。人做了命运的囚徒,神恩的临在无论如何不会取决于属人的意愿。欲求回报的爱让人走向自我毁灭,不求回报的爱反而使人蒙福。作为故事的结局,希腊英雄世家纷纷陨落,安德洛玛克做了王后(拉1586-1592),历代君主将在特洛亚人赫克托尔的独子身上复活(拉1071)。
12
与大师决裂
虽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同名,拉辛却声称维吉尔才是他写作《安德洛玛克》的主要参考对象。在分别写于1668年和1676年的两篇前言里,拉辛的开场白如出一辙: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卷三(引自埃涅阿斯的口述):“她低下头悲声说:‘普里阿摩斯的女儿多有福啊!在所有特洛亚女人中,只有她受命死在特洛亞高墙下敌人的墓旁,用不着沦为战利品被抽签分配,用不着给胜利者做奴妾,和主子同床席!我啊,祖国化为灰烬,我飘零海外,忍受阿喀琉斯之子皮洛斯的轻侮,在奴役中给他生儿子。他又去追求勒达的后人赫耳弥俄涅,与斯巴达联姻。俄瑞斯特斯深爱他那被抢走的未婚妻,又受着那折磨弑母者的复仇女神追逐,趁皮洛斯不防备杀了他,就在他父亲阿喀琉斯的神坛旁边。”(埃3:320-332)
维吉尔的短短几行诗包含了这部悲剧的主题,包括发生的地点、故事情节、四个主人公,以及主人公的性格。只除了赫耳弥俄涅的性格,欧里庇得斯的《安德洛玛克》里已经足够清晰地刻画了她的忌妒和行为举止。
相较于初版前言,再版前言有意地进一步与欧里庇得斯划清界限:“尽管我的悲剧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同名,主题却极为不同。这也是我在悲剧里借用欧里庇得斯的唯一地方。”这里说的“唯一地方”即是指赫耳弥俄涅的人物性格。
拉辛采取如此态度与彼时舆论有关。《安德洛玛克》在宫中演出大获成功,年轻的拉辛成了名,同时也招惹来不少诟病——有个名叫希布里尼(Subligny)的作家甚至还把大多数批评集中起来写成一出讽刺喜剧《疯狂的争辩,或关于“安德洛玛克”的批评》(La Folle querelle ou la Critique dAndromaque),隔年由莫里哀剧团演出。在这些诟病中,有一条即是拉辛改动了欧里庇得斯悲剧里的一个关键情节:安德洛玛克致力于拯救的孩子不再是她与皮洛斯所生的摩罗索斯,而是赫克托尔之子阿斯提阿那克斯。
再版前言就此问题专门做出辩解。首先,拉辛把“另一个丈夫”和“另一个孩子”当成安德洛玛克对赫克托尔的背叛,尽管依照古代记载的不完全统计,安德洛玛克先后共有过三个丈夫和至少五个孩子。
在欧里庇得斯笔下,安德洛玛克为摩罗索斯的性命担惊受怕,这是她为皮洛斯生下的儿子,赫耳弥俄涅想要母子二人一起丧命。但在这里,根本没有摩罗索斯:安德洛玛克除了赫克托尔没有别的丈夫,除了阿斯提阿那克斯没有别的儿子。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与如今我们对这位王后的印象达成一致。大多数人听说安德洛玛克,往往只知道她是赫克托尔的遗孀和阿斯提阿那克斯的母亲。人们决不相信她还会爱上另一个丈夫,生出另一个儿子。倘若安德洛玛克流眼泪是为了另外一个儿子,而不是为了她和赫克托尔的儿子,那么,我很怀疑这些眼泪还会照样深深打动观众。
夏多布里昂在拉辛的安德洛玛克身上看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典范。贞洁的人妻,慈爱的母亲。阿斯提阿那克斯是赫克托尔留给她的唯一希望:“我要去和他一起哭一会子,我今天还未拥抱过他呢。”(拉262-264)夏多布里昂赞叹这两行诗文:“如此简朴,如此可爱。这不是希腊人的趣味,这更不是罗马人的趣味。”确乎如此。从这个角度看来,拉辛做出的改动不只针对欧里庇得斯一人,甚至不只针对特洛亚英雄诗系以降的神话传统,而是充分显示出古典理性传统与启示传统的区别。不止一名古代作者写到,基于希腊国家理性的考虑,阿斯提阿那克斯绝无活命的可能,而希腊人也分明从特洛亚的望楼摔死了他。在塞涅加的《特洛亚妇人》里,安德洛玛克试图把孩子藏进赫克托尔的坟中,但被奥德修斯识破(塞164-409)。塞涅加甚至还安排报信人出场讲述那孩子被摔死的现场惨状(塞1115)。拉辛反过来设计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桥段:“为了拯救她自己的孩子免受死刑,安德洛玛克竟骗过机智的奥德修斯,原来从她怀中抢走的是别人的孩子,给阿斯提阿那克斯做了替死鬼。”(拉73-76)
确实我不得不做出改动,让阿斯提阿那克斯活得更久一些。不过,在我从事写作的这个国度里,这一点自由不可能不被认可。且不说龙萨让阿斯提阿那克斯摇身变成《法兰库斯纪》的主角,谁不知道,古老的法兰西王公均系赫克托尔之子的后代,我们的编年史让这位年轻的王子在故国覆灭之后幸存下来,以便成为法兰西君主制的建立者?
拉辛提出的第二个自我辩解的理由更为充分,也为后世的评论家做书立论提供了证据。中世纪广为流传一个传说。法兰克王的先祖名曰法兰库斯(Francus),或法兰西安(Francion),本是赫克托尔之子阿斯提阿那克斯的传人,换言之,法兰西王室乃是古远的特洛亚王族后裔。赫克托尔由此从古代英雄谱中脱颖而出,做了中世纪传说中的“骑士九杰”(neuf preux)之首。比拉辛早一个世纪的大诗人龙萨即有一部未完成的史诗《法兰库斯纪》(La Franciade)。拉丁诗人维吉尔通过《埃涅阿斯纪》这一罗马建城神话叙事来追溯罗马王族的神圣祖先,也即维纳斯女神之子特洛亚王子埃涅阿斯。法兰西诗人们纷纷仿效之,其中拉辛的溯源最是彻底,他以一出悲剧直接交代安德洛玛克如何拯救赫克托尔之子也即法兰西王族的光荣远祖。
安德洛玛克的故事发生在布特罗屯王宫,位于伊庇鲁斯地区,传说中皮洛斯在希腊以外的领地。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里讲安德洛玛克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此地。这印证了拉辛本人的见解。欧里庇得斯讲安德洛玛克的故事发生在希腊本土佛提亚,所思所虑无不是从希腊共同体内部生活的立场出发。相形之下,法兰西人和罗马人一样地自认作特洛亚王族后代,整出戏中数次提到在外乡重建特洛亚(拉220,230,330,564)。在这场关乎政治写作意图的论辩中,拉辛在寻求参考时取拉丁诗人而弃希腊诗人,既是自然而然的,又是发人深省的。
13
巴洛克不在的年代
到了“声讨”拉辛的时候,我反而踌躇起来。我发现,我对拉辛的偏见跳脱不了三百年前那场“关于《安德洛玛克》的批评”里已经澄清的问题。我原以为明确的东西只是某个更大格局的问题里的细节,好比巴洛克装饰里的一条额外蔓延开来的花边,一味执着于那条花饰就会陷入洛可可,唯有尽可能看见整个巴洛克装饰,才会明白,再怎么追求蔓延伸张的自由,也要服从对称和均衡的根本。繁复的巴洛克造型犹如一个属人性的椭圆,永在内心召唤古典理想的正圆。
我们绕着半圆的奥德翁广场一连转了三圈。我终于打破沉默,同时为抓不住重点感到苦恼:“法国几乎没有巴洛克,不是吗?正当欧洲到处兴起巴洛克的年代,法国独自坚持一种古典主义。”
贾非没有显出对我的离题话有意外。他领我走出那个小小的广场,一边接道:“那是路易十四的年代,那也是拉辛的年代。”我们走到高乃依街,街的尽头是卢森堡公园,就在奥德翁剧院背后,像一只鸟,庞大安静,潜伏在冬夜的更大的寂静里。
拉辛的安德洛玛克是十七世纪的观众所熟悉能认可的贵妇人形象,哀伤而虔诚,温柔又坚定。她不但有爱子在身边作为寄托,更有多情的皮洛斯时刻准备效劳。拉辛在初版前言里也承认:“我自作主张稍稍缓和了皮洛斯的残暴性格,这是因为,无论塞涅加的《特洛亚妇人》还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卷二,这个人物的性格均过于极端了,我想有必要略作缓解。”事实上,拉辛笔下的皮洛斯俨然脱下一身古风战士的戏装,化身为风雅剧里的贵族绅士。伏尔泰后来也批评“若干卖弄风雅的爱情场景让人更多地想到泰伦提乌斯而不是索福克勒斯,若非有此缺陷,这出戏当为法兰西古典悲剧之首”。
那么,拉辛不是简化了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不幸吗?不是冒古典悲剧之大不韪偏偏在舞台上谈情说爱吗?虽对古希腊悲剧情有独钟,他不是做了悲剧精神的反叛吗?
我们从沃日拉尔街进入卢森堡公园。天色暗下来,脚下的沙地越发的白,树影在头上比夜色更黑。园里人很少。偶有一两个散步的影子从眼前淡进淡出。
面对我发出的一连串疑问,贾非显得不慌不忙,而又饶有兴致。我知道,比起回答问题,他更乐于面对问题,更在乎让提问引领思考的过程。我们一路走,他一路断断续续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在不幸或恶的问题上,欧里庇得斯显得比拉辛现代。这是就我们今天对不幸的理解而言。委身一个残杀至亲的敌人,被迫为他生子,并且在母子遭难时那人根本不可依靠,欧里庇得斯让安德洛玛克在流亡的不幸之外平添了更羞辱更复杂的命运:她是个奴隶,并且从头到尾被当成奴隶对待。在这一点上,波德莱尔的理解很准确,他确乎深谙恶的秘密。
安德洛玛克,从伟丈夫的怀里坠下,
落在高傲的皮洛斯手心,如低贱的畜
蜷着身,恍惚地枯守一座空冢;
赫克托尔的遗孀哎,沦为赫勒诺斯的新妇!
拉辛的悲剧部部有典可考,拉辛笔下的悲剧人物却大大有别于古代经典的样貌。我们常常忽略两点。第一点,希腊人最终在婚礼上杀死皮洛斯,这就如国家理性对爱情冲动的某种惩罚。其他剧中人物因为陷入爱的疯狂而纷纷自我毁灭,唯独有德性有节制的安德洛玛克活了下来。其他剧中人物的爱欲没有孕生或传世的希望,唯独安德洛玛克有机会传下世代為王的子女后代。在政治理性与自然爱欲之间,拉辛的判断有别于拉辛笔下的人物。还有一点,拉辛的爱情戏不只违背古典悲剧规范,还公然与同时代谈情说爱的另一种文坛风气大唱反调。彼时的观众习惯了从《阿斯特莱》(Astr e)这样的田园史诗小说里走出来的完美情人形象。他们甚至无法接受皮洛斯对安德洛玛克难得发一次火说几句狠话。为了解释皮洛斯不是《阿斯特莱》的男主人公,温柔殷勤的塞拉东(C ladon),拉辛甚至援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自己辩解。
亚里士多德从不要求塑造完美英雄,而要求塑造悲剧人物,也就是说,这些人物的不幸营造出悲剧性的灾难,悲剧人物既不能全好,也不能全坏。他们不能全好,因为惩罚一个好人会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愤慨。他们也不能过分地坏,因为没有人会同情恶人。他们有一般程度的善,有无不弱点的美德,由于犯错而陷入不幸,让人怨叹而不惹人厌恶。
在当年的古今之争中,拉辛可是很重要的崇古派!他行之有效地贯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有趣的是,我们今天说到拉辛,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仿古,而是他做新。拉辛一心思慕古希腊文学,同时知道这等理想不可能为他的时代所接受。众所皆知,他是为路易十四作传的人,他显然有能力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最为严肃的问题。他确乎也尽了全力。《安德洛玛克》献给在路易十四宫中极为受宠的英格兰的亨丽埃特公主(Henriette dAngleterre)。不妨说,爱情话题迎合了凡尔赛王宫的主流趣味,同时又让拉辛有效地关注他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作为一种新传统的发端,拉辛在欠缺巴洛克精神的法国影响深远,他开出一条新路,并且后无来者。即便在拒斥拉辛时,司汤达不得不承认,法国空等一百五十年也没有等到第二个拉辛。阿尔托在二十世纪奠定残酷戏剧理论,把拉辛的心理戏视为西方现代戏剧的开端。
司汤达在讨论拉辛和莎士比亚时说,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是雅典时期的做新派(浪漫主义者),正如拉辛是路易十四宫廷里的做新派(浪漫主义者)。反过来,在十九世纪主张仍然要模仿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或者拉辛,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当时代的的法国人打哈欠,那就是仿古派(古典主义者)。阿尔托后来宣称与大师作品决裂,大致是同一意思。恰恰在拉辛的年代,做新就是仿古典悲剧。关于做新,他引欧里庇得斯来为自己辩解,说《海伦》这出戏“公然颠覆了整个希腊的共同认信”,他确实找到了最佳的例子。司汤达说过,尼采说得更清楚,欧里庇得斯当年在雅典确乎做了做新派、革命派。
我们从美第奇喷泉的背面经过。那浮雕上刻着宙斯化作天鹅与勒达相遇的事。借着一点天光,依稀可见勒达坐在水边草木丛里,端庄美丽。她没有看见角落里的爱神已然盯上了她。那只神样的天鹅翩然而至,停在浮雕的正中央,还来不及收起翅膀,头伸向水里,化成喷泉的出水口。就是那一刻吧。那一刻孕育了海伦,那个引发安德洛玛克故事的关键人物。
喷泉的水声在夜来时格外动听。我依稀记得贾非那天在卢森堡公园里还说了好些别的话。作为乡愁的化身,安德洛玛克在不同时代现身,引出新与旧转变的诸种撕裂。拉辛身体力行地探究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安德洛玛克问题。我记得他谈到卢西安·戈尔德曼重构拉辛悲剧的冉森派思想源流,谈到罗兰·巴特提出“拉辛式的爱欲”(eros racinien),谈到拉辛如何再度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批评浪潮的论辩核心。我记得他长篇大段地援引夏多布里昂,并且说我们本可以更好地领会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德洛玛克以故乡的西莫伊斯大河为一条小溪命名,在这条小溪里头藏着何等动人的真相!”
14
重要的是活下来
闭园时间到了,我们正好走到圣米歇尔大街的出口。我们出园过街,朝圣热内维尔山坡上走。先贤祠就在正前方。抬头可见一弯新月斜斜地挂在圆穹顶的上空。我一路回味贾非的话。我被深深地打动,心里的迟疑却没有化解。我们一直在讲安德洛玛克的故事,原来这是关乎新与旧的转变问题。并且,依照贾非的说法,这似乎没有标准答案。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原以为,安德洛玛克代表乡愁,也就代表过时,现在看来,安德洛玛克没有因为追忆过去时光而凝滞不前。她经历过数次如死一般的苦难,一次次地从时代的危机里活下来。她甚至活得比谁都长久,也比谁都有生命力。
“重要的是活下来。拉辛也说:‘安德洛玛克在万众欢声中走过,把特洛亚的记忆一直带到神坛(拉1437-1438)。多少好作者湮没在历史的沙尘里,多少好纷争褪尽本朝代的鲜颜。传世的经典不会僵死,必要有活水般的流动。”
贾非这么说时,我们站在圣热内维尔广场。我隐约想起,就在四周不远的好几处地方,拉辛也以种种方式“活”了下来。他的骨灰安放在几步之遥的圣斯德望堂。古老的圣热内维尔图书馆前厅有他的头像。不远处巴黎高师的院落里也竖着他的像。山坡下的克吕尼索邦地铁站,抬头可见天花板上他的签名,大写的R字拖成长长一撇,由红蓝的马赛克细砖拼接而成。而在拉丁区的另一头,维斯孔蒂街24号,一扇暗绿的窄门上钉着小铜牌:“1699年4月21日,拉辛在此与世长辞”……
但不止如此。远不止如此。这些是看得见的标记,石头的僵硬的,还有更多无名无形的,转瞬即逝,而又源源不断。只要有人想起他的名,有人在读他的诗,只要有人演他的戏,有人看他的戏,只要有人追问古典主义,有人反思现代性,拉辛就活在那数不尽的瞬间里。当里维特在六八年代通过《狂爱》宣告一种电影美学革命时,看似与拉辛无关,而拉辛形同又活了一回,活在那个喧哗与骚动的年代里。
在里维特的电影里,一对夫妻要在三周时间里排演拉辛的《安德洛玛克》。他是导演,她是扮演赫耳弥俄涅的女主角。电影里有大量镜头表现了演员聚在一起朗读、讨论和表演拉辛剧本的现场。有一支拍摄团队进场全程跟踪,记录下三周的排戏过程。女主人公不能适应现场被拍的干扰,在与丈夫发生争执之后,中途退出排演。男主人公的前妻代而担纲主演。随着排戏推进,男主人公与前妻的合作越来越亲密,在生活中与妻子也越来越疏远。女主人公发现自己就像拉辛戏中的赫耳弥俄涅嫉妒皮洛斯和安德洛玛克那样,无法克制地嫉妒自己的丈夫及其前妻,更进一步说,她为无法参与丈夫以戏剧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而受尽折磨。里维特说,这是一出關乎嫉妒和疯狂的电影。同样的故事情节在戏里和戏外平行展开。女主人公像赫耳弥俄涅那样,在疯狂中想要自杀并杀死丈夫。
电影交叉运用两组拍摄方式。一组是纪录片导演拉巴尔特(Andr Labarthe)负责用16毫米胶片全程拍下话剧排演的过程,类似于他自1963年以来制作《我们时代的电影人》(Cin astes de notre temps)采用的做法。另一组是里维特用35毫米胶片拍摄演员们在排戏之余的日常生活场景,并且是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记录演员们的即兴表演。里维特本着“电影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个理念,在当时做了好些实验性尝试,诸如导演不干预演员的表演,拍电影的行为本身即是电影的主要构成部分,等等。两组记录方式的交叉组合清楚地呈现出主人公的戏剧世界和现实生活互相交错、互相发生影响的样貌。
在这部六八年代的电影里,拉辛的戏剧虽以安德洛玛克为名,却是赫耳弥俄涅真正引发时人的共鸣。她感觉、观察乃至想象丈夫的外遇。而他就像皮洛斯那样陷入没有回报的爱中,只不过,外遇的对象与其说是前妻或某个女演员,不如说是大写的戏剧本身。他不断付出,不断挫败。从某个时候起,戏剧与现实已然交缠在一处,让人无法自拔。在里维特的版本里,作为赫耳弥俄涅无法战胜的情敌,安德洛玛克从根本上已不是某个具象的人物,而干脆化身为名曰“安德洛玛克”的那出拉辛的戏。
电影的结尾耐人寻味。开演前夕,男主人公在巴黎的街上独自走了很久。空荡荡的无人的巴黎的街。一开始他还轻快地哼着歌,东张西望,但渐渐地他的神情越来越凝重,街两边的建筑仿佛要压到身上。有那么一刻,他在街角的一面镜子前停住,认真看镜中的自己。走在巴黎的街上,这似乎对六八年一代具有特殊的意义。与此同时,剧场里找不见导演,观众坐等在座位上,舞台上空荡荡的。
贾非说:“里维特以戏剧方式思考严肃的政治问题,当代电影导演中没有人比他更深谙古典主义戏剧。他的电影里总有人在尝试排演古典戏剧,《巴黎属于我们》中也有一群年轻人在排莎士比亚的《泰尔亲王伯利克里》,同样状况连连,连性命都搭进去。我想他的思考有一点很好的意思,甚至新评论的行家们也未必能有。今人演一出古人的戏,重点不在于重新阐释,思考今人带给老戏,而是思考老戏带给今人。重点在于越是投入戏中,越能清晰地照见每个个体日常生活的撕裂。”
15
巴黎不属于我们
我们绕过圣热内维尔图书馆,沿着窄窄的石子小路下山。
我边走边想里维特的电影。《巴黎属于我们》的本意是“巴黎不属于任何人”,语出佩吉写于1910年的《维克托-玛丽·雨果公爵》 。如书名所显示,佩吉仿效雨果的做法,谈论巴黎,实为谈论人群,谈论现代性世界的人的困境。并且无独有偶,书中长篇大段的文学批评指向拉辛和高乃依。
从什么时候起,巴黎不再属于任何人?至少可以从试图在文学中定义现代性这个概念的波德莱尔那里算起吧。在波德莱尔书写“巴黎的忧郁”时,巴黎不再属于任何人。我隐约想起有个关于希腊古人的说法,生活在城邦里,就是作为共同体生活的一员并且感觉自己不可或缺。如果说拉辛还一心思慕古希腊,在波德莱尔的心里确乎没有古希腊了。本雅明说过,波德莱尔心目中的古代是罗马,作为与现代巴黎遥相对应的古代城邦。古希腊只有一次进入波德莱尔的视野,从女诗人萨福生活的勒斯波斯岛(Lesbos)引申出女同性恋者(lesbienne)这一现代性世界的女英雄的意象。
波德莱尔一直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朝一日能够像古代作者的作品那样被人阅读时,他已经体会到古人对永垂不朽的追求。“所有现代主义都值得有朝一日变成经典”,对于他来说,这规定了艺术家的基本使命。在他生存的那个时代,最接近古代英雄的任务,最接近赫拉克勒斯的功绩的,莫过于时代赋予他而他也心甘情愿担任的任务:阐明现代性。……波德莱尔艺术理论中的美学思考丝毫没有呈现现代主义与古典古代的相互贯通,而这在《恶之花》中的一些诗歌里却有所体现。在这些诗中,《天鹅》最为重要。
写《天鹅》的波德莱尔站在新的卡鲁索广场。那一带从前是喧闹的老城区,坐落在罗浮宫与卡鲁索凯旋门之间,和所有首都心脏的街区一样龙蛇混杂,陈旧拥挤而又生气勃勃。1848年革命期间那一带发生暴力流血事件。隔年,奥斯曼启动更新计划,老房子被拆,老巴黎人被迁,老城区被夷为废墟工地。本雅明分析过奥斯曼在这座十九世纪的首都进行改造的政治意图,既是避免内战杜绝巴黎再起街垒的可能,也是要抹去剛发生的武力冲突在巴黎人心里留下的伤痕记忆。波德莱尔把这首诗献给流亡中的雨果,并在开篇提起安德洛玛克,因而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某个清晨,天空冷而明亮,一片狼藉的工地遮蔽了城市的旧模样。整个世界在慢慢睡醒,白天的劳作即将开工,满地垃圾在死寂的空气里扬起黑风。就在那时,仿佛在神话中般的,诗人看见一只天鹅——
我看见一只逃出笼的天鹅,
蹼足擦着街石,
白羽毛拖在糙地上。
那鸟张嘴在无水的沟边,
烦躁地在尘灰里洗翅膀,
一心想望故乡的好湖,它说:
“水啊,你何时才流?雷啊,你何时才响?”
我看那不幸的鸟,古怪致命的神话,
几次向天,如奥维德的人物,
向嘲弄人的蓝得残酷的天,
抽搐着颈,把贪婪的头伸直,
仿佛那是在向神发起责难!
奥维德的变形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单从诗人指明的参考文献看,天鹅就有诸多譬喻的可能。从前的宙斯王化身天鹅,从前的天鹅如神一般。这才有海伦,才有十年特洛亚战乱,才有安德洛玛克的故事。然而,在波德莱尔笔下的十九世纪的首都,不但安德洛玛克,连那神样的天鹅也一起做了现代性世界的流亡者。高贵的公主沦落为异乡的奴隶,洁白的天鹅坐在城市的污秽堆里,翅膀沾满厚厚的尘土,好比赫克托尔的遭遇,他活着时骑马征战何等骄傲,死后被马拖在地上,“在自己的祖国被恣意凌辱”(伊22:404)。错位的,荒诞的,不自在的,屈辱至死的。波德莱尔以诗的意象准确地譬喻现代性生活里的人的困境。
天鹅对天说话。这是诗中唯一拥有言说能力的造物。芸芸众生中只有人抬头看天。看天是希腊哲学传统的标志性动作,与启示传统相悖。看天是人的理性抬头,努力地无限接近神。这让人想到奥维德的变形故事。天鹅也许就是其中的某个主人公,因僭越与神的界限,从人形贬为鸟。半个多世纪以后,卡夫卡写出另一个更彻底的现代变形记,天鹅变成一只丑陋的虫。
巴黎变了!我的忧郁却没有
一丝偏移!新宫殿,脚手架,大片城区,
老旧的市郊,一切在我眼里如譬喻,
而我珍惜的记忆比石头更重。
这罗浮宫前有个景象在压迫我:
我想起我的大天鹅,发了疯的动作,
好似那些流亡者,可笑,崇高,
被无尽的爱欲撕咬!我想起你,
安德洛玛克,从伟丈夫的怀里坠下,
落在高傲的皮洛斯手心,如低贱的畜
蜷着身,恍惚地枯守一座空冢;
赫克托尔的遗孀哎,沦为赫勒诺斯的新妇!
安德洛玛克就这样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走出来,未加修饰直接走进波德莱尔的诗里。没有新添补的故事情节,甚至没有心理言说的机会。她只是一味哭泣,眼泪流成河,这记忆的长河激活了诗人的思绪。一个古代女战俘想念故国和亡夫。一只流亡的大天鹅想念故乡的湖。一个当代移居欧洲的女黑人想念非洲的椰树。“她们的共同特点是为现实悲伤,对未来绝望。这种惨淡构成了现代性与古典之间的最紧密的联系。”本雅明的话不妨进一步理解为,这一点紧密然而单薄的联系也标注了现代性与古典之间的根本分离。
历代作者讲安德洛玛克的故事,无论欧里庇得斯还是维吉尔,甚至拉辛,均不可避免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安德洛玛克生活其中的政治共同体的命运。身为流放者的安德洛玛克在流放地没有归属感,这是波德莱尔身在巴黎想起她的原因。身为流放者的安德洛玛克必要给流放地带去意外的生机,这最终成了《恶之花》的疑问。巴黎变成一个精神还乡的重大譬喻。数不尽的安德洛玛克流浪在这个没有国族名目的现代性荒原,不再感觉自己是共同体的成员,自我否认,也被他人否认。孤儿,被遗忘在孤岛上的水手,被俘虏的和被战败的,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是名曰“巴黎”的现代性生活里数不尽的外乡人。没有名字,他们是褪去了声名光环的安德洛玛克。但有更惨淡的,他们在记忆的河里渐渐丢失那渐渐模糊的原乡,沦为没有赫克托尔的安德洛玛克。
我想起那消瘦的痨病的黑女人,
走在泥里,迷离的眼看向
看也看不见的大好非洲的椰树,
在那堵没有边的大雾的墙后。
我想起那些丧失之后就永远,
永远找不回的人!那些流泪的人,
吸吮痛苦就如吸吮母狼的乳汁!
我想起如花般枯萎的瘦孤儿!
我想起被忘在孤岛上的水手,
想起被俘的和战败的,想起其他许多人!
我们在学府路街口左拐,走过法兰西公学院,再过圣雅克街就是索邦大学。那些白色的巨石建筑屹立在藏蓝的天空下,人在暗黄的街灯影里格外渺小。我们走过佩吉当年创办《半月丛刊》的索邦街,在羊肠小道般的尚波利昂街拐弯,一连经过三家毗邻的独立电影院。最里的拉丁区电影馆赶上开映点,门前排着长队。继续往上走,经过拉辛的另一处故居,小街尽头就是索邦广场。
上晚课的学生三三两两。广场上的咖啡馆相当冷清。在我念完书的那年,大学出版社书店停业。一晃十年过去,书店新近在对街重新开张,门面很小,买书的人在电脑中随选书目并现场印刷装订,人称书业革命,轰动一时。广场上还有一家佛兰哲学书店,也是开了上百年的老店。到了打烊的钟点,白天摆在门外的几只书箱收了,陈列新书的橱窗还亮着光。
贾非轻轻伸手往空中挥了挥,好似要赶什么。他见我看他,嘴角牵起一丝笑意,低低地嘟哝一声:“真安静,不是吗?”我努力追赶上他的思绪,想象另一个索邦的样子。六八年代的索邦,到处是拥挤的人潮,梯形教室里,广场上,长廊里,楼梯上,各种论辩声音此起彼伏,空气中飘浮着热情洋溢的气味。我不由得深呼吸,但吸进的只是一股冬夜的寒气。我的想象必定是浅薄的。到我上学的时候,三大与四大的比较文学系隔着一条窄窄的走廊对峙而立早已成了传奇。好比公学与大学,渐渐地一块儿笼罩在权威的光环下,渐渐地一块儿化作不朽的石头标志,渐渐地让人好似不必在意最初那些成立理念的天壤之别。
“老巴黎不复存在,城市的样子哎,比人心变得还快?”
我笨拙地学了一句波德莱尔的话,末了帶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再次想要向他求证那个过去的年代。但他一如既往只笑而不答。
贾非说过,他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遗憾的是没能为子女后代留下同样的好。贾非没有子女,但我大约能懂他的意思。巴黎人抱怨巴黎正在僵化成一座博物馆,让人百无聊赖的。我想起在我常年客居的城市,转变倒是没个消停地扰乱日常的节奏,让人措手不及的。我心里突然有些怅然。我明白贾非与我的这些交谈算不得什么真正的对话,既不针锋相对,也无起承转折。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起散步各想各的。我们的想法偶有交集,更经常是南辕北辙。我很期待听他说说年轻时的事,但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也很想对他说说泉州,说说少时的钟楼,或西街的双塔,但我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那天我们在夜风中站了很久。贾非念着之前没念完的诗。我静静地听。我们彼此心知肚明,不是所有的疑惑都能从一首诗中找到答案。
16
特洛亚战争将爆发
我再走进贾非的旧书店时,那盆孤挺花花事已过。花瓣枯了瘦了,只剩一点红,挂在花枝上。我恍然注意时间的快。我在此地暂停,很快又要离开。
贾非一见我就说,那天的话题还缺一个小小的尾声。
荷马之后,几乎无人敢重写赫克托尔在世时的安德洛玛克。但也不是没有例外。季洛杜的《特洛亚战争不会爆发》讲述荷马之前的安德洛玛克的故事。整出戏发生在特洛亚战事爆发前夕,安德洛玛克新嫁给赫克托尔,尚未做母亲。这出戏于1935年11月首演,包含了作者对战争的诸多思考。正式定名前,季洛杜先后想过不同的标题,诸如“海伦”“前奏之前奏”(Pr ludes des pr ludes),还有“伊利亚特前传”(Pr face lIliade)——终场最后一句话确实指向了荷马:“特洛亚诗人死了,轮到希腊诗人开始吟唱。”(季551)
安德洛玛克在开场高声喊出第一句话,也即作为标题的那一句话:“特洛亚战争不会爆发,卡珊德拉!”注定要落空的话。特洛亚战争会爆发,而巴黎不属于任何人。人心的挣扎和撕裂在现代作品的标题里头就看得分明。在整出戏里,安德洛玛克主要有四场对话。她一次次表达心愿,试图说服对方,依次是卡珊德拉(第一幕第一场)、赫克托尔(第一幕第二场)、普里阿摩斯(第一幕第六场)和海伦(第二幕第八场),一次次以失败告终。
卡珊德拉是赫克托尔的妹妹,阿波罗女祭司。安德洛玛克没能让她也赞同“战争不会爆发”。卡珊德拉虽盼望和平,却洞察到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就在眼前,自从满城皆是这种断言,说是世界和世界的走向总的来说掌握在人类手里,特别是在特洛亚的男人和女人手里。”(季484)
赫克托尔刚打完前一场仗,回到特洛亚,满怀信心要去关闭战争之门。安德洛玛克告诉他帕里斯带回海伦的事。她没有说服卡珊德拉,反倒被说服了似的,担心战争之门还会打开:“战争在特洛亚城里,战争刚才在城门口迎接你,是战争而不是爱情把无措的我交给你。”(季489)赫克托尔不能理解她的不安,认为只要让帕里斯交还海伦就能避免战争。赫克托尔如卡珊德拉所说的相信“世界和世界的走向”掌握在自己手里。
赫克托尔很快发现,不但帕里斯不肯交出海伦,而且普里阿摩斯以降的特洛亚男子们一致反对交出海伦。海伦在不知不觉中颠覆了每个特洛亚男人的常态,在他们身上激发出根本性的转变。在战争正式爆发以前,每个人已然在自身掀起一场名曰海伦的战争。诗人因为海伦而大大干涉城邦政治,最终直接做了战争的导火索(季503,550)。几何学家本该讲求科学的理性和精确,却因为海伦而比诗人更像诗人,把海伦的步子、肘长、目光和声音所及的距离当成唯一的丈量标准,声称特洛亚风景因为美人的来临才有了意义(季497)。德高望重的长老们本该在城门下迎接凯旋的士兵,却变成比小青年还要狂热的仰慕者,痴痴等看海伦出城(季493)。更不用说帕里斯为海伦着迷,一改喜新厌旧的本色:她不同于“特洛亚本地类型的女人”,若即若离,“她在场时又不在场,这比什么都值”(季491)。就连少年特洛伊罗斯也在海伦充满挑逗的目光下迅速长大,在终场时分接替帕里斯成为新情人(季550)。
在众人面前,安德洛玛克代表“普天下的妻子”(季501)与普里阿摩斯王展开争辩,徒然地想阻止“最英勇的丈夫死在战场上”(季502)。但她不可能说服坚决主战的特洛亚男人们,于是转而请求海伦爱帕里斯,唯有如此,她即将承受的一切苦难才有正义的理由——
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未来若建筑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的故事的基础上,那还不算坏……我们若要为一对名义夫妻受苦送命,岁月福祸、思想习惯和百年风俗若要建筑在两个不相爱的人发生艳遇的基础上,那太可怕了。爱帕里斯吧,要么就明说我看错了你,告诉我他死了你也不想活,告诉我你情愿为救他而毁容。这样的话,这场战争就只是灾难,而不是不义的。这样的话,我会尽量忍受。(季530-531)
海伦回绝了安德洛玛克,坦承自己不爱帕里斯:“如果说只须有一对完美的夫妻你就能接受战争,那么,安德洛玛克,总归还有你们这一对呵。”(季533)季洛杜还原了荷马诗中的那对特洛亚模范夫妻形象,并且始终以帕里斯和海伦做反衬。在众人批评女人天生善变时,老王后赫卡柏站出来维护:“让安德洛玛克清净点吧,女人的是非与她毫不相干。”(季500)卡珊德拉说赫克托尔也许只会为了安德洛玛克一人去打仗,赫克托尔则声称他们情愿自杀死在一起:“安德洛玛克和我已经商量好了躲过一切牢笼彼此重逢的秘密方法。”(季498)
在季洛杜笔下,安德洛玛克一方面当众坦言,倘若赫克托尔不是她的丈夫,那么她会不顾声名美德,情愿和他私奔,为他私生孩子(季500)。另一方面,安德洛玛克又以明白无疑的动人口吻指出,夫妻相爱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如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人在相爱时并不相和。一对相爱的夫妻,生活永是缺乏冷静的。真夫妻与假夫妻的聘礼大致一样,就是原始的不和。赫克托尔与我截然相反。我的趣味爱好,他一样也没有。我们过的日子不是互相征服就是各自牺牲。相爱的夫妻是面目不明的。(季531)
依据柏拉图的爱欲传统,爱本来是无法分享的,相爱不是爱的必然本质。安德洛玛克与赫克托尔的爱情因此在特洛亚城绝无仅有。但即便如此,安德洛玛克渴望和平和天长地久,赫克托尔崇拜战争和声名不死。他们的趣味截然不同,对生活各有期待。赫克托尔天生热爱荣誉,渴望美好的声名,“在战斗的时刻感觉自己是神”(季487)。他一方面向妻子承诺战争不会爆发,另一方面又承认,战爭吸引他,向他“许诺善良、慷慨”,乃至安德洛玛克“也是战争赋予我的”(季488)。赫克托尔在与希腊来使奥德修斯谈判时发现,交不交出海伦,战争都不可避免,关键问题是希腊贪图特洛亚的富庶:“拥有过分金灿灿的诸神和庄稼实在不够审慎。”(季547)出人意料的是,奥德修斯声称要和赫克托尔一起阻止战争爆发,因为“安德洛玛克那闪动的睫毛和佩涅洛佩一模一样”(季549)。
然而,从古到今,妻子的眼泪鲜少阻止得了丈夫上战场。终场时分,赫克托尔亲手松开安德洛玛克捂住耳朵的手,亲口向她宣布:“战争即将爆发。”
贾非陆续从不同的书架找出季洛杜的旧书,摆在窗前的书台上。《特洛亚战争不会爆发》有格拉塞出版社在1935年的初版,此外有同一年《小插图》(La Petite illustration)半月刊和《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月刊的预印。《巴黎杂志》同期有瓦莱里的评论专稿,将季洛杜称为“哲学家和年轻的命运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