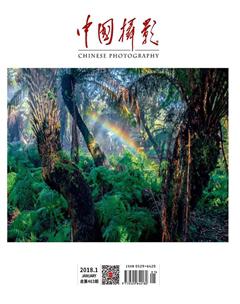他们如何去爱
任悦
阿琳·戈特弗里德(Arlene Gottfried) 并未告知她的朋友自己身患癌症的事实。兴许,最佳的,能够定格她的样子是在2012年Look3摄影节,这并非因为舞台上的屏幕里放映着的是她一生的作品;而更是因为她是这个舞台上的歌者。这位摄影师的名片上印着:“歌唱的摄影师”,被一间教会的唱诗班感染,她也加入其中,并最终成为独唱。是以,舞台上,她的歌声与她的照片同步。你发现,这照片和她的歌声出奇地相似,悠长的,一种关于生的旋律。她的每一部作品都由时间写就。
阿琳被称为记录纽约城市变迁的街头摄影师,她的拍摄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但她的观看并非散漫,一个场所,一片地域,一段人生,在其中所融汇的各种复杂性都被她的照片包含其中。她陪伴自己陷入各种麻烦的朋友,记录他的生命历程二十年;她观察纽约波多黎各社区将近四十年,她最后一本书《妈咪:三代女性》(Mommie : Three Generations of Women),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时间跨度四十年,祖母和母亲相继去世,她们在世的最后的日子是极度痛苦的。书的最末了,是艾琳妹妹孩子的出生。
“衰老,病痛,死亡,那都是生命的一部分。”阿琳将之毫无遮掩地呈现给我们,她让我们看到死亡阴影在追逐每个人,你感到压抑,却同时也得到了一种安慰。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做到这点。我发现,在她很多的照片里,被摄对象都盯着镜头,无论是路人、流浪汉、舞女、孩子,还是她的母亲,这种观看,也许用阿琳朋友们追忆她最常用的一个词来形容最为恰当—温暖。
夏天偶然间我竟买了这本书,我的一位学生将之借走,她也在拍自己的家庭。
摄影与音乐的关系,罗伯特·德尔皮(Robert Delpire) 也在一次访谈中被追问这个问题,我猜想,访谈人是想问出这位出版人,策展人,导演,平面设计师是否会以音乐的思路来处理一本书、一个展览、一部电影。尽管并未获得直接的回答,但是其在言语中早已透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更深远。他说自己阅读照片从来都是靠感情而不是论证,所感超过所思;他谈及处理照片与文字的关系,处理照片与照片之间的关系,这些各式元素之间的合作就仿佛一场音乐会的合奏。当谈到涉及一本摄影书出版的各个环节,他说艺术家永远是主角,其他人都是陪伴。陪伴,这个词难免会让人想起他如何跟随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前往伊朗拍照,与寇德卡一起工作,为他的作品《流放》撰写文字,做图书设计。您喜欢团队合作吗?面对这个很多人会感到头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与他认定的朋友都保持着亲密距离,这也就多少回答了为何他能创造出小黑书(photo poche),这套小书有着亲密的尺寸,你可以用一只手把握,但内容是厚重的,凝聚的是一代又一代摄影师的智慧,从历史到社会,这几百本书因其谦卑的尺寸,一本又一本,在一起挤挤挨挨。
人们对佩泰·特纳(Pete Turner) 的追忆也与音乐有关,他为不少爵士乐手拍摄专辑封面。这种关联并非偶然。佩泰的父亲领导着一支有着23人的爵士乐队,从小他就沉浸在一场又一场的爵士演出中,佩泰提到,他着迷于观看这些乐器独特的外形以及其中映射出的影影绰绰的画面。
“有着剧作家般对事件的直感,强烈而又浓郁的色彩”,这是评论人A.D.科曼( A. D. Coleman)对其作品的形容。颜色是人们对佩泰作品又一常见的形容。能够操控色彩与他的学院派训练很有关系。1956年,佩泰·特纳从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毕业,他的同学是著名的报道摄影师布鲁斯·戴维森( Bruce Davidson)以及超现实主义摄影师杰利·尤斯曼(Jerry Uelsmann)。这些人可谓美国第一代学院派摄影师。更加上从40年代开始拍照,佩特经历了画报的鼎盛时期,他所供稿的媒体是《展望》《体育画报》《国家地理》……
这位生命停止在83岁年纪的摄影师,经历了摄影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形态从成长到繁盛,以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从摸索到成熟的过程,他们这一代,对摄影的热爱已不仅仅是自发,同时也是自觉。
一种语言的形成,不仅需要作者,同时也需要读者,他的生命跨越一个世纪,图片编辑约翰·莫里斯(John G. Morris) 是照片的第一代专业读者。人们称他为传奇人物,但在他离开,他才在他所编辑过的照片中慢慢显现,显现在卡帕的诺曼底登陆照片之中,在艾迪·亚当斯( Eddie Adams )的《西贡处决》之中,在黄功吾(Nick Ut)的《战火中的女孩》之中,后面两张影响越战期间美国国内舆论的照片,因其画面中的“恐怖”,往往会在传播中被“净化”,约翰坚持将之原本呈现。
2016年,这位100岁的老者还曾接受与之合作最为紧密的玛格南图片社的采访。谈到战争,他请摄影记者们思考:“为什么我们拍下如此之多的战争照片,却依然还有战争?难道我们去报道战争就是为了给士兵以一个英雄化的形象?这是我们想要做的?”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去询问斯坦利·格林(Stanley Greene) ,作为当代著名的战地摄影师,他活跃在阿富汗,伊拉克、车臣,格鲁吉亚等地区。一些图片编辑小心翼翼地遵循着早餐法则,为让读者不要在早餐阅报的时候感到恶心,要对照片做一定删选。而斯坦利却坦言他的目的,“你坐在家里吃着麦芬蛋糕与蓝莓,你不想看到毁掉你的早晨的照片。但这就是记者的工作,让你从早晨就感到沮丧。”
就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他在荷赛的颁奖礼上致辞,舞台上,他着黑衣,唯有一点点灯光,嗓音沙哑,他阅读着自己纸上写的文字,诗一样的语言,他谈到报道摄影师的忠诚,谈到自己的孤独,关于拍摄之后无法改变现实的内疚,谈到他喜歡坐在窗前写作,而摄影却也是一种视觉的沉思。背后的屏幕上是他一生的作品。
“假如有年轻人非要当战地摄影师,我会告诉他们,你要拿命换,假如他们坚持要问,我要告诉他们这个选择的后果,其中没有荣光。”
纪念他的文字太少。他说当想到每个人终有一死,就会给足自己勇气。而让他激动的从来都不是砰砰的枪响,他说:“一天末了,所期待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