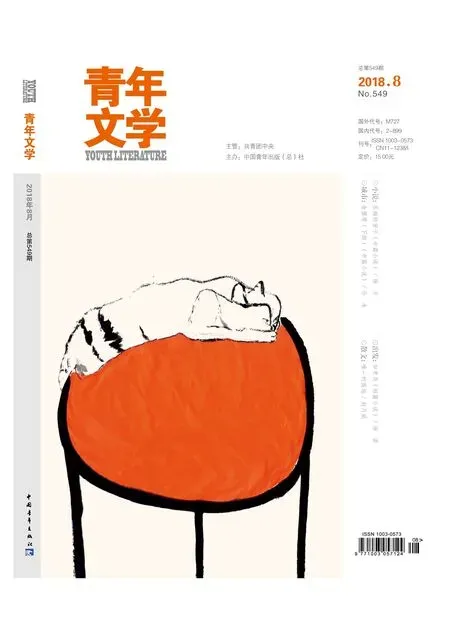唯一的高地
⊙文/赵月斌
大平原上唯一的高地就是这儿了。这唯一的高地却成了我精神上的重要寄托。它是我的精神高地,每一次登临都意味着一次扩张和高飞。大平原上突兀而起的这块高地给了我超越地平线的依持,让不甘拘囿于现实的我得以四望远处缥缈的风烟和模糊的形影。
我把这唯一的高地叫作雪儿。在我的想象中,是两千年前的那个严寒的冬天吧,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凝固成这座梦幻之城。也许从那时起,这座城就开始融化了。
确切地说,这片高地是一处古城遗址,是片古老的废墟。这片以土夯筑的城墙来于土地却高于土地,它漠然地匍匐于四野乡村之间,似乎又回复于土地了。如果你不注意去分辨或者不了解它的历史,你很容易把它误认为土地的自然隆起,但是,它的确是一座古城,在史书上它的名字叫作薛。
薛国故城位于鲁南平原的滕县境内。《滕县志》载:“薛国……周二十八里,盖古奚仲所封国,城则田文增筑。”面对这段贫瘠的文字我只能揣想被它掩盖了的繁华。我情愿相信那些美丽而离奇的传说,比起车祖奚仲和食客三千的孟尝君来,让我更感兴趣的倒是那位早夭于豆蔻年华的奇异公主和那个使薛城在顷刻间化为灰烬的怪物“祸”。
我下意识中竟觉得那纯洁无瑕的公主应该叫作雪儿。雪儿,我这样呼唤你,你该听见了?你骑一匹白马掠过空旷的平原,闪电一般倏忽而逝。你一袭长发流泻至今,你一支利箭射向沓沓无期的星辰。雪儿用生命的瞬间留下了永恒的背影,千百年来一直美目盼兮,气宇轩昂。痛失娇女的国王用奢侈的方法埋葬了雪儿,八个方向的八座坟墓给后代留下了几多疑惑几多迷狂。如果按一般的方法,国王以倾国之资为公主殉葬,八座坟是为迷惑那些觊觎金银财宝的人。我却不这么想,因为八座坟毕竟还是给了人们八种可能,国王不会这般简单,至少,他会用八座坟掩人耳目而另外为公主选择绝佳的安息之地。或许,做父亲的晓得女儿生性不愿拘谨,所以才给了雪儿这么多休歇的地方,让雪儿继续打马远行。这八座坟如今成了八个村庄,但它们冠以“堌堆”之名:刘堌堆、高堌堆、白堌堆……我只听说有的村庄从前还有一个高高的土丘,那就是雪儿的坟吗?还听说有个村子曾在“堌堆”里挖掘出一些碗盘之类的器皿,村人以其做红白喜事的器皿之用,但“文革”中,这些古董被“破四旧”的破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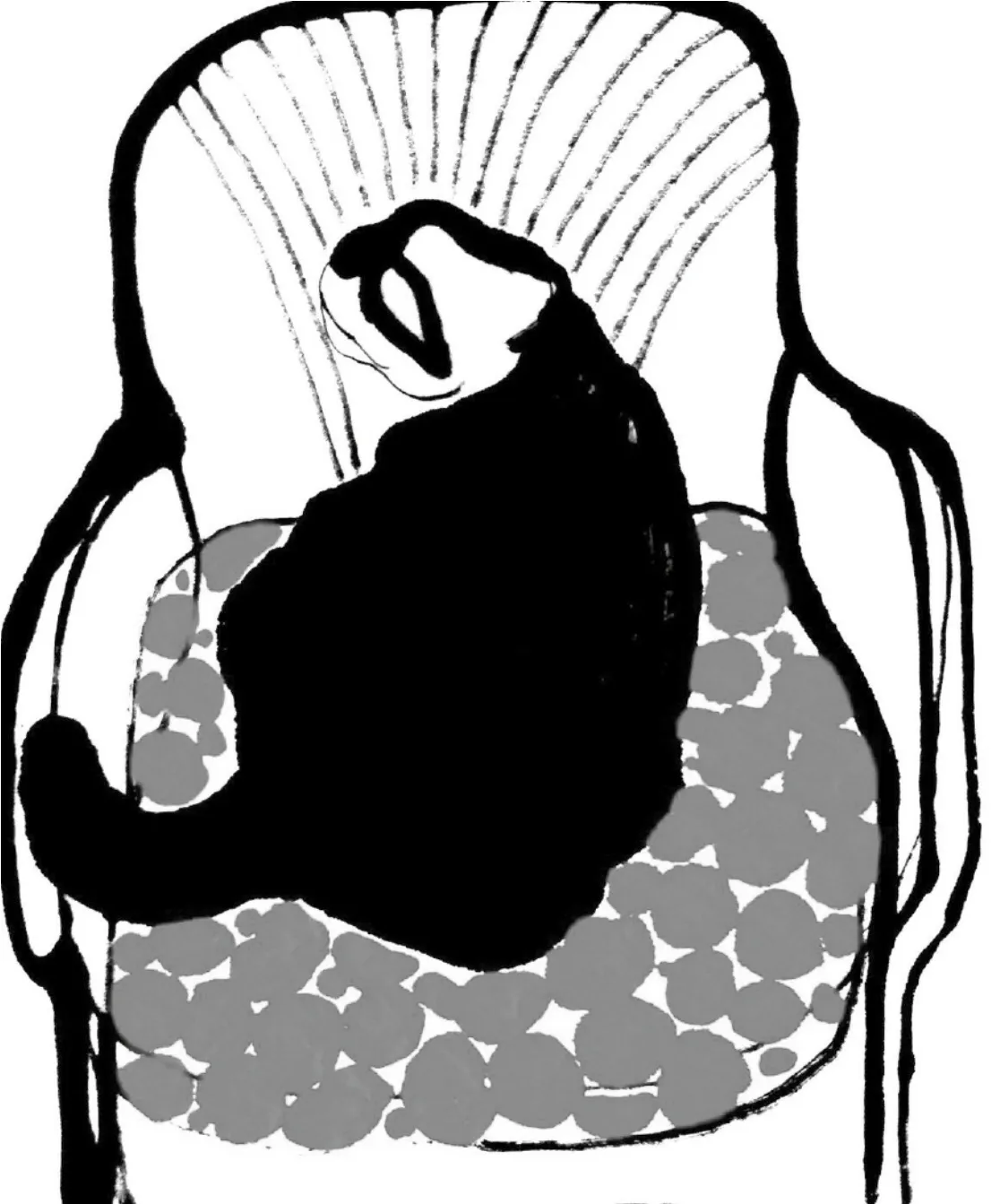
⊙陈 雨·猫6
这八个“堌堆”曾引得历代目的不同的人前来寻宝,可所有的人都失望而归。这是雪儿跟人们开的玩笑吗?她用她的死捉弄了所有活着的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许那宝物确确实实存在着,但永远也不会被人找到──这莫如说宝物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如果人们只顾四处寻找那纯属子虚乌有的宝物──这又等于承认那宝物确确实实存在着。世上很多事不都是这样吗?有或无,永远都无法应验,人们只能屈从于模糊,屈从于懵懂。这也是一种明智吗?我曾觉得自己、他人,包括身边的一切:地球、太阳、宇宙,是不是都是另外一个人的梦?一旦他猛然醒来,所有的光怪陆离都会消失。所以,人的最佳状态就是处于混沌,如果陷入生死荣辱之外的冥想,就会趋入绝望。
人只能安慰自己,借最后一点幻想。雪儿是我登临古城时最后一点幻想。这位单纯的公主当然不会想到她的死其实意味着大薛国辉煌的终结,她悲痛的父亲竟然为此断送了一个国家。老国王接受了一个诸侯国的礼物“祸”(我只能很主观地猜成这个字)──这是一个吃铁吞金的怪物。老国王最初侍弄着这个可爱如猫的小家伙倒也暂时忘却了失女之痛。可“祸”却日渐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老国王不得不以兵器盔甲填塞“祸”的巨口。三月后,那怪物已大比王宫。薛国王惊恐之间令人驱“祸”出城。然而城门太小,早有怨声的薛人拼命往外赶。谁料这怪物喷烟吐火,偌大一座城池顿时化为一片焦土,剩下的仅仅是那一圈悲哀的城墙。这一圈城墙围拢了一片骄傲,留下的却是一场悲凉。所有的鼎盛必以衰败的结局映衬方能遗世而立吗?像秦纳四海八荒终究还是破灭,像古罗马帝国占三洲之地还是不免消亡。也许盛极一时是必然,这世间原本就是盛衰剧变的轮回。可我还是悲哀。
因为薛国的强盛了无踪迹,史书无载,民间亦无口碑,即是终生处于废城中的村人也不会想到从前这座城池该是何等荣耀,连素有“善国”之称的滕也难与之比肩。这座曾拥有六万之家的战国古城内,如今散落着十二个村庄,那个叫皇殿岗的村子据说就处于当年的王宫位置。然而无论如何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明薛国强盛的痕迹,而且人们一向漠然于过往,很少有谁在意这座城缘何而筑、缘何而毁。他们心中从来没有有关薛国的骄傲或耻辱,这一城墙在他们眼里全然是土地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所以古城墙上种满了庄稼,有的地方已因烧砖瓦窑夷为平地。本来就已颓败不堪的古城墙更加伤痕累累,它不再连贯,生活于其中的人似乎打通了很多通向外界的缺口……
不过,这片平原并未因此再度繁华,薛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熄灭了。骤然间的明亮之后一片黑暗,人们只能从秦汉的残砖断瓦摸索至唐宋的破陶碎瓷,从元明的动荡流离逃亡到大清的内患外辱,民国的枪炮声还响在远方,人们不经意已走到今天。这悠长的历史静如麦子的生长收割,一茬一茬的人终究没有收获祖先的荣耀,大平原依然平整如旧,只是那一段一段的城墙和一个一个的堌堆偶尔阻挡你的视线,它是在提醒也是在逼迫你──登上高地。
登上高地其实一点也不困难,登上高地其实也看不太远。这样的高地最早出现在我眼里时却委实让我惊异了一番。在大平原上疯惯的孩子远不知什么是障碍,所以在蒙蒙的雾里看见一道高高的墙,的确感到新鲜。那是我十岁的时候吧,生病的我从父亲那里第一次知道了薛国和“祸”的故事。我家离这座废城有十来里地,十三岁那年我有幸去废城里的一个村子读书一年,这时候,古城墙才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只是我很容易就把它踩在脚下了,十三岁的孩子觉得自己很高很高。也是在那时,我第一次从老师那里知道孟尝君,知道毛遂,我开始为他们自豪,他们在小孩子里眼里极易成为至尊至上的楷模。但是我不清楚孟尝君和毛遂是何等的英雄,直至后来上中学、大学,我才明白养客的孟尝君无非是战国时一个很会利用人的贵族,他本身并无多少过人之处。要我看,孟尝君不过是利用钱财赚得了一世美名而已,他没有高标可言。至于毛遂的敢于自荐,也不过是一个人的胆量与勇气的爆发,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像这样的人在战国时期或可风光一时,但他的豪勇最终于事无补。如果让我评说,冯谖其实高于田婴(孟尝君),张仪要胜过毛遂。当然,我看的是他们的终极价值。
这块大平原(它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两位名人奇士,从战国至今一直空白。这沉默的土地像冻结的湖面一样,平静得近乎入梦。有学者说,古徐州的中心就是这儿,但是后来它南移了。这样,这座废城就再也难以勃发,最后连“薛城”这个名字也被三十里外的另一市镇取走(原临城改称薛城),薛国故城终于丧失了仅有的一点虚荣。
但它的城墙还存在着,并且被人以全国重点文物的名义保护下来。人们开始以各种理由去挖掘和发挥祖先曾有或未曾有过的事迹,以赚取新的光彩和利益。我知道北辛文化遗址、前掌大墓葬群的珍贵文物(早至商周时期),已被阵列在现代化的博物馆内。我去看过新建的孟尝君陵和毛遂墓。现代气息似乎已吞没了青铜的锈斑和坟茔周围的仿古建筑,只明白门票面值的看门人在我眼里像是一个游戏人间的幽灵。很多人把灵魂抵押出去,再到别处收买更廉价的灵魂。这一块高地已很少有人登临了,大平原上矗立起很多高于城墙的楼房或水塔之类的水泥砖石建筑。
我的这块唯一的高地开始萎缩了吗?我想起十五岁时与文朋诗友组建雪飘飘文学社(这“雪”其实正出于我对薛的怀念)的情景,我在发刊词里那么慷慨地宣告:“我们是雪,五彩缤纷的雪……我们要站在薛国古城上呐喊。也许,这喊声不能激荡长天;也许,这喊声不能让人听见──我们也要用赤诚的心做出卑微的贡献!”如今,那一群激昂少年已经长大。有的远走,有的高升,有的回到田间,有的徘徊在城市的喧嚣里,我则继续带着诗歌和梦想探寻。
古城墙这般沉寂是为了什么?我曾查找过地方志,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我发现这片土地没有留下哪怕一个流血牺牲的名字。如果作为补偿,值得欣慰的是这儿也没有出现过多大的坏人。这一片土地似乎安然地躲过了战争,远离了子弹和血光,人们就这样平安和顺地生活。这儿的人不偏不倚,不优秀也不恶劣。这就是幸福吗?这块平原不是生长传奇和壮烈的地方。吃惯了煎饼喝惯了糊涂的人已习惯了平淡无奇索然寡味,谁曾想过要改变什么?这块离孔孟之乡很近的地方竟然如此固守着夫子圣言不加怀疑,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那么畏畏缩缩唯唯诺诺。人们已不自觉地在血液里渗入了那种苛守陈规安于现状的成分。几年之前又有专家学者把墨子论争给了这块平原:据说墨子故里就在故城东北十多里的地方。于是此地又成墨子圣地,人们又争相捕捉墨圣的光辉,树像建故居忙个不亦乐乎。我不否认这些做法的积极作用,我只是担心,这位小生产劳动者会不会把本来就不甚进步的人们带回那竹杖芒鞋的时代?大平原需要改变的是内在精神,大平原甚至需要危机,或许只有危机才能引发它积蕴了两千多年的潜能。
这块大平原属于谁?古城墙属于谁?在可登楼远眺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需要一块坚实的高地?至少从我的感情上,古城墙永是平原的一条脊梁,只有它才能背负起历史和未来的沉重。两千年前的那场雪融化了,露出的应该是现在。古人筑起的城墙仅剩遗骸,我们怎能不在心灵上为它留下一点位置。
然而谁能理解它的沧桑?慕名而来的人见了它总是失望。它一点也不雄伟,甚至还有些寒酸。我曾颇有兴致地引了远方的朋友登临古城墙,他的轻佻和讪笑简直令我难以容忍,我从心里反感他的浅薄。他也写诗,难怪怎么也写不深刻。从那以后我们渐渐疏远,我们之间隔着这块唯一的高地。我还曾陪黑龙江的一个女孩登临古城墙。她一语未发,只是望着远方,这已足够。这位腿有残疾的朋友也写诗,她的诗具有城墙般的分量。
理解了古城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人生,这是有生命的一块高地你怎能对它无动于衷?它存在于你的生命之前,也将存在于你的生命之后。你不可不看它,它的生命就是人类的延续,它是土地的精魂……
“一片辽阔的旷野中横亘着那连绵不断的高高的古城墙。它的脚下是荒石野蒿,它的身上长满了长长的枯草迎风而舞。站在城墙上迎风而立,满目苍凉。茫茫的宇宙唯有火红的夕阳挂于天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唯有你在此喟叹世之沧桑人之渺小──这是我的想象,是没见到古城墙之前通过你的言语想象的它。虽然没有说过,可在心里早已默许,有机会一定去看看它。可真的看到它时却非我所想,也不由得感到些许失望。它的周围它的上面是青青的麦,它的旁边的小路上是往来的行人,极目四望也是青的麦没叶的树和升烟的村舍。它已和周围融在了一起,安静、平和。唯有那黄土中的枯草在风中昭示它的久远,它曾有过的辉煌。我是站得高才看它很低吗?我真后悔没有站在它脚下,站在那壁立如削的一面去看它可能会是另一种感觉吧?回来之后,也不时地想起它。想象中的东西和它的真实面目总是有差距的。平常的事物一旦渗入了人的感情色彩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你对古城墙的钟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这是女友随我看过古城墙之后写来的信。诚如她所说,对古城墙的确渗入了我的感情色彩,正因如此,普普通通的土墙才在我眼里变得不同寻常。爱情不也如此吗?那次和她同上古城墙,实际是为了诀别。她第一次从她所在的城市来到我所在的乡村中学,我首先想的便是带她去看古城墙。我明白,她看了肯定失望。就像对我的失望一样。正如我预料的,她说,这就是城墙吗?这么矮。我无话可说,对即将消逝的爱情我更是无言以对。
所幸那次告别并未断送我们的爱情,反比以前更牢固了。我从心里感念古城墙,是它,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对方的机会。
后来我又带了她去古城墙以北的一个沙塘,去看那两口古井和碎陶片。古井是人们挖沙时发现的,被泥沙淤死的井被剥除了原来的井壁,仿佛是用模具铸出了两根坚实的柱子。这就是井吗?它沉积了什么?我曾和一朋友在这片沙塘里挖取出一个庞大的瓷器,它造型奇特,让我难以命名。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搬回的途中,有很多人问:挖到了什么?里面有宝贝吗?
我回答他们:怎么没有,很多的泥沙!
我怎能不感到悲哀。我甚至担心有一天那仅剩的古城墙也会踪影全无。据说城后那个村子从前很穷,据说只有把村前的城墙挖光了这个村子才能富起来。现在这个村庄的确把村前的城墙“吃”掉了,这个杀鸡宰鸭的专业村,的确财运亨通了,可我从它腥气弥漫、污水四溢的街巷中走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这个机器时代,民间的衰落尤其让人痛心。人们只顾追逐利益忘了歇息。往往只是一点小利小惠就出卖了这块平原。没有英雄的土地啊,沉默如万古洪荒。聒噪的是人群,他们忽略了这块平原上还有一块高地。
你知道吗?这块高度仅有五六米的高地,已没多少人能爬得上去了。
这唯一的一块高地,像我一样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