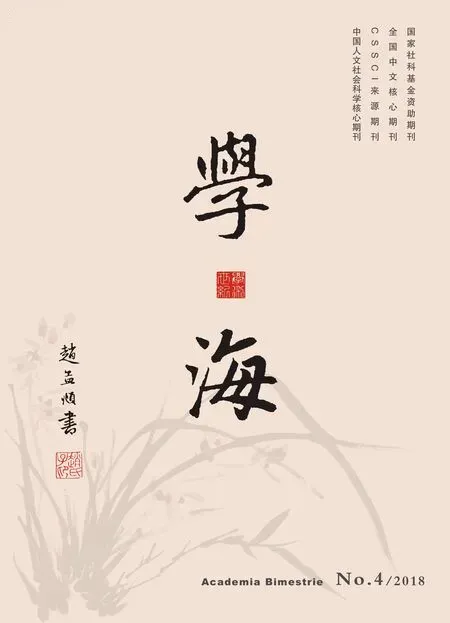长期护理保险家庭化:来自德国的证据*
内容提要 福利供给的责任划分是社会保障领域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老年照料被看作是个体与国家之间非此即彼的责任。随着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如何在国家宏观福利政策支持下刺激家庭责任的互动参与,实现以老年需求为中心的多主体支持体系引发学界关注。镶嵌于德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与政治诉求,兼纳劳动力市场发育背景,本研究采用政策分析法对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过程进行探讨,发现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家庭化偏好,并通过承认家庭内照料服务经济价值的方式将女性从劳动力市场拉回至家庭照料责任体系之中。更重要的,现金给付方式催生规模巨大的非正式照料市场,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补贴家庭照料支出的行为提供有利条件,刺激家庭性别角色的重塑与女性家庭责任概念的更新。因此,本研究提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通过将经济逻辑与市场规则带入传统情感驱动型家庭照料服务,维护家庭内部关系稳定,刺激家庭照料责任的回归与重塑,刻画社会福利政策的家庭化特征。
老年照料是社会保障领域一项经久不衰的议题,国家力量和个体所在家庭对老年照料福利供给的重要性在不同时代、地区得到验证。①②然而,在福利国家诞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老年照料服务的提供一直被看作是非此即彼的责任。在家庭文化和氏族观念盛行的地区,如早期保守主义观念主导的德国以及古、近代中国,老年照料被看作是家庭内部的绝对责任。德国保守主义将传统家庭的解体与家庭照料责任的缺失称之为道德的沦丧,③费孝通也将家庭养老习惯总结为中国家庭代际间的反馈模式,并强调这种反馈背后的社会均衡互惠原则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④在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之外,生产方式论强调养老方式是由经济形态与生产方式共同决定的⑤: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使得家庭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最基本原子,无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生产过程的参与还是生产结果的分配都在家庭内部完成。除了自身生存需要维持所消耗的福利之外,剩余劳动与剩余产品都在家庭内部积累,因此注定家庭养老成为必需。与之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遵从“挤出假说”(Crowding Out Hypothesis)的观点⑥,提供的高水平福利待遇力求实现养老服务的个体化和机构化。此时,国家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供给目的在于让家庭逐渐从养老照料的责任主体中退出,代之以高水平的机构照料。当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老年照料责任会在主体之间进行变动。1840年后,康有为在批判“父为子纲”的传统后提出一个“幼儿抚育、青年教育、老年照料均由公共资源负责”的理想社会,倡导建立“公恤院”来进行老年集体照料。⑦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福利国家水平与范围不断向外扩张。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与其公民之间不断就公民权利与保障问题缔结新契约,⑧老年照料责任逐渐向国家转移。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济滞涨的开始,国家难以独立维持高水平的福利开支,提倡福利的规则制定、资金筹集、服务提供由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福利多元主义兴起。⑨
在传统教会文化的影响下,德国等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特别强调家庭在个体福利获得过程中的贡献,这在老年照料领域里表现更为明显。根据德国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德国社会70%需要照顾的老人住在家里,只有30%的老人生活在疗养院,家庭成为德国社会老年照料服务的实际场所。⑩与此同时,德国社会“家庭主义”文化所塑造出来的“官方政治语义”进一步刺激了公众“老年照料就应该由家庭来提供”的福利诉求,加上公众对疗养院的“污名化”认知,使得德国老人对于家庭照料的需求居高不下,并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市场化正式照料服务的生存空间。为了降低家庭由于长寿风险与健康风险而陷入危机的可能性,维护社会稳定与良性发展,国家作为福利供给方也开始介入老年照料服务,针对性制定包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内的福利政策为个体进行风险保护。因此,国家与家庭成为德国社会老年照料“福利三角”中的支柱性力量。从福利发展视角来看,如何在家庭养老偏好明显的环境下,刺激社会福利政策与家庭主体的互动参与和责任共担,从而建立以老年照料需求为中心的福利供给体系成为重要议题。
家庭观念式微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的提出
长期护理保险在德国的提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西方社会的“家庭”概念正在经历一个消逝的过程。随着资本积累对于劳动力需求的持续走高,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借用诸多国家优惠性福利来降低对家庭的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离婚率的攀升。德国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传统家庭的消逝源自于文化和经济双重催化下带来的传统道德沦丧,并会带来包括老年人无法在家庭中得到优质照料、孩子健康和性格形成风险激增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德国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缩减单亲家庭(很多时候是以母亲为主要劳动力的家庭)的福利支持、给予健全家庭以更多的福利优惠等政策,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单亲家庭的“羞耻性文化”来重建德国社会的家庭价值,将妇女拉回家庭照料的责任体系之中。因此,在传统照料救助难以满足德国社会老年照料服务需求,需要制定新的照料支持政策进行添补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出台有效地回应了“号召家庭责任回归”的政治诉求。
长期护理保险是一项依托健康保险,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政策,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参与社会长期护理保险或是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在缴费一端,个体的职业和社会身份成为唯一标准。配偶参保个体可免费享受长期护理服务,而没有子女的社会成员需缴纳一笔额外的“补偿金”,表现出明显的“家庭主义”倾向。当个体产生照料需求时,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会根据专门机构对申请者进行的能力评估,结果按等级进行福利的给付。一般来说,给付形式分为服务给付和现金给付两种,全部机构养老以及部分居家养老的老年人通过获取正式服务的方式进行养老,绝大多数的居家老年人则选择获取经济补给来对家庭内部成员照料服务进行补贴或者通过非正式照料市场购买服务。
据统计,德国近70%的老年人选择在家获取照料服务,而84%的居家养老者选择以现金给付的形式获取社会长期护理保险的照料福利。不同于传统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国家福利供给会降低家庭内部非正式护理强度、稀释家庭照料责任,德国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典型代表的照料福利体系,希望通过赋予家庭内部正式护理以一定的劳动经济价值来吸纳妇女回归家庭。20世纪90年代以来“去家庭化”明显、个体主义逻辑盛行,德国长期护理保险现金给付的提出,试图借用经济逻辑与市场规则重塑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和连接,进而维护德国社会中家庭关系的稳定,形成以社会福利政策与家庭责任交织而成的老年照料福利体系。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中的“家庭化”偏好
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定旨在增强家庭的粘合度,这一政治意涵在社会个体进行保费缴纳的阶段就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以职业和收入作为主要缴费标准,那些在家承担照料工作的家庭妇女、同居者和被抚养的子女,根据社会法典第5篇第10条,在其配偶(父母)已经参保长期护理保险的基础上无须额外进行缴费,也可以免费享有同等待遇,即与原参保人入保同一保险机构并具有相同的保险期限,同时有权利向保险机构提出给付申请。“有福利、不工作”这种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吸引妇女留在家庭内部进行家庭照料,而非进入劳动力市场。相反,那些无子女的个体在保险资金存在运营风险时成为首当其冲的保费增加者,需要交纳额外的总收入的2.05%以维持参保资格,作为其没有子女参与到长期护理保险资金供给中的提前追偿。虽然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争议,如不孕症等非自愿的无子女家庭所面临的福利排斥等问题,但这种分化的投保标准体现了国家复兴传统家庭信仰的需要:一方面可以平衡参保人因养育子女而产生的缴费不公平现象,并通过对直接相关福利水平的控制将个体引向传统的“家庭结构完整,男女分工明确”的家庭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化的对待策略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非正常家庭”的歧视性文化,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对于家庭化的维护表现在通过给予被照料人直接的现金补贴,将家庭内老年人变为私人雇主,实现家庭照料服务的有偿化。一般来说,大多数接受长期护理保险现金给付、具有购买选择权的个体往往会将这笔钱用于补偿与自己关系较为密切、提供实质照料服务的家庭成员。据调查,德国近50%的非正式照料者享受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在长期护理保险出现之前,传统德国养老服务将家庭内部成员提供的护理服务看作是义务与职责,其不被赋予对应的经济价值。所以当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因为家庭需要,返回家庭进行相关照料服务时,其社会保险以及其他方面的福利会出现相应的断裂,使得妇女本人及其家庭因为照料老人而陷入生活的困境之中。在面对家庭内部的护理需要时,由已经参与工作的个体进行全职照料往往是最后的选择。长期护理保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选择的顺序优先性,也促成了工作妇女回归家庭进行照料服务的可能性。家庭照料的有偿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非正式护理的投入程度和专业程度,也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粘合度和家庭结构的稳定。
为了保证家庭成员照料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提高老年服务供给效率,德国政府在2008年长期护理保险改革行动中专项成立照料小站(Care Station),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使得家庭成员照料技巧得到专业化锻炼。此外,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从2011年开始对家庭照料服务进行监管和年度审核。通过市场化的逻辑,家庭护理服务的有偿化促使家庭成员的照料服务与经济反馈之间进行置换,用市场规则将家庭成员紧密联系起来,刺激独立于正式护理市场之外非正式护理行为的发生与发展,推动实现德国保守主义者所喜闻乐见的养老服务“去机构化”。
配套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基金供给制度,不仅实现家庭非正式照料服务的有偿化,德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辅助性政策强化家庭成员对于老年照料的热情,调动家庭成员成长为老年照料服务潜在人力资源的可能性。对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个体而言,每人每年享有大约四周的照料假期来应对临时性的家庭照料需求。与此同时,社会法典第11篇第44条规定,家庭护理者理应享有同等的年金、职业灾害与失业等社会保险,遵循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护理优先”的原则,因为居家护理而没有正式工作或是减少原有工作量的家庭照料者,由长期护理保险机构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险。此外,家庭长期照料者还有权享有失业保险,自愿投保者在护理工作的24个月内,如果已经缴纳至少12个月的失业保险费,并在护理工作之前已经存在失业保险关系或者享受失业津贴,就可以向联邦保险局申领失业保险。当然,如果个体在家庭照料实施期间仍想续保失业保险,保费须由个人承担,但对于停薪留职的处于护理假期内的家庭照料者,护理保险机构每月为其支付7.06欧元。作为与长期护理保险绑定的社会健康保险,当护理者处于护理病假状态时,依据其配偶的健康保险缴费状态缴纳最低保费或者完全不缴,长期护理保险则根据申请对其进行保费的偿还。一般而言,护理保险公司对于此类家庭照料服务提供者的补充健康保险费为每月130.2欧元,长期护理保险则为16.38欧元。通过为家庭照料者构建一整套优惠的社会保险体系,德国政府在国家整体就业率下降而女性劳动力占比上升的时代背景下有效地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重新吸引回家庭场域之中,以重塑传统家庭文化中的照料互助网络。围绕家庭照料需求而建立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目的绝不在于削减家庭责任,而是借用福利的缓冲作用,增强家庭内部的团结力,强化老年照料中的家庭责任回归,避免由国家提供太多的福利支持而威胁家庭团结的道德原则。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下非正式护理市场发育对家庭福利责任的重构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设计充斥着“家庭主义”取向,坚持“家庭照料优先于机构照料”的方针刺激老年照料责任向家庭转移,试图重塑传统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将女性固定在家庭内部进行照料服务。但随着工业时代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传统家庭照料责任划分认知受到冲击,将老年照料任务自然分配给女性的传统变得不再那么容易接受。如前文所述,大部分居家养老者选择无限制对象的现金给付,在可能强化家庭内部成员照料责任的同时,也同样可能刺激不受管制的非正式护理的市场化行为产生。伴随着劳动力流动速度的加快,私人家庭中提供照料的外来者数量急剧增加,一个规模巨大的、旨在满足家庭护理需要的非正式护理市场产生了。
根据德国社会经济小组的调查,2007年超过11%的德国家庭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地聘用家庭工人来完成家庭日常的照料工作,近145万政府登记为需要接受照顾或帮助以实现自己在家照料服务的老年人之中,名义上是“亲属照料者”,但实际上为全职工作者的人占比高达40%。将家庭内部照护转移给外部市场企业或个人来提供成为越来越多德国家庭的选择。随着劳动力流动的全球化,移民参与德国社会家庭照料服务外包形势加剧。移民妇女代替传统家庭妇女成为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转变被贝迪鸥等称之为“地中海”模式,即养老服务的提供从“家庭照料”转换为“移民的家庭护理”。
大规模移民照料衍生出来的非正式市场及其表现出来的巨大利益潜力使得老年照料服务提供开始逐渐变得专业化,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照料责任起到稀释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内部成员关系与老年人福利使用效用造成冲击。从现实情况出发,由专业移民护理者提供的生理性照料服务比家庭内部成员负责照料更具技巧性,但基于金钱交易而非情感驱动的照料服务有时会容易忽视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需求和情感需求,进而对老年人整体生活满意度与福利提升造成潜在威胁。与此同时,在传统教会观念影响下,选择在家养老者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家庭观念,其潜在逻辑和取向都将照料提供者直接指向家庭内部的成员,而非家庭外的雇佣者。同样单位的照料服务,由家庭内部成员提供可能比家庭外个体提供给老年人带来更高程度的保护性效应,也更加有利于老年心理健康和整体生命质量的改善。因此,当大量家庭照料责任被家庭外部成员所承担时,老年人的效能感和健康状态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损耗,进而影响到家庭内部关系的团结和家庭结构的维系。从这个角度说,长期护理保险所衍生出的非正式照料市场对社会福利政策目标指向的传统“家庭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移民的非正式护理市场”的产生对老年照料领域传统家庭责任的参与造成冲击,但也为家庭,特别是家庭女性个体的福利责任内涵更新创造了契机。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男性和女性被赋予不同的角色分工。男性通过工作为家庭获得经济收入而贡献自己的家庭责任,遵从经济逻辑;女性通过家庭内部直接的照料服务贡献自身的家庭责任,遵从情感逻辑。因此,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产生之前及设计之初,家庭照料责任被放置于家庭内部进行划分,遵从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女性被要求承担更多的直接照料责任。但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女性平权运动的双重背景下运行,现金给付催化出的非正式照料市场使得家庭照料责任被置于一个社会化环境中进行,直接照料责任由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转移至社会非正式市场交易中的买卖关系中,家庭照料责任的参与形式被重构。家庭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贡献家庭照料责任不再仅仅通过直接的照料服务。相反,女性可以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报酬,再将经济收入用于购买照料服务的方式履行家庭责任,进而弱化家庭内部角色分工的性别差异。因此,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对传统家庭直接照料责任的稀释与解构,但从一个历史前进的角度来看,也是家庭角色分工更新,家庭照料责任重构,家庭关系在市场化深化过程中维系的关键,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催生出的非正式照料市场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推动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设计及运行过程进行评估分析发现,德国社会福利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家庭化”倾向,通过与老年个体所在家庭进行互动,推动家庭责任在老年照料领域的参与和内涵更新。在认同“福利三角”研究范式所构建的社会福利支持体系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国家与家庭不仅作为独立的主体参与到老年照料福利的供给,家庭责任在老年照料议题上的参与同样受到社会福利体系设计的间接影响。一方面,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代表的德国老年照料福利体系回应“家庭主义”政治诉求,通过制定对传统家庭的优惠政策鼓励家庭直接承担老年照料责任,并通过现金给付赋予家庭内部照料对应的经济价值,从而刺激照料行为的积极性与连续性。另一方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衍生出的家庭非正式护理市场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经济支持代替直接服务履行老年照料责任提供了可能性,刺激经济思维与市场逻辑下“家庭化”概念的更新。社会福利政策与家庭脱离传统“福利三角”的分割状态,相互交织、影响,共同构成以老年照料需求为中心的福利供给体系。
长期护理保险的现金给付制度将经济价值引入家庭照料服务,使得“福利三角”研究范式下情感驱动型家庭照料向“情感+经济”双驱动转变,强化家庭福利供给热情,维持家庭内部良性关系,凸显社会福利体系的“家庭化”特征。通过赋予家庭照料责任以对应的经济价值让老年照料服务回归家庭场域,对国家、老年人及其所在家庭都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对于国家而言,同等级的照料需求,居家照料的现金给付形式给国家财政和保险基金带来更低的负担。家庭照料在德国护理服务资金总支出中占比仅为机构护理的四分之一,在老龄化趋势加重的时代背景下有效降低了国家财政的老年照料负荷,增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金积累与可持续性运行。对于老年个体而言,现金给付增强其对于老年照料服务的自主选择性,无论是照料形式、照料内容或是照料人员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老年照料资源的配置合理性。对于老年个体所在家庭而言,经济价值在老年照料服务中的渗透使得家庭内成员在面对老年人照料需求时,能够根据自身及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亲自照料或者购买照料服务,使得家庭抵御长寿风险和健康风险的能力更强,家庭结构更加稳定。利用经济手段强化家庭作为社会福利供给的主体力量,不仅彰显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家庭化”特征,对于整个社会福利体系的积极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承接长期护理保险带来的经济逻辑,社会福利政策的“家庭化”通过不同路径进行。对于劳动收入收益低于社会福利政策优惠总额的个体而言,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行直接照料服务成为首选,反之则带来家庭照料责任的内涵更新,由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转移为社会性的职业分工,甚至是民族分工。在就业引力与政策“家庭主义”拉力的博弈之间,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职业位置成为关键性变量。根据安德森对于后工业化就业结构的构建标准,将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职业,如管理型、专业型、科学和技术型的职业界定为“好职业”,反之将那些从事卑微低下或者日常例行工作的职业界定为“差职业”。在“好职业”与“差职业”之间,存在的是由非专业型保健人员、社会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护理助理)和私人服务从业者(如摄影师等)组成的中间群体。随着工业化时代热潮的消退,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以产业工人身份进行劳动的妇女面临较为严峻的下岗危机,成为工业大裁员首当其冲的对象,回归家庭进行照料服务或者进入诸如非正式护理市场在内的后工业化部门成为她们的可行性归宿。因此,在工业化浪潮消退,劳动力市场需求萎缩的时代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用于不同职业身份的女性个体。那些处于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替代性较强的“差职业”的个体,可以选择回归家庭,“家庭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给予他们适当的照料津贴,以增强其风险抵抗能力。与此同时,这些被暂时淘汰的职业女性可以通过进入非正式护理市场就业以获取一定的收入,履行家庭经济职能,维系家庭结构的稳定。那些就职于“好职业”的个体可以通过购买非正式照料服务应对家庭照料需求,通过经济补给的路径履行家庭照料责任。在社会福利政策的作用下,不同阶层与职业的个体选择差异化的家庭福利供给形式,但最终价值均指向家庭团结原则,参与以满足老年人照料需求为中心的福利供给体系的构成。
①Morel, Nathalie: From Subsidiarity to “Free Choice”: Child- and Elder-care Policy Reforms in France, Belgium,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 Vol.41, 2007, pp.618-637.
②Jensen P H: Tensions between ‘consumerism’ in elderly care and the social rights of family carers : a German-Danish comparison,IndianJournalofSocialResearch, Vol.2, 2011, pp.8-22..
③Skolnick A S, Skolnick J H.,Familyintransition,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1989, pp.76-97.
④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⑤洪国栋等:《论家庭养老》,石涛主编:《家庭与老人》,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年,第16-23页。
⑥Oorschot W V, The social capital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the crowding out hypothesis revisited,JournalofEuropeanSocialPolicy, Vol.15, 2005, pp.5-26.
⑦梁启超:《大同书》,陈瑛等主编:《中国伦理思想史》,贵州出版社,1985年,第864页。
⑧米拉什:《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⑨Johnson N. 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 Vol.40,1987, p.150.
⑩Bundesamt S. Neue Daten zur Migration in Deutschland verfügbar,2007.

——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