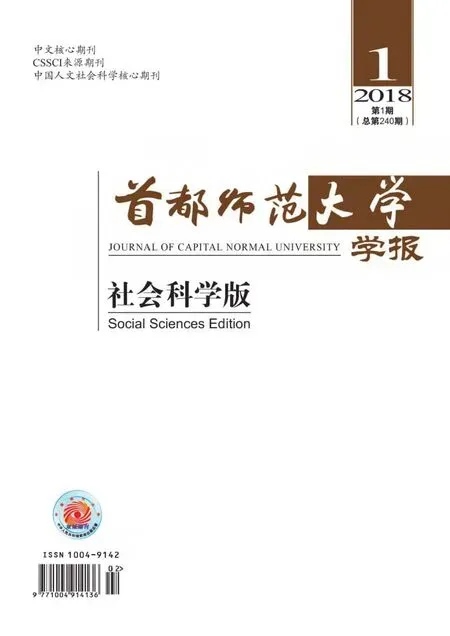扬雄甘泉四赋新解读
龙文玲
扬雄《甘泉》《羽猎》《河东》《长杨》四赋全文载录于《汉书·扬雄传》,历来为研究汉代文学者关注。有考证四赋的作年*拙文《扬雄〈甘泉赋〉作年考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01-108页)对《甘泉赋》作年的相关成果有归类,并作了细致考辨,可参看。;有研究四赋的主题与艺术特征,如王德华先生《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结合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王德华:《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65页。;宋皓琨先生《扬雄四大赋的文本重读》认为扬雄赋的内部构成要素与司马相如赋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它的写实性、时间性和言志艺术三个方面”,并指出其变化原因是扬雄生活在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受到屈原的影响,扬雄本人偏爱史学*宋皓琨:《扬雄四大赋的文本重读》,《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11-13页。;有讨论扬雄赋模拟与创新及文学成就的问题,古人多以扬雄赋模拟司马相如,如祝尧《古赋辩体》卷四所录《甘泉赋》题下注云:“全是仿司马长卿,真所谓同工异曲者。”*(元)祝尧:《古赋辩体》卷四,(清)永瑢、纪昀等编:《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13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61页。下同。当代学者多肯定扬雄模仿中有创新,如张震泽先生《扬雄生平、作品评价及其他有关问题》认为扬雄的模仿是“要超越前人,压倒古典”,并从蕴藉风格、大赋体制突破、练字遣词三方面,肯定了四赋的创新*张震泽:《扬雄生平、作品评价及其他有关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95页。;蓝旭先生《论扬雄赋》认为“扬雄大赋重视讽谏,并开辟了新的讽谏手法”*蓝旭:《论扬雄赋》,《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102页。;冯树勋先生《是摹拟还是创新——范式冲突内的扬雄》认为“扬雄并非全然同意司马相如的作品为美文的最高典范”*冯树勋:《是摹拟还是创新——范式冲突内的扬雄》,《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30期(2013年7月),第41页。。这些现有研究对理解扬雄四赋颇有帮助,但限于各自研究的角度和目的,均未将四赋放到西汉后期社会危机、社会批判思潮涌起的时代背景下,细致讨论其创作动机、讽谏艺术的表达方式及其典范意义。有鉴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对扬雄四赋作重新解读,期待对其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危机之下社会批判思潮的涌起
笔者《扬雄〈甘泉赋〉作年考辨》认为,扬雄《甘泉赋》作于汉成帝永始四年(前13),他本人因此而病一年。之后,至迟到元延二年(前11)冬这段时间里,完成了《河东》《羽猎》《长杨》三赋。其时,正值成帝“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东汉)班固:《汉书》卷十《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0页。下同。之际,西汉帝国已由宣帝中兴期进入到风雨飘摇的衰亡期。
汉成帝时外家擅朝,从公元前33年成帝即位以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开始。成帝母王政君有兄弟八人:王凤、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其中王凤、王崇与王政君同母。成帝即位后,除王曼早死,其余七位舅舅均封侯。期间于河平二年(前27)同日封王谭、商、立、根、逢时为列侯,世称“五侯”。并且,“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东汉) 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4018页。。外戚势力如此之盛,西汉建朝以来,未曾有过,无怪乎班固感慨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东汉)班固:《汉书》卷十《成帝纪赞》,第330页。外戚势盛,必会极力维护既得利益,排斥迫害异己。如刚直敢言的京兆尹王章被王凤构陷致死;元帝冯昭仪之弟、被百姓称颂“聪明贤知惠吏民”*(东汉) 班固:《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第3305页。的冯野王被压抑乃至免归;“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66页。的刘向被压抑,成帝欲任其为九卿而不得。更有甚者,汉成帝欲任命自己赏识的刘歆为中常侍,不仅遭到王凤直接阻挠,而且还被随侍左右的臣子阻止。*事见(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4018-4019页。足见王氏执国命之下,汉成帝连官吏任免的自主权都没有。在皇权走向式微的同时,王氏势力日渐强盛。《汉书·元后传》记载,王章死后,“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又以侍中太仆音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4023页。。在王政君庇护和汉成帝纵容下,王氏及其爪牙还把持着地方的重要职位,刘氏政权已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成帝耽于女色,导致赵氏乱内,进一步加重了这时期的社会政治危机。鸿嘉年前,成帝后宫主要由许皇后、班婕妤主掌,鸿嘉元年之后(前20),情况发生改变。《汉书·外戚传》载:
自鸿嘉后,上稍隆于内宠。倢伃进侍者李平,平得幸,立为倢伃。上曰:“始卫皇后亦从微起。”乃赐平姓曰卫,所谓卫倢伃也。其后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越礼制,浸盛于前。班倢伃及许皇后皆失宠,稀复进见。鸿嘉三年,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坐废。……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倢伃,贵倾后宫。*(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第3984、3988页。
据此,进入鸿嘉元年,成帝开始耽于女色。先有班婕妤所进的李平,后有赵飞燕与赵合德姐妹。鸿嘉三年(前18),在赵飞燕诬告下,许皇后被废,绥和元年(前8)被赐死;班婕妤虽免于难,但恐久见危,自请到长信宫供养太后王政君,方得以善终。赵氏姐妹入宫最多三年,就导致原本受宠的许皇后、班婕妤由失宠到一个被废、一个退处太后宫中,足见其极擅争宠夺位。据《汉书》中《成帝纪》与《外戚传下》载,绥和二年(前7),成帝暴崩,时年四十六岁,赵合德无法解释成帝死因而自杀。汉哀帝即位,司隶解光奏赵合德逼迫汉成帝残杀许美人和曹宫所生孩子之事,并引故掖庭令吾丘遵揭露赵合德为专宠,“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者无数”*(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第3995页。。由解光所奏,足见赵合德固宠手段之残忍,亦足见汉成帝因沉迷女色而荒唐冷酷。值得注意的是,鸿嘉元年之前,许皇后和班婕妤曾有生育,但全都夭折;鸿嘉元年之后,赵氏姐妹无子,后宫虽有生育却被残杀。成帝无子,对西汉国祚的延续、政局的稳定显然不利。
伴随王氏持国命、赵氏乱内的,是以汉成帝、王氏外戚为首的统治阶级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汉成帝即位前就“幸酒,乐燕乐”*(东汉) 班固:《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01页。,即位后依仗外无边患、国家承平,挥霍无度。其挥霍巨大者,一是生活奢靡,其中以优宠赵合德为甚;二是耗费巨大财富,营建陵墓。
《汉书·外戚传下》记载赵合德所居昭阳舍装饰的奢华:
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第3989页。
昭阳舍装饰如此富丽堂皇,不难想见住在里面的人生活是何等奢靡了。
成帝营建陵墓,耗费更是巨大。他先于建始二年(前31)开始下令营建延陵(又称“初陵”),鸿嘉二年(前19)微行期间看中霸陵曲亭南面之地,即令停建延陵,改作昌陵。永始元年(前16)又下令停建昌陵,还建延陵。《汉书·陈汤传》载有司就营建昌陵数年不成而批评道:
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徧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东汉) 班固:《汉书》卷七十《陈汤传》,第3024页。
昌陵还没建成,就因工程量巨大,导致天下虚耗,百姓苦之。尽管成帝接受有司批评还建延陵,但营建规模依然泰奢。汉成帝在营建其陵墓一事上反复折腾,奢侈过度,足见其视耗费国家人力物力形同儿戏。
成帝奢侈挥霍如此,王氏外戚亦不逊色。《汉书·元后传》载:
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其奢僭如此。*(东汉) 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4023-4024页。
以五侯为代表的王氏外戚依仗皇权,大治第室,姬妾成群,歌舞享乐,其奢侈挥霍,令人瞠目。百姓所作《五侯歌》,就真实反映了五侯奢侈僭越的情景。*拙文《西汉社会转型与元平时期乐府演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85页)对《五侯歌》揭露五侯的越礼逾制有详论,可参看。
统治者争于奢侈,必然会败坏社会风气,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社会危机。《汉书·食货志上》就此总论云:“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永始二年(前15),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并记载师丹给汉哀帝的建言,其中云:“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42页。师丹所言之“今”,其实就包括成帝时期情况。一方面是统治者奢靡享乐,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部分的豪富吏民之家;另一方面是百姓贫弱愈困,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梁国、平原郡遭连年水灾,竟至人相食,景象凄惨,可谓触目惊心。而永始二年,正是扬雄作《甘泉赋》的前两年。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百姓贫弱无法自保,必然会揭竿而起。据《汉书·成帝纪》载,鸿嘉、永始年间,就于鸿嘉三年四月发生了广汉郡郑躬领导的起义,至鸿嘉四年冬方被镇压;永始三年十一月、十二月又先后发生陈留郡尉氏县樊并和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人的造反。这些平民起义,更加重了西汉帝国的社会政治危机。面对危机,士人们纷纷著书撰文批判、讽谏,推助了西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涌起。
有抨击王氏外戚专权者。刘向就经常向成帝陈说母党专政、权在外家的危害性,如其阳朔二年(前23)《极谏用外戚封事》云:“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安全之也”。*(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60、1961页。指出王氏外戚僭贵前所未有,力劝成帝收回被分割的皇权,以稳定刘氏政权。出言恳切,忧世之情溢于言表。
有批评成帝沉迷女色、奢靡享乐者。这方面批评之声比较复杂,其中掺杂着王、许、赵三家外戚的斗争。当时部分士人多附王氏而对许、赵进行批评。谷永、杜钦即属此类。谷永于建始三年(前30)《举方正对策》批评成帝惑于许氏,建议成帝宜“损燕私之闲以劳天下,放去淫溺之乐,罢归倡优之笑,绝却不享之义,慎节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礼而动,躬亲政事,致行无倦,安服若性”。力劝成帝不可贪图后宫燕私,并指出帝王之夫妻关系与王事纲纪、国家安危相关:“夫妻之际,王事纲纪,安危之机,圣王所致慎也。”*(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第3445-3446页。永始二年又就成帝宠赵氏作《星陨对》:“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沈湎于酒。”*(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第3459页。尖锐指出沉迷后宫将有亡国之祸。刘辅亦因成帝欲立赵飞燕为后而上书谏止:“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七《刘辅传》,第3252页。言辞激切,无所顾忌。刘向则因“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作《列女传》《新序》《说苑》,以此作为谏书,希望能“助观览,补遗阙”*(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57-1958页。。
有批评汉成帝耗费巨资营建陵墓。这以刘向《谏营延陵疏》为代表。此疏不独历数汉成帝营建昌陵劳民伤财,使“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招致民怨,而且还在开篇借《周易·系辞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指出“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56、1950页。提醒成帝要居安思危,并深刻指出天命并非永远眷顾一家一姓,若不改变当前所为,必将招致亡国之祸。晚清学者吴汝纶评此文:“有危亡之惧,发兴无端,不专为起陵立论,故沸郁湛至,悲愤苍凉。”*高步瀛:《两汉文举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7页。可谓深得其意。
有揭露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与危机。如薛宣于建始元年(前32)作《上疏言吏多苛政》,指出地方官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第3386页。,是造成阴阳不调的重要原因。谷永还批判成帝时“饮酒无节,君臣不别”的政治乱象,并指出:“赋敛滋重,不顾黎民,百姓虚竭,则日蚀,将有溃叛之变。”*(宋)范晔:《后汉书》卷十八《五行六》刘昭注补,第3369、3370页。
综观成帝时期政论文不难发现,武、宣之际的颂声已被批判之声替代。这些政论文往往直切时弊,针对性强,显现出士大夫浓厚的匡救时弊意识。尽管刘向、谷永常借自然灾异批判时政,但他们作品的批判力量并不因使用譬喻而削弱。这些讽谏批判的政论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批判思潮。扬雄甘泉四赋,就是这股社会批判思潮涌起之际产生的优秀作品。
二、甘泉四赋的补衮意识及其文学实现
重新解读扬雄四赋,除需关注其产生的历史大背景之外,还需把握其具体的创作背景与创作动机。根据扬雄自序写成的《汉书·扬雄传》对此有较详的记载。
据《汉书·扬雄传》载,扬雄甘泉四赋都是上奏给汉成帝的作品,这就需要先了解扬雄进入朝廷的具体时间。班固于《汉书·扬雄传赞》补充扬雄入仕经历云:“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第3583页。说明扬雄入仕前先被时为大司马的王音赏识,王音以其为门下史,并向成帝推荐扬雄为待诏,于是,扬雄通过作赋,进入仕途。但《扬雄传赞》并未明确扬雄入仕的具体时间。而这一时间,《扬雄传》中有透露:“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22页。据《汉书》之《成帝纪》与《郊祀志》记载,成帝即位之后,就听从匡衡建议,将汉武帝时期修建的甘泉泰畤与汾阴后土祠坛徙至长安,定南北郊。到永始三年(前14)十月,才因没有子嗣,请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畤与汾阴后土祠坛,决定由成帝“复亲郊礼如前”*(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第1259页。。而成帝首次郊祀甘泉泰畤与汾阴后土,分别在永始四年正月和三月。据此,扬雄被荐举到成帝朝中,当在永始三年十月至永始四年正月之间。
在此还需指出,《汉书·扬雄传赞》记载向成帝举荐扬雄的是王音,但据《汉书·成帝纪》,王音卒于永始二年正月,如此,举荐扬雄的不可能是王音。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宋祁《通鉴考异》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诏承明之庭,奏《甘泉赋》,其十二月,奏《羽猎赋》,事在元延元年,时王音卒已久,盖王根也。”*(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十七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5页。下同。然而,考《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永始二年“正月乙巳,大司马音薨。二月丁酉,特进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永始四年“十一月庚申,大司马商赐金,安车驷马免”*(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835、837页。。举荐扬雄者,并非是宋祁所说的王根,而可能是王商。王先谦还认为《扬雄传赞》所说的“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之“四”当为“三”,理由是:扬雄生于宣帝甘露元年(前53),王音于阳朔三年拜大司马车骑将军,时扬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王音薨,扬雄年三十九,与“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的记载不合。“古四字作亖,传写时由三字误加一画,应正作‘三十余’始合。”*(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十七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但王氏所论,并不符合《扬雄传》所说的“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的时间,故笔者不予采纳。
无论扬雄如何淡泊自守,获得王氏外戚的赏识和举荐的经历,多少会使其心怀感激,故在其赋和奏议文中看不到批评王氏外戚专权的内容。
《汉书·扬雄传》载录甘泉四赋的赋文之前,均有一段叙述文字说明扬雄四赋创作的背景与动机,《文选》收录《甘泉》《羽猎》《长杨》三赋时,就将这些叙述文字作为赋序一并收入。*《文选·羽猎赋序》所收文字,与《汉书·扬雄传》略有差异:“其十二月”,《文选》作“孝成帝时”;“雄从”,《文选》无;“南至宜春”,《文选》作“东南至宜春”;“田车”,《文选》作“甲车”。明代郑朴辑《扬子云集》于《扬子云集序》中,节录了《甘泉》《羽猎》二赋的背景介绍文字,而将《河东》《长杨》二赋的背景介绍文字全部录入。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卷八《扬雄集》录扬雄《自序传》,则将《扬雄传》中的背景介绍文字全部录入。说明在前人眼里,往往将《汉书·扬雄传》记载的甘泉四赋的创作背景与动机的四段文字视为赋的序言。这些序言,提供了以下信息:
《甘泉赋》是扬雄随从汉成帝赴甘泉宫祭祀太一神返回之后写作的。扬雄有感于甘泉宫建筑过于奢侈,而当时赵昭仪专宠并随同成帝到甘泉祭祀,因此“奏《甘泉赋》以风”。
《河东赋》是扬雄随从成帝赴河东祭祀汾阴后土返回后创作。扬雄此番随同成帝巡祭后土并游览唐虞故地,看到成帝对唐虞之风的倾慕,故而“上《河东赋》以劝”。
《羽猎赋》是扬雄随从成帝到上林苑校猎后所作。扬雄有感于上林苑规模宏大,各种建筑精妙富丽,“游观侈靡,穷妙极丽”,故“因《校猎赋》以风”,希望成帝能避免泉台之讥。“泉台”,据颜师古引服虔注曰:“鲁庄公筑泉台,非礼也,至文公毁之,《公羊》讥云:‘先祖为之而毁之,勿居而已。’今扬雄以宫观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当以泉台折中也。”用“泉台”之典,有谏成帝羽猎当合于礼制的意味。
《长杨赋》是元延二年冬,汉成帝为炫耀汉帝国多禽兽,命右扶风征发百姓捕捉各种禽兽运送到长杨射熊馆,令胡人手搏自取,以此取乐。为此,被征发捕猎的农民不能按农时收获粮食。扬雄对这种严重伤农之举深有感触,返回之后“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57页。。
由四赋序言不难发现,四赋均抓住当时重要的时事政治事件进行书写,因以讽谏,有的放矢,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典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期待社会变革、延续国运的普遍心理。这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叙事的想象性质显然不同。与刘向以《列女传》《新序》《说苑》为谏书性质一样,扬雄是以赋为谏书,期望成帝能通过阅读这些赋有所感悟,以裨补时政。《诗经·大雅·烝民》有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在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中,君主施政有过失,臣子往往想到的就是如仲山甫那样,想办法通过劝谏方式裨补君主过失,从而形成浓厚的补衮意识。西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涌起,其实就是这种补衮意识的体现。扬雄四赋序言屡屡重申其创作动机就是“以风”、“以劝”,足见其作赋有着自觉而强烈的补衮意识。
然而,对扬雄甘泉四赋的讽谏问题,学术界大多学者认为,四赋序言表达了讽谏的创作动机,但赋文却没能有效表达讽谏内容,因而出现了赋的内容与创作目的的背离,仍不脱司马相如“劝百讽一”的窠臼。其中以清代学者黄承吉批评尤激烈。黄氏自称其《梦陔堂文说十一篇》专为批评扬雄赋与赋论而作,其中云:“追序《甘泉赋》,自谓风戒,其实《甘泉赋》通篇专以昆仑谀讼。献媚赵昭仪,则比之西王母。”*(清)黄承吉:《梦陔堂文说十一篇·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5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对这类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通过对四赋序言与文本重新解读,笔者发现,四赋序言继承了先秦叙事文直陈其事的记事笔法,因此表达比较直截;而赋正文则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比兴传统,采用的是主文谲谏的文学表达方式。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开篇所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诠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赋这一文体最大的特征就是在铺采摛文中叙事状物,委婉抒写内心情志。而甘泉四赋的赋文正是将作者“以风”“以劝”的内心情志通过“铺采摛文,体物”的文学手段表达出来的。
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主要采用空间移位的书写方式不同,《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一律采用时间先后顺序,完整呈现了汉成帝祭祀甘泉太一、河东后土、赴上林苑畋猎的全过程。《长杨赋》则沿承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问难模式,按时间顺序,先敷陈汉高祖、文帝、武帝的历史功绩,最后对成帝振师校猎长杨之事发表意见。四赋均在依时间顺序铺写中,有选择性地铺陈、体物,不时将讽劝之志融入其中。在讽谏艺术表达上,主要采用了借刺古以刺今、借美古以刺今、借美今以讽今、借第三者之口直接刺今等四种方式来表达其补衮意识。
借刺古以刺今的讽谏艺术表达方式,在《甘泉》《河东》《长杨》赋中均有运用。
如《甘泉赋》描写祭祀队伍行进途中,先是“乃望通天之绎绎”,接着见到的是“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靡虖延属”。据《汉书·武帝纪》载,通天台为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建造。《史记·封禅书》还记载了此台建造之因,是方士公孙卿向渴望升仙延寿的汉武帝胡诌仙人好楼居,于是武帝下令“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人之属”。“通天茎台”,司马贞《索隐》案云:“《汉书》并无‘茎’字,疑衍也。”*(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00页。下同。是。扬雄写到通天台,其中就隐含着对汉武帝将求仙欲望融入郊祀活动的荒唐举措的讥讽。而离宫、封峦、石关,应劭注曰:“言秦离宫三百,武帝复往往修治之。”颜师古又云:“,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处则有之。……封峦、石关皆宫名也。”*(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26页。结合此赋正文后的说明:“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棃、师得……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34-3535页。可知赋文描写途中随处可见的离宫,并列举封峦、石关两座宫殿,意在点面结合,引领读者回顾甘泉离宫建造的历史,以秦二世而亡为警醒,而以汉武帝泰奢导致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为戒惧。继而,浓墨重彩铺写封峦、石关宫殿的高峻雄伟和富丽堂皇,其中云:“翠玉树之青葱兮,壁马犀之瞵。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壁,《文选》作“璧”。吕向注曰:“谓武帝植玉树于此宫,以碧玉为叶。青葱,玉树也。又作碧马、犀牛等为饰。”*(梁)萧统编、五臣注:《文选》卷四,台湾“中央”图书馆影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陈八郎宅刻本,第2页。王观国《学林》卷七据上下文义,认为当依《文选》作“璧”*(宋)王观国:《学林》卷七《甘泉赋》:“凡此赋句皆以下句释上句,则‘璧马犀’为‘璧玉’之‘璧’,其上下文句通矣。其曰‘据軨轩而周流兮,忽坱圠而亡垠’,然后言玉木金人者,盖谓依栏槛而四顾,见广大而无际畔,但见庭中玉木之青葱,金人之岩岩耳。玉木植于殿庭,金人捧露盘,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见殿庭中物,不应反言殿壁也。”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7页。。殿中玉树青葱,并饰以碧玉马和犀牛角,何等奢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赵合德所居的昭阳舍。金人承钟虡,则暗用秦始皇故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长杨赋》中翰林主人批判秦残害百姓,使天命转而顾汉,也是借过秦以讽今。在成帝之前,士人们讽谏时政就往往借过秦、过武以谏今,因此,这样的借刺古以刺今的讽谏艺术表达,对汉成帝这样的读者而言,并不隐晦。*(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借子虚、乌有之口批评齐、楚二王畋猎为失礼僭越,以批判汉初诸侯王僭礼行为,汉武帝读之大悦,即为明证。参见齐清仙:《论司马相如入梁路径对子虚赋的影响》,《学术论坛》,2016年,第1期,第125-130页。《河东赋》写成帝游行思慕唐虞之风时,插入了“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与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几句,将目光投向项羽、夏桀的失败之处垓下和南巢。同样是这片土地,尧、舜、禹、周文王声名远播,而项羽、夏桀却遭到败亡。这样的借刺古以刺今,其意亦甚明。
借美古以刺今的讽谏艺术,主要运用于《河东赋》《长杨赋》中。
《河东赋》赋文总共三段,就用了一整段敷陈成帝祭祀后土神之后游经的尧舜禹和殷周旧迹。其中赞美大禹治河功绩:“洒沈菑于豁渎兮,播九河于东濒。”*(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38页。成帝时期,水患频发,据前文所引《汉书·食货志》记载:成帝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连年伤水灾,乃至人相食,而如此惨象就发生在《河东赋》创作的前三四年间!扬雄在此颂大禹治河之功,其中蕴含的现实感慨,不难品味。赋中赞美虞舜亲耕历山,倾慕唐尧崇高、周文王大宁,这是借美古圣王勤政修德来劝成帝当勉力进取,以免遭项羽、夏桀那样的败亡之祸。《长杨赋》借翰林主人之口,赞美汉高祖历经艰苦奋战创立帝业之功绩、汉文帝躬服节俭稳固汉家基业之文德、汉武帝打击匈奴解除汉帝国边患之武功,其实是借颂美这几位建立卓著功绩的帝王以告诫成帝帝业来之不易,当力戒奢华,建立功业,而不是伤农扰民、荒淫田猎以奉无用之事。这些借美古以讽今的艺术表达,体现了扬雄对成帝振兴国运寄予的幻想。
借美今以讽今,在《甘泉》《羽猎》《长杨》三赋中多有运用。
如《甘泉赋》写汉成帝在祭祀太一神仪式举行之前穆然静思,“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31页。,体悟到好色败德,从而却女色而亲道德。而现实中的成帝却是领着赵合德共赴甘泉祭祀。因此,这里的“屏玉女而却虙妃”显然是对成帝好色、赵氏乱内的反讽*(东汉)班固:《汉书·扬雄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第3535页。,而非黄承吉讲的“谀讼”“献媚”。《羽猎赋》铺陈猎捕水族一段结尾云:“鞭洛水之虙妃,饷屈原与彭胥。”*(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51页。颂扬成帝远女色,近屈原、彭咸、伍子胥等贤臣,其用意与《甘泉赋》讽成帝好色乃异曲同工。《长杨赋》最后一段夸赞成帝能够“平不肆险,安不忘危”,在丰年时“振师五莋,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遵循古代圣王畋猎的三驱之义,爱惜民力,“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第3563-3564页。。这些夸赞,正与现实中成帝的所作所为相反。最后一句“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表面指责客不理解成帝校猎长杨的用意,实则是与前面的反讽一起,对成帝耗民力、夺农时而向来朝的少数民族首领炫耀汉多禽兽给予了委婉批评。《羽猎赋》则通篇寓讽劝于颂美。此赋开头即云:
或称戏农,岂或帝王之弥文哉?论者云否,各亦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则泰山之封,乌得七十而有二仪?是以创业垂统者俱不见其爽,遐迩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颂曰: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虖侔訾,贵正与天虖比崇。齐桓曾不足使扶毂,楚严未足以为骖乘;狭三王之阸薜,峤高举而大兴;历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闳;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42页。
颜师古就此段开头二句注云:“设或人云,言俭质者皆举伏戏、神农为之首,是则岂谓后代帝王弥加文饰乎?故论者答之于下也。论者,雄自谓也。”*(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3543页。在此,扬雄借批评有人动则称道伏羲、神农氏节俭尚质的观点,肯定帝王因时制宜,由此赞颂成帝富贵与天齐同,可以使齐桓公、楚庄王这些历史上的有为君主难以攀附;其文质政教可以与三王、五帝并肩。赋结尾又夸赞成帝谦让,开放禁苑,散公家之财,与民同乐,其功业“加劳三皇,勖勤五帝”,这样的虚美夸赞,有劝勉之意,更有对成帝羽猎过于奢泰、不恤民力物力的讥讽。可以说,这几篇赋文所赞美的,大多正是现实中所没有的,其讽谏意味均不言而喻。

由以上分析可知,借刺古以刺今、借美古以刺今、借美今以讽今、借第三者之口直接刺今,这四种讽谏艺术表达方式在甘泉四赋中得到了综合运用与互相补充,从而使扬雄的补衮意识得到了充分展现。因此,就赋文本身而言,四赋不但没有与扬雄的创作动机产生背离,反而是在尊重赋体铺采摛文的艺术特征基础上,将讽谏意图融入全篇,从而与枚乘、司马相如开启的劝百讽一的大赋传统拉开了距离,实践了扬雄“以风”、“以劝”的创作动机。
三、甘泉四赋讽谏艺术表达的典范意义
客观上说,扬雄甘泉四赋的讽谏艺术表达方式除第四种讽谏意义比较明朗之外,其他三种均属委婉的譬喻,需要读者了解相关历史掌故方能心领神会。这恐怕也是四赋正文被一些学者认为缺乏讽谏意味、与赋序给出的创作动机产生背离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一位刚来到朝廷的待诏臣,扬雄在随行途中切身体会到汉成帝的奢靡荒淫和赵氏乱内的危害,利用散体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南朝)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第21页。的功能,通过献赋,表达讽谏劝勉的补衮之志,对他来说乃是不得已也是最佳的选择。扬雄创作的这一情况,对当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士子而言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毛诗序》就对中国古代等级社会制度下的臣子讽谏艺术有总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郑玄笺云:“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孔颖达疏:“臣下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义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义风动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义以风喻箴刺君上。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战国)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页。结合郑玄笺和孔颖达疏不难发现:“主文谲谏”在政治家那里,是谏君的必要手段;在诗人那里,是谏君的重要表达方式。在“天子实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都听命于他”*[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的社会里,作为人臣的诗人只能使用譬喻,以风喻箴刺君上,要咏歌依违不直谏,如此,方能在不直言君之过失,不逆龙鳞的前提下,保全生命,使君主读后自我警戒。在汉代文人眼里,赋源出于《诗》,《汉书·艺文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6页。。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一,第21页。均为这一观念的体现。因此,汉代赋论者无论肯定还是否定赋这种文体,都认为赋应当承担起《诗》的讽喻功能。扬雄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汉书·扬雄传》记载了他的赋观念:“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第3575页。既是认同赋源于《诗》,赋应该具备讽喻的功能,那么,如何讽喻,运用什么样的讽谏艺术表达方式,就需要特别重视。
《汉书·扬雄传》中,扬雄对司马相如赋的讽劝艺术给出了批评:“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第3575页。《汉书·司马相如传》也记载了扬雄的类似观点:“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下》,第2609页。在扬雄看来,赋如果过分追求铺陈上的推类而言、语言上的丽靡之辞、规模上的闳侈巨衍,将讽谏之志放到结尾表达,就会导致喧宾夺主,劝百讽一,淹没掉作者的讽谏意图。想要在赋的讽谏艺术表达上突围,就必须改变这种曲终奏雅的表达方式。扬雄《法言·吾子》还表达了他对赋优劣的看法:“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所谓“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宋咸注云:“诗人之赋,犹二雅之作”,“辞人之赋,犹景唐之流”。所谓“淫”,李轨注云:“即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东晋)李轨、(唐)柳宗元注,(北宋)宋咸、吴秘、司马光重添注:《扬子法言》卷二《吾子》,(清)永瑢、纪昀等编:《四库全书》,第6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0-281页。由此可见,扬雄对继承《诗经》二雅艺术的诗人之赋给予了肯定,而对景差、宋玉、枚乘之类的辞人之赋给予了批评。在扬雄看来,辞人之赋均因追求丽靡辞藻和宏大规模而“不免于劝”,达不到应有的讽谏效果。
基于对前人及自己作赋的反思,扬雄有意识地追求赋的讽谏意义的表达,使其赋作跻身于“丽以则”的“诗人之赋”的行列。甘泉四赋的借刺古以刺今、借美古以刺今、借美今以讽今、借第三者之口直接刺今等四种讽谏艺术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正是扬雄对司马相如以来“劝百讽一”的赋困境的努力突围,同时也是他将《诗经》主文谲谏艺术运用到赋体创作中的积极实践。扬雄之后,汉大赋的现实针对性和讽谏意味明显增强,如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就讽谏艺术表达方式而论,大体不出扬雄四赋的范围。故此,甘泉四赋在当时和后世赋坛的典范意义,值得重视。
应该说,扬雄本人对甘泉四赋的讽谏艺术表达是满意的,由其将这四赋完整收入自序中,就可以见出他的这种自信。《汉书·扬雄传》将这四赋完整保留下来,亦可以见出班固时代人们对这四赋价值的肯定。萧统编《文选》,载录《甘泉》《羽猎》《长杨》三赋,并在总全书之旨的《文选序》中说:“《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页。在萧统看来,扬雄与荀子、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的赋作均与《诗经》六义有紧密联系,而扬雄《长杨赋》和《羽猎赋》乃是戒统治者畋猎赋作的典范。刘勰《文心雕龙》多处评价扬雄四赋,如《比兴》云:“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诠赋》,第602页。其中“纤”,范文澜注:“当作织。”肯定扬雄赋具有《诗》之比兴特征。《诠赋》指出扬雄《甘泉赋》具有“构深玮之风”的艺术特点同时,还将扬雄与荀子、宋玉、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王延寿放在一起论道:“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诠赋》,第135页。足见刘勰对扬雄赋的高度肯定。由《文选》之收录、《文选序》和《文心雕龙》之评,足见至南朝时期,甘泉四赋已经历时间的磨洗,成为人们公认的文学经典。
就甘泉四赋讽谏艺术表达的现实效果看,尽管现实中的汉成帝并未因读了这四篇赋而改变其政治作为,但据《汉书·扬雄传》载,扬雄上《甘泉赋》后,“成帝异之”。《扬雄传赞》又云:“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说明这四篇赋至少获得了汉成帝这位特殊读者的审美欣赏。其实,赋是否有效表达讽谏之志,与读者是否根据赋的讽谏之志而改变作为,是两码事。事实上,汉成帝不独未因扬雄赋而改变现状,而且对刘向、谷永等臣子的切言直谏也置若罔闻。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说刘向、谷永等人的奏议文没有表达讽谏之志。因此,甘泉四赋虽然有效表达了扬雄的讽谏意图,但起不到他期待的讽谏效果,这并不能说明扬雄赋讽谏艺术的失败,反而昭示着在西汉末社会政治危机之下,由于皇帝官僚政治制度的天然弊端无法补救,这时期士大夫补衮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西汉国运已经无法挽回。
ANewInterpretationofYangXiong’sFourPoemsonGanquan
LONG Wen-ling
Abstract:This essay examines Yang Xiong’s Four Poems on Ganquan by placing them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discovers that they were some of the finest works born out of a climate of social critique in late Western Han. All four poems targeted at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s taking place at the time, a highly critical and allegorical reminder of the literati’s social expectation for social change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national fortune continue. To that end, Yang Xiong employed four types of allegories, namely utilizing the ugly past, the good past, the good present, and voice of the third person, to criticize the present. Exquisite as they were, the poems, however, failed to achieve their intended effects of admonition, a chilling reminder that the literati’s efforts were doomed to failure and that the national fortune was irreversible.
Keywords:Yang Xiong; Four Poems on Ganquan; art of allegory; 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