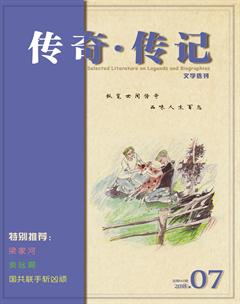母亲与崔岑
刘向阳
秋色向晚,夜幕低垂。母亲撂下碗筷,饭还嚼在嘴里,人已下了屋场,穿过几条田埂,爬上另一个山头,到了崔岑家。
帮别个做事,去得早,回得晏,费神费力,耽擱睡眠,蠢得死!父亲望着黑黢黢的远山,摇头叹息。
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我埋头写作业,写困了就去睡了。半夜起来上厕所,仍不见母亲回来。清早,桌上多了三五片“华乐香”饼干。
宝生,带去学校吃。母亲双眼通红,边说边搅动灶台上热腾腾的猪潲。
崔岑喊你挑茶壳子,忙活到半夜,几块饼干就打发了?这崔岑,也太抠门了!父亲往灶膛里添柴火,一脸的不悦。
秋闲夜无事,邻里乡亲的,帮着做点手边上的事,我乐意!母亲瞪了父亲一眼,父亲便不再吱声了。
在我的印象中,崔岑容貌姣好,轻言细语,逢人露笑,给人一种亲切感。她是水府庙对岸的渔家姑娘,家庭条件不错,找对象千挑万选,一眨眼成了大龄剩女。常宁去相亲,崔岑看中他有木匠手艺,就嫁给了他。
画岭出产茶油,油茶树漫山遍野。常宁在外做工,崔岑便请人把茶子采摘下山,晒得十天半月,茶子咧开嘴笑成花,于漫长秋夜,叫上几个妇女帮忙把茶子与壳分拣开来。她家堂屋摆一大竹盘箕,妇女们团团围坐,挑挑拣拣,有说有笑。数母亲去得最多。常宁不在家,又得孩子,崔岑一个人不容易啊。母亲常这样感慨。
这天傍黑,鸡鸭都进了,母亲在灯下补衣服,没有起身。父亲觉得奇怪,瞟母亲几眼,忍不住问,哎,今晚怎么不积极了?崔岑的茶壳子都挑完啦?
母亲低着头一针一线,嗫嚅道,不去了。
她家茶壳子不挑完,茶子不上榨油房,你是不回的。今晚……莫不是常宁回来了?父亲追问。
没呢。母亲的声音细了下去。常宁寄了1000块钱,前天她从邮局取回来,笑得合不拢嘴,晚上还给了“华乐香”,昨夜讲钱不见了,也没其他人进屋,就我和另两个人……我们一起帮着找,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找着……
父亲盯了母亲许久,一字一顿道,崔岑怀疑你们三个中有人偷了钱?
另两个是常宁的姐姐。她们都怪怪地看着我……我怎么会拿她的钱呢?这钱又到哪去了?母亲一急,声音都带哭腔了。
这下好了,做好事反倒背黑锅了,唉。父亲长叹。
母亲平静下来,说,我没偷,身正不怕影斜。
接下来的日子,正如父亲所料,村里关于母亲的流言四起,更有人背地里戳脊梁骨。母亲背负“小偷”的罪名为村人所不齿,我也跟着抬不起头。有时候,母亲躲到里屋流眼泪,伤心与委屈如影随形,她的腰身也不再挺拔。我不知怎样安慰母亲,唯有默默地陪着她,替她拭去眼角的泪花。
那个秋天,崔岑再没来我家,母亲也未去她家。偶尔在村子里遇见,崔岑的眼里就像有两把刀子,寒光闪闪。母亲见了,心里不由得发慌,就算浑身长嘴她也说不清了。
常宁知道这事后,回家揪住崔岑的头发往死里揍,还朝着我家方向破口大骂:哪个偷了我的钱,走路要被汽车轧死,过河要被大水淹死……留着吃药,买棺材……父亲从别处听到此话,一气之下,抡起锄头,要找常宁拼命。幸得母亲死死地抱住父亲,膝盖磨出血也没松手。
常宁在家没待几天,就把十箩筐乌黑发亮的茶子卖给了肖懒鬼,带上崔岑到长沙工地干活,过年都不曾回村。
端午节到了,崔岑独自回娘家。不料天黑地暗,暴雨肆虐,水府庙水库水位猛涨,浊浪排空,掀翻轮渡,包括崔岑在内共4人罹难。
超度崔岑亡灵之前,需梳洗妆抹,换上干净寿服。崔岑在水里浸泡了三天,捞回家时全身浮肿,面目狰狞,无人敢近前。只有瘦瘦的母亲走过去,剪其衣褛,摆正其身躯,从头到脚,为其去沙除垢……弄得大汗淋漓,却一丝不苟。
崔岑妹子,你那1000块钱,也不知你咋地混进箩筐里了,肖懒鬼榨油,上机焙茶子才晓得,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崔岑妹子,你安心上天堂吧。母亲长吁一口气,像卸下了一副重担。
装殓完毕,崔岑被白布包裹着塞进了棺材,合上棺盖。
母亲洗了手,默然回家。此后,母亲成了一名乡村“装殓师”,每有女性去世,都是她做最后的清洁。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剑南文学》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