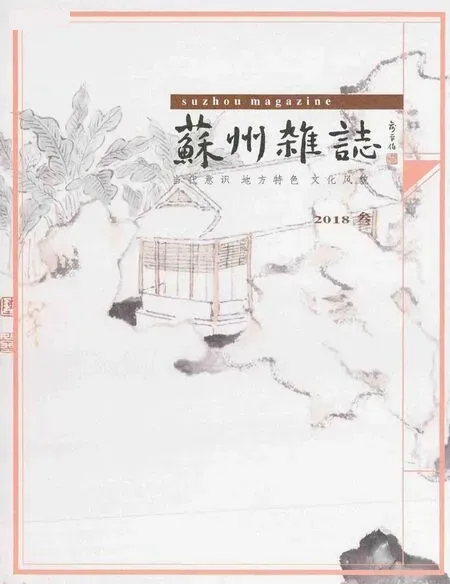宿栖小沧浪
周湧

小姐是广寒宫紧闭广寒门,只有嫦娥影与行。无趣味,暗伤神,傍妆台,不语暗销魂。好比失宠宫妃面,下第举人心,非醋非酸一阵阵生······
有线喇叭里播着苏州评弹《珍珠塔·哭塔》,正在乌鹊桥弄20号小院井边刷鞋的陈家保姆听得是津津有味。而这一古词曲对于才爱上南国广东音乐不久,又从湛江野战部队调到苏州医院的我母亲来说,听这软绵绵的苏州评弹就和听天书一样,一句都听不懂。1959年秋,我母亲从南海边的法式建筑里迁居到小桥流水的苏州后,生活节奏一点没有跟上“苏州节拍”,居住也是一直在“打游击”,东住个几周,西住个几月,后来,有了孩子之后总算分得乌鹊桥弄20号里的一间平屋。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乌鹊,亦称喜鹊,每年七夕为牛郎织女搭桥相会。住在乌鹊桥弄,自然先是想到了相聚,这对于十年来一直漂泊在外,过着单身和分居生活的我父母来说是一个好兆头。这乌鹊桥弄,北接乌鹊桥,南过大云桥,是一处典型的“水乡人家”之居。行过十全河上的乌鹊桥,从北可步入乌鹊桥弄,弄口很窄,只有六尺宽,不过光滑的弹石子路面上很是干净。传说这条老弄堂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宋元时期曾有几户大户人家居住在此。元末,“大周国”吴王张士诚定都于平江(苏州)。元至正二十六年九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明军围攻张士诚,张士诚为了坚守平江城(时称隆平府),拆了城南与城北两地的大片房屋,种粮种菜,自给自足。而这条乌鹊桥弄往南正是通往城南,弄尾衔接着大片菜地,当年兵燹时形成的田园风貌依旧,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不过,这条弄堂北端还是热闹,离百年老店万康南酱店很近,打个酱油、买点南北货啥的极为方便。可是,我母亲在乌鹊桥弄里住长了也有一些不满意:一是,这里的房屋太小,只有一间,如果上海来个亲戚或者雇个保姆啥的,都没地方可住;二是,弄堂南端的大云桥边有个“粪码头”,每天窄窄的弄堂里有不少粪车经过,颠簸的弹石子路面上时常让粪水四溅,倘若行人不注意避让,粪车里的粪水会溅到你的嘴边,这个滋味常人自然难以忍受。最让人难熬得是,我母亲到一〇〇医院上班时要经过这个“粪码头”。桥堍这个“粪码头”是个很老的“水朝”码头,存在了许多年,也没有搬迁的迹象。运粪的几条船只每天会停在粪码头边的河道里,敞着大大的舱口,臭气熏天。管理这个码头的“粪老板”是个老“粪头”,不过,他为人还可以,只是他那个满手戴着金戒指的老板娘比较凶,连来往于羊王庙河里装粪船上的“乡下人”都怕她。我母亲算是盐商家庭出身,从小生活优裕,也很爱干净,所以她每次经过“粪码头”时都要下意识地捂着鼻子,而她这种“富太太”似的举止如被粪码头上的老板娘看见的话,会给她一个凶狠的白眼,然后嘴里还会吐出几句难听的脏话。
遇到这些不顺心的事,我母亲只能埋怨我父亲不应该离开广东。在广东时,他们听听南国雅乐,喝喝广式早茶,住住法式洋房,生活很是惬意。再说当初我父亲从军大毕业时,还是有机会分配到广州的,只因他是个孝子,恋家思乡,心里总想着工作单位离上海老家近一点。现在可好了,已经在广东过惯了的我母亲只能埋怨他是一个“人无远虑”的孬男人啦。不过埋怨只是一时,生活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总是有着距离的,眼下,他们只能期待医院领导给换房了。可是,当初医院的住房还是比较紧张的,福利分房除了要看家庭人口,还必须参照你的行政级别。
1960年4月,我父亲在医院的见习期已满。5月10日,医院为他向上级机关申请的“任命书”已下发,这天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任命为“第一〇〇医院口腔科军医”。
有了这张军医“任命书”以后,申请改善居住条件一事似乎变得简单起来。5月提出住房申请后,只等了几个月,医院院务处就通知我父亲可以看房搬家了。
这回我父亲分得的两间平屋正临水色碧青的沧浪池南岸,东边一间紧贴着古典名园沧浪亭,西边一间隔着眼科程医生家;二房北窗均临水,三月隔水可观彼岸桃红柳绿,七月依窗可赏水中荷花鱼虫,倘若你有兴趣,窗口架根钓竿,在家可享钓鱼钩虾之乐;朝南主房开门就见太湖石堆成的假山,假山上除了一棵粗大的糙叶树外,还有几株芭蕉、棕榈点缀,次房门往西开,开门即邻平屋长长的轩廊,次房南面还有一扇小窗,开窗可见假山上的一株百年香椿树。这里两间房,主房地板,次房青砖,院落中央还有一口古朴的公用水井,我父母俩乍看一眼这房屋与这环境就喜欢上了这里。
当年拿到好房子,表达自家喜悦心情的举止是:笑眯眯地上街买两把新挂锁,然后再请上医院的王司令(木匠)为“新”家补一下老地板和填几块青砖地,这在当年算是最奢侈的“装潢房屋”了。王司令帮着修房时,我父亲才从王司令那里了解到:这个小院原本也是属于沧浪亭的一处西花园,这里幽曲的L形轩廊入口处的轩壁顶端嵌着一块陆墓金砖,金砖上阴刻着黑底的“小沧浪”三字,故此,住在这个园林般院落里的人们,把这秀丽的地方叫作“小沧浪”。
六十年代宿栖“小沧浪”院落时已是秋天,那时,邻居们在出入“小沧浪”院落的小石板桥上,或者在不远处的小木桥上,总能看到我恩奶背后背着一个“粽子包”,不辞劳苦地整日把她那个心爱的孙子背进背出的。而窝心待在“粽子包”里的孙儿郎子对恩奶的“粽子包”很是依赖,每次只要一松开“粽子包”,他就会嚎哭乱叫,恩奶没有办法,只能让他吃睡都在“粽子包”里。由于“粽子包”里空间狭小,外面的风又大,所以郎子总爱缩着头蜷缩在“粽子包”里,以至于他长大后脖子特别短,这一事后来让特别疼爱他的恩奶后悔不已。
搬到“小沧浪”大院后,对于还在“粽子包”里牙牙学语的郎子来说是一件好事,所谓孩子的好事就是,这个大院小孩极多,有个说笑,也有个看头。远的不说,单单是门口的小院落里,就有口腔科陈医生家的大鹭、大嫘、大舰这几个大姐大哥,还有隔壁眼科程医生家的珉珉这位小姐姐,院口住着的王护士长家孩子阿阳,则与郎子是同年的。这阿阳的母亲王护士长,心底特别善良,也喜欢孩子,郎子经过她家门口时她总爱逗一下他,或者在他嘴里塞半颗糖果。阿阳妈妈王护士长是医院自己培养的老护士了,她1952年9月就在一〇〇医院的前身“苏南军区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毕业。这所解放后被解放军接管的护士学校创办于民国二十八年,原本是日伪统治苏州时期“日本华中铁道医院”所创设的护士班的老底子。解放前,不说别的,单就西医来说,日本比旧中国领先许多年,而且当初派到苏州“铁道医院”来的日籍各科的主治医师基本都有医学博士学位,医疗技术精湛。但是,日据时期他们一般只为日籍侨民和日籍军人服务,中国只有少数“达官贵人”才得到他们的医治。除了日籍医师,各科的日籍护士技术也不差。不过,由于当时医师需要带着护士一起去出诊,所以,医院里的日籍护士就经常不够用,这样,“铁道医院”就开设了护士班培养中国籍护士。有趣的是在这些日本人培养的护士中走出了一位“八路军女战士”,这位女战士就是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从苏州“铁道医院”逃往延安去参加“抗大”的姚权。姚权在日本人的“铁道医院”里做了五年护士,技术过硬,解放后被解放军部队提拔到“福州军区护士学校”当副校长,可惜,她在1969年3月时因公牺牲,成了革命烈士。这里之所以说到姚权,是因为“苏南军区医院”培养的王护士长和姚权一样,技术过硬,连后来走的路也和姚权一样,从事护士培训工作,她们俩都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强的医护人才。
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席卷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很快波及到“鱼米之乡”的苏州。1960年秋天,我母亲接到她四哥的来信,说是在长沙的母亲病了。得知家里这一情况后,我母亲心里很着急,向医院申请了探亲假,奔赴长沙准备去服侍自己父母一段时间。到了长沙后,她进门就发现原本瘦小的母亲满身浮肿躺在床上,而原本肥胖的父亲却瘦成了皮包骨,也躺在床上。顿时,她心里一阵难过。为了避免父母看见她落泪,她假装去厨房里做饭。可是,她找遍了厨房里的米缸和可能放米的地方,却没有看见一粒米。这时,她实在忍不住了,端着空锅子在厨房里哭了起来。在外间躺在床上的父亲似乎听到了她的抽泣声,咧着嗓子道:“丫丫,我们晚上煮山芋吃。”听到父亲的话,她才发现,厨房的门后面有几个快要霉变的山芋。我母亲看见这几个山芋几乎已经不能吃了,于是就找来一只空米袋,准备去粮店量点米回来。我母亲娘家住在长沙清香留,这里算是长沙的市中心了。可是,这天她跑了清香留附近的七八家粮店都没有量到,拿着空米袋回家了。这一夜,她躺在床上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我母亲一早就出了门,找了一位医生来家里为她父母看病,医生一看,两个老人并无大病,都是被饿坏了,一个是饿过了头,得了浮肿病,另一个也是营养不良,心脉很弱。送走医生以后,我母亲把随身带来的两大包饼干和一百元钱放下,自己则感觉再也没有脸待在家里来与父母分抢地上那几只山芋了。傍晚时,她瞒着父亲,只是悄悄地和母亲说了一下,空着肚子赶到长沙火车站,返回了苏州。
这三年的灾害似乎没完,可是,越是困难时期人越是有“事”。这“事”就是我母亲从长沙回苏州后不久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由于当时是灾害年,她没有把自己有喜的事告诉给娘家人听,只是独自扛着。在困难时期,部队里虽然有一口饭吃,但是比起往年来饭堂里的伙食缩水了很多。特别是女兵,抢饭、抢汤啥的原本就抢不过男兵。怀孕时的我母亲也一样,在饭堂里经常吃不饱。每次,她走进饭堂时总是希望满满,可是,饭堂里总是摆着一桶舀不到几粒米的稀饭,或者是一桶捞不到几根面条的烂糊面。吃完烂糊面,她想再去看看有啥可以吃的,可是桶里连一根菜叶也没有了。无奈地走出饭堂,可她总还是有点不甘心,回头望望,看看还有无别人落下的东西可以吃,可是,空荡荡的饭堂里总是让她失望。由于在饭堂里吃不饱,肚里的孩子又需要营养,所以我母亲就经常随身带着个盖碗,到医院豆腐坊里看看老殷那儿是否有点豆浆让她喝一口。在那时,豆腐坊似乎成了医院里怀孕女兵的惟一寄托,每个孕妇都希望增加一点植物蛋白来加强营养,培育胎儿,所以一时间,连豆腐坊里的豆腐渣都变得紧张了起来。我母亲与豆腐坊老殷平时就关系不错,这回她怀孕后两人的关系似乎又密切了一些,打豆腐浆时,老殷会多给她一些,另外供求紧张的豆腐渣,老殷也会私下藏一点留给她吃。
1961年6月间,我母亲的第二个孩子,“丫头”出生了。这“丫头”出生前就营养不良,出生后全身发黄,而且身体里的黄疸迟迟不退。那年4月,正巧台湾蒋介石执行“国光计划”反攻大陆,我父亲作为一〇〇医院“东南沿海前线野战医院”的派遣人员,留下了“血书”被部队派往温州地区执行备战任务。东南沿海备战紧张,无法顾及刚出生的孩子,苏州家里只有我恩奶来照顾我母亲。这个“丫头”真是生不逢时,出生后就没有奶水吃,孩子饿得不行,整天哭闹,可怜的是,由于没啥吃喝,这“丫头”时常连哭闹的力气都没有。家里拿这“丫头”没有办法,只能把她送进医院病房挂盐水补充营养。“丫头”在医院医治了几天,病情略有好转,黄疸似乎也退了一点,医生看她好转,建议我母亲把她带回家观察几天。“丫头”回家后我母亲想起了她老家的一种偏方,就是用“蟾蜍敷肚脐”来消除婴儿身体里的黄疸。蟾蜍当时化验科里常用,我母亲平时虽然有点怕这蟾蜍,不过为了救自己的亲生骨肉,她还是决定用偏方试一下。可是,用上“偏方”也不管用,没过几周,这“丫头”的病反而有所加重了,看来待在家里“医治”还是不行,只能再次把她送进医院。这回送进医院的“丫头”病情确实加重了,需要输血救命。可是困难时期,大家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去献血,所以血站里根本无血可供。这时,在上海的我父亲的二妹听说侄女病重需要输血,连忙从上海赶到苏州为“丫头”献血。其实,我这位二娘娘在上海自己也饿得不行,有一次她在“自留地”里刨到了一只山芋后,洗都没洗就往嘴里塞。就在这样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我这二娘娘还两次专门从上海来苏州为她侄女献血。
这个大灾之年出生的“丫头”先天不足,命又苦,只在人间只活了半年多,就夭折了。
“丫头”送葬那天,我母亲悲恸欲绝,被几个好友强行劝留在医院病房里,不让她去火葬场看见那悲伤一幕。“丫头”她父亲,没能赶回来,因为他要坚守在东南沿海前线。
送走“丫头”的那天傍晚,一只老鸦正巧落在“小沧浪”院落树梢上鸣叫,听到老鸦怪叫声,还沉静在悲伤之中的我恩奶似乎突然间醒悟了过来,随手拾起一块瓦片,对着老鸦嚷道:“丧门星!我家丫头就是被你这个坏东西给叫死的!你给我滚!”
或许1962年这样的灾荒之年就是多死人的年份,这一年的1月17日,一〇〇医院山东藤县籍“三八式”老干部华一山副院长,在用烧煤炭炉子取暖的医院浴室里煤气中毒身亡!我的那个未曾谋面的“丫头”姐姐夭折的时间离华一山副院长去世时间很近,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或许就是为了与华一山烈士短暂相遇的。
点燃清香一炷,祈愿他们在天之灵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