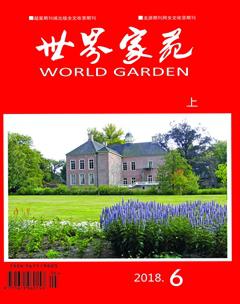论“大历史”的书写与关照
张艳鑫
摘 要:历史学的本质是求真。人们总是从两个角度解读历史:其一是从整体上掌握人类历史的来龙去脉;其二是关注具体的历史场景。当下学界历史视角的选取和史料的把握呈“碎片化”,这也是历史失真的因素之一。汤因比的“大历史”学说和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 “ 整体史” 与“ 长时段” 理论研究及其影响下的黄仁宇“大历史观”对坚持历史的总体性,以及对我们当下历史问题的解决和史观的把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唯有从整体上探究其深化动力及深层结构,才能摆脱“碎片化”的困窘,而不会在碎片中走向虚无。
关键词:“碎片化”;大历史;长时段;总体史
一、引言
后现代主义史学解构宏大叙事、否定历史的统一性与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在此影响下,学术研究论题过于琐屑,人们甚至放弃对于历史总体性的认识以及对于历史意义的追求。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如何把握微观视角与大的历史视野之间的关系及平衡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历史学的“碎片化”问题
(一)“碎片化”对历史解读的削弱
成千上万的细节组成了历史研究对象,然而历史细节毕竟有主次之分,随意提取甚至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样貌。随心所欲地将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再加以解构和从细节上解读历史有所不同。“碎片化”不仅在研究视角的选取上片面,也在于所选史料的片面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对历史事实的层层“失真”。首先是历史研究视角的“碎片化”,其次是史料捡选的“碎片化”,此外还有表述的“碎片化”。
历史的建构有选择性,记忆是一个积极的、有选择性的建构过程,我们的心理认同就好像一张过滤网,尽可能无限靠近历史事实,但永远不可能达到求真。我们所说的事实经常混杂着本身的学术知识建构,个人的文化背景知识和立场的不同,对真实的认知也会有差距,对同一事实的认识和表述也有差异。影响历史叙事的尚且有“意识形态立场”、因治学路数不同形成的“门户之见”等。我们的遣词用字已经在社会文化心理下让描述对象成为新的建构。无论以何种方式诉说、书写历史和社会真相,所呈现的是在自身记忆筛选下以及表述手法安排下的事实或真相。在提取材料佐证自己的观点时,往往已经过分片面地进行了形而上的割裂。
(二)“碎片化”的研究现状
随着民间文献大量涌现,口述、书信等史料层出不穷,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为重点的新史料观在史学界如日中天,对历史学形成了冲击。在传统史学重政治史、经济史和帝王将相史的学术背景下,在史学领域涌现出“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学术浪潮,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深入到更具体的层面。这种学术认同中,历史学家就像把散落在地上的土豆用绳子串起来一样,从中建立一种联系从而呈现历史全貌。然而,很多研究却就碎片而谈碎片,研究领域也越来越狭窄,重叙事、轻理论蔚然成风,中国史学“碎片化”越发严重。这便导致史学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問题被淡薄和漠视,一些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重大理论问题长期处于冷门。相当一部分学者都只满足于具体细碎问题的研究,把在局部知识点上的进步奉为法宝,忽视对总体性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即使作为断裂的碎片也能反映整体样貌,从而只需要证明如何从断裂的片段看到历史的整体就可以,片面地就碑而谈碑,就史料谈史料,整体历史学的面貌却未能从根本上改观。正如王学典所言,“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这是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
微观和具体的命题最终要逐步走向宏观,细致入微的研究终归要置于宏观的历史洪流中去。“碎片化”问题很多情况下难以经受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理论构建。局限于对个案的研究,经常是一种偶然性甚至谬误的解读,狭隘性也可能使历史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其次,缺乏理论性的阐释而只有碎片化的解读导致对根本性问题的关怀不足。若对细碎的史料“自下而上”进行条理化,使之成为整体史中的合理要素,细节研究自当构成推进整体历史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础性价值不容忽视。在“碎片化”弊端的启发下,我们不禁要反思史学研究视角。
三、“大历史”、“整体史”与历史研究
不同主体对“大历史”的理解不一,它可以是一种历史的观念、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一种叙事手法。其中,它更多被当作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来用。东西方学者均对此予以关注,较为常见的有汤因比的“大历史”观和布罗代尔“ 整体史”与“长时段”理论及其影响下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拉开距离审视历史更易通古今之变。“整体史” 观提倡史学多元化发展,历史的时间被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时间和空间统一,历史是特定时空连接点上的一个坐标,就成为自然、社会经济与个人事件三位一体的“ 总体史”。把宏观视野和整体思维融入大历史之中的方法逐渐成为史学共识,并扩展到了人类历史的哲学立场。这种“大历史”观不仅是具体的历史观念,而且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强调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历史因果关系的合理性,主张用宏观的历史眼光与理念考察历史,在考察一段历史时将历史的基线向后推,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看历史,而是力图勾画社会整体面貌。
历史研究的适当范围是整个世界所有时间段。汤因比“大历史”写作超越了传统历史中的国家、民族等概念,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地理环境问题也得到关注,各个较为独立的文明被整合成一部世界史。可谓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考察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洞察并预见了当代全球的发展方向。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将人类史与自然史视作一个整体进行描述;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则描述人类这个物种从产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皆为大历史的视角的伟大尝试。
四、结语
克服“碎片化”,关键在于回归“总体史” 和“长时段”。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最终归旨之一是认识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探索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从而服务于社会现实。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要宏观地照顾到那些人类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社会形态。纵观自古以来整个人类史上,东方有对 “道”的追问,西方有对“命运”、“逻各斯”等社会使命。历史学作为一种反思当前和前瞻未来的工具,不仅要求掌握大量史料,而且强调理论假设,与微观史学相比,更大胆地建构人类历史基本脉络和规律,甚至上升到历史和哲学层面。这无疑对人类命运的相关命题提供借鉴,进而可以建构起全新的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中国历史解释框架和叙事方式。
参考文献
图书:
[1](美)李怀印 著,岁有生、王传奇 译.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北京:中华书局,2013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学术期刊:
[1]宋雪玲.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17,12
[2]李勇.论中国史学面临的“挑战”——学术史视阈中的考量.东岳论丛.2017,10
[3]张艳国.章开沅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理论贡献.江汉论坛2017.11
[4]张仲民.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5]刘耀辉.大历史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7,4
[6]孙岳.超越人类看人类?——“大历史”批判史学理论研究.2017,4
[7]何兆武.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史学理论.1989,1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