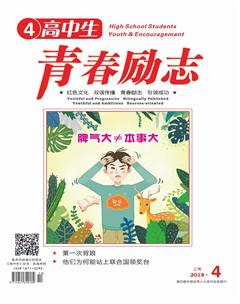读书相长
沈书枝
作为真正在乡下长大的小孩子,我能读的书极少。从小学到高中,除了语文课本以外,我所读过的书,几乎能数出来。大部分是大姐在外面读书、工作时买了,给我寄回来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一本《古希腊神话》,一套精装硬壳的《堂吉诃德》和三册青色封面的《平凡的世界》。
我平常若还想有额外的书读,就只能到亲戚家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一两本。
初中的时候,我在村子一户人家的屋顶上,捡到一本没有封面的短篇小说集。它被雨水打湿后又被太阳晒干,变得很蓬松,我把它捡回去看。
上大学以后,我才回忆起那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百花文学”作品集,充满那时“主题先行”的意识形态。然而,在生硬的外壳下,一些柔软的人性的东西,温柔地包裹在里面。
如今回想起来,一种我的性格里注定偏好的东西,在那时已经出现了端倪。俄狄浦斯悲惨的命运使我感到难过,堂吉诃德疯狂的胡言乱语使我感到惊异。高三时,我第一次从邻居那里借到沈从文的《边城》。当时,我连沈从文是谁都还不知道。然而,一读之下,我还是深深地感觉到,《边城》那样的作品,正是能打动我的充满人性与美的作品。
因此,大学读了中文系以后,我就去找更多沈从文的书来读。那优美的文字里的深切悲悯使人忧愁。受这种影响,我开始学写小说,试着将自己在乡下所经历的难以忘却的事写下来。自然都写得幼稚,从题材到语言,都有着很重的模仿的味道。然而,这算是我文学写作的起始。
因为课业的关系,那时,我读了许多现当代文学作品,有的喜欢,就多读了几本,有的硬着头皮也读不完一本,就放下了。最后,读起来最觉亲近的,还是沈从文、周作人、汪曾祺与废名等人的作品。
我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受戒》时,简直觉得惊艳,因为难得见那样活泼、可爱、如明净的梦境一般圆满的故事。在我们现当代文学作品里,像这样不充满悲惨与批判的小说实在是太少见了。因此,我立刻找了汪曾祺大部分小说来看。
周作人的自选集在图书馆的架子上一册一册排得很长,我无事时去借,每次挑封面和书名喜欢的先读。在读周作人的作品之前,我对散文的认识大概只停留在中学的“美文”阶段,读了他的作品之后,我才知道散文有如此质朴的根底和开阔的境界。“嘉孺子而哀妇人”是周作人许多文章体现的精神。不知道是不是受他的影响,作为他的弟子,废名的作品里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废名的作品里时常跳跃着一颗儿童的心,这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一直到大学毕业几年后,我才真正开始写一点东西。一旦开始写起来,从前读那些作品所受的影响,就会不自觉地在笔下表现出来。它可能并不外化得那么明显,然而,我知道自己对家乡、自然与从前的人与事所表现出的温柔来自何处。
我的朋友叶行一有一天说:“一个人如果去写作,是不是就靠几个作家的几本书打基础,其他的阅读不过是开阔一下视野?就像是练习书法,一辈子也就守着那一两本字帖。”书法我不懂,不过,我很喜欢“临帖”这个说法,我的写作好像的确就是这么回事。我就是读到喜欢的作家们的书,心里感到欢喜,受此触动,最终开始写自己的东西的。
后来,我虽然也讀过许多其他作家的书,但如他们的作品那样在我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迹、帮助我认识和寻找自我的书,却很少能再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