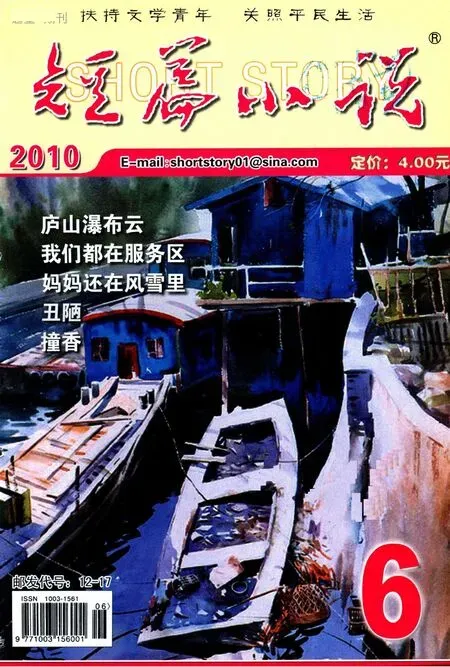矿山人物志
◎王晓峰
厨师关胖子
头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这句话用到关胖子身上绝对的标准。
关胖子叫关项英,是李庄子煤矿职工食堂的主任。关项英一米七五的个头,长得头大身子胖,往那一站,就像半截缸放在地上。
关项英是河北保定人,关项英当过兵,复员后先是被分到李庄子矿一掘队,后来矿职工食堂要人,当时的矿长马富国听说他在部队当过炊事员就感觉专业对口,让他到职工食堂当了伙夫。后来,食堂主任李大彪退休后,就提拔他当了副主任,而后转正当了主任。
关项英家住在矿区北渣堆,家里有六口人,其中三个儿子。我和关项英的二儿子关长空是同学。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叫长天、长空、长云。记得小时候,我也曾去关项英家去过几次,找他的二儿子玩。那时候,关项英还没当主任,每次见他都是戴着一副蓝色的袖套,浑身上下白乎乎的,身上、头发上都是面粉,总也洗不干净。因为他在食堂卖饭,所以我每次见他,都会给他打招呼,叫他胖子伯伯,他会很亲切地冲我一笑。有时候,还会用那肥厚的手摸摸我的脑瓜盖。
那时候在矿上,家家户户几乎都不做饭。就是做饭,也是做一些简单的饭,如做个稀饭炒个菜下个面什么的,馒头肯定是不蒸的。矿职工食堂的馒头蒸得又大又暄又实惠。有时候,家里来了人,大人也总是要我们去食堂买一些馒头,或者买一些菜。因为和关长空是同学,所以每次大人让我去食堂买东西,我总是先在各个买东西的窗口看一遍,看关项英在不在,如果在,就会挤到他卖东西的窗口,递上半斤粮票,冲他挤挤眼,不说话,然后他就会递上你要买的馒头啥的,当时馒头是二两粮票一个,他总会多给你两三个。如果机会好,遇到他在卖菜,你递上一毛钱,他总会给你打一份三四毛钱的菜。这样,一连几天,我就会成为众多孩子倾慕的对象。
后来,关项英当了主任。当了主任的关项英就不卖东西了。但有时候还会在卖饭的窗口转悠。有时候看到他在,我就会故意地大声喊“胖子伯伯”,他回过头来,总会从卖东西的窗口递过来一个包子或者油条啥的,嘴里骂一声“臭小子”。
那时候,矿上职工供应的商品粮发的都是矿上自己印制的粮票,拿着那粮票,到食堂能买到馒头、面条等熟食,但就是买不到面粉,如果想把手中的粮票换成面粉,就得开关项英的后门。特别是有的一头沉职工,一年到头积攒下几十斤粮票,通常会趁过年换成面粉背回老家。那时候,农村种粮的反而粮食不够吃,因此,在食堂当主任显得很有身份。
那时候,不仅粮食凭票供应,就是猪肉、鸡蛋也是凭票供应。每逢年节,如果没有肉票,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而这些肉啊、鸡啊、鱼啊,食堂里都有,如果想买,就得开后门。因此,不论走到哪,关项英都显得很有人缘。
因为手里有了这些权利,关项英就显得不一般了。再以后,见了我们这些毛孩子就不再搭理了,喊他,装着没听见。于是,我们这些毛孩子就聚在一起骂死关胖子,咒他不得好死。关长空找我们玩,我们也不跟他玩。
但最后关项英还是翻了船。
关项英当主任后,求他的人多了,用粮票换些面粉,过年买一些鸡鸭鱼肉啥的,都得找他。于是,有时候,关项英就趁天黑把找他帮忙的人换的或者买的东西送去,而且显得很神秘的样子。这些人中,有的是矿上的各级领导,他得罪不起,不得不送;有的是他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人在世上混,谁没有需要帮忙的时候;还有的是关项英的“特殊顾客”。说特殊,是说和关项英的关系不一般,如一些特殊的女顾客,为了报答关项英对她的特殊关照,有些就甘愿“投怀送抱”,甚至以身相许了。
关项英凭借手中的“特权”“俘虏”了这些女人,很快就又沦落为这些女人的奴隶。这些女人,如果需要换面粉或者买鸡呀肉呀的,给关项英说一声,他就屁颠屁颠地送去。
在关项英相好的女人中,有个叫英子的小媳妇,因为长得甜美,深得关项英的喜爱。英子是二采队何大山的儿媳妇,何大山有三子一女,大儿子何卫国在矿务局财务处当科长,二儿子何卫家在部队当兵,前两年上了军校,现在部队提了副连长,三儿子何卫田在矿保卫科当民警,女儿何卫风还在上初中。英子是他的二儿媳。
挑起事端的是何大山的三儿子,在保卫科当民警的何卫田。一天何卫田在无意中听到二嫂的事后,认为是对他们何家的最大侮辱,于是就在一个深夜,潜入他二嫂家附近,当事毕的关项英从英子屋里兴冲冲出来的时候,被他从后面一个砖头盖在头顶,然后拿起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铁棍朝关项英左腿就是一下,只听“咔嚓”一声响,关项英的左腿必断无疑了。
后来,关项英被上夜班的矿工发现送到医院,因为理亏,清醒后他也不敢说出事情真相,只好吃了哑巴亏。
矿上得知关项英的事后,也觉得蹊跷,就安排矿纪委下去调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关项英当食堂主任的六、七年时间内,竟有三千多斤猪肉、近万斤面粉对不上账。问关项英,说是给领导和关系户送礼了。
但无论怎样,关项英的主任是当到了头,后关项英被调到矿职工澡堂看澡堂直到退休。
后来听说,何大山的二儿媳英子也与何卫家离了婚,离婚后的英子,回到了老家驻马店再没有消息。
当然,这已属题外话了。
清洁工张德子
张德子是个清洁工。
张德子不是一般的清洁工,张德子在李庄子矿机关大院里打扫卫生。张德子是新安县石寺乡人,张德子是七零年参加工作的,张德子最初在一掘队抡大铣挖煤,后来因在井下出事故砸坏了腰,才调到地面打扫卫生。刚调到地面时,张德子先是在学校门口扫大街,后来有一年冬天,机关打扫卫生的马四清因为煤气中毒死了,队长张祥雷就安排张德子顶替马四清到机关院打扫卫生,一扫就是好多年。
张德子个子不高,是个瘦子,属于精瘦精瘦的那种,瘦到啥程度,这么说吧,夏天他如果穿个背心,你能看到他胸脯上的肋条,一根一根的,十分清晰。张德子在一掘队时有个外号叫排骨,确实人如其名,机关里的人觉得也十分恰当,但机关的人不这样喊,机关里都是些文绉绉的文明人,文明人怎么能侮辱人呢?再说一个整天在矿机关里进进出出的人,怎能是根排骨呢,咋着也得是个胖子。于是,就有人给张德子起了一个新外号——张胖子。叫的人多了,人们觉得也很般配,好像张德子就应该叫张胖子一样。
在机关院,张德子主要任务是打扫机关楼卫生,一至五楼的楼道和卫生间都归他管。领导办公室的卫生不归他管,领导办公室配有通信员,通信员不仅负责给领导送报纸,还兼给领导打扫卫生,提个开水,拖个地,整理个办公室啥的。干通信员的,一般都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男孩子,年龄通常都不大,也就十六七岁,当通信员的还有些是有根子有门路人家的孩子,让孩子伺候领导几年,然后找一份诸如小车司机、供应科计划员之类的好工作,是矿上每个干部职工的心愿。因此,能给领导当通信员的,一般都是比较机灵的孩子。
因为要赶在八点钟机关人员上班前把卫生打扫干净,张德子通常不到六点就起来了,冬天六点钟,天还不太亮,就听到张德子刺啦刺啦拖地的声音。干通信员的孩子,因为年岁比较小,早上常常起不来,一般天明,通常都是七点左右,因为要赶在八点以前把领导办公室打扫出来,通常都是急匆匆的,抹桌子提水,一路小跑。通信员给领导打扫办公室,有时候,还会清理出一些纸箱子、废报纸啥的,因为时间紧张来不及清理,通常都是掀开帘子,在楼道理吆喝上一声“张胖子”,张德子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看见门口的废报纸破纸箱,喜得鼻子眼都是乐的。然后,他就拎起他的战利品,美滋滋地回到他的小屋。
机关楼西楼一楼楼梯下可着楼梯的坡度挤了一间小屋,那是张德子的“办公室”兼储藏室,他在机关院里拾的废纸箱、废报纸啥的都在这里存着,存到一定程度,他会拉个架子车,把捡的废报纸破纸箱啥的送到废品收购站,废报纸一斤五毛钱,纸箱子一斤两毛钱,虽说不多,但天长日久,积少成多,也非常可观,这也是他在别处打扫卫生没有的,因此,张德子干得很认真。
为了能收集更多的破烂,张德子对机关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尊敬,不论见了谁,脸都是笑得像一朵花。有的人懒得去提开水,就站在办公室吆喝一句“胖子”,话音未落,张德子就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然后双手拎着四五个暖瓶如飞而去,不一会儿,就把满满的开水打了回来,放在门口的桌子上。然后,弓着腰,走到一张办公桌前,谦卑地对着那个指使他的人说句,李主任,水提来了,以后有啥跑腿出力的事,您只管说话。那人有时候鼻子会哼上一声,有时,干脆头也不抬,摆摆手,让张德子退下。
张德子除了打扫卫生,还有一件常做的事,就是修剪院子里的冬青树。李庄子矿机关院里有一个花池,花池外围种的是冬青,冬青长得很快,有一个多月,树头就长出来了,参差不齐,乱蓬蓬的。张德子就拿了一把很大的剪子,两手执着剪子把,叭嗒叭嗒地剪,剪得一地冬青叶子。不一会儿,整个花池外围的冬青树就剪得平崭崭的,像一排刚理过发的孩子。于是整整一天时间,院子里到处都是冬青嫩叶子的清香。
张德子还给院子里的花草浇水。
李庄子矿机关院很大,但中间广场占了不少面积,广场距离机关主楼大约10米的地方还砌有一个十五六平方米的水泥台子,台子周边用大理石贴了一层,台子中间是一个旗杆,旗杆上飘着一面国旗,每逢“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机关里都会举行升旗仪式。因为广场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院子里的花池就不是很大。院子里的花池里,冬青的树围子里面除种有两棵广玉兰外,还种有三棵石榴树。石榴成熟的季节,矿上的一些孩子会趁机关下班的时候来偷摘石榴,但因为机关院有保卫科的民警把守,所以总是不能得手。另外,花池里还种有一些月季、牡丹、剑麻等花草。张德子就给这些花浇水,用一个很大的喷壶。
院子里紧挨机关楼的地方还种有一圈白杨树,秋天到了,杨树叶子落了一地,张德子就拿一把大竹扫帚扫,刷刷刷,刷刷刷,下班时间到了,地上还有不少落叶,张德子也不回家,继续扫。张德子不回家,有时候,张德子的老婆就会提着饭盒把饭做好了送过来,两个人躲在楼梯下的小屋子里吃。
吃过饭,张德子的老婆去卫生间外面的水管前把饭盒洗干净,然后一扭一扭地就走了。
张德子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儿子已经成了家,女儿还在上初中,因为家里住得紧巴,所以大部分时间张德子就住在机关楼下的楼梯间里。
张德子捡拾破烂,有时候处理得不及时,就堆在楼梯间外面,机关党委的蒋树方书记见了,就把他叫到办公室训斥了一顿,说,打扫卫生就打扫卫生,不许捡拾破烂,弄得机关院就像个收破烂的店铺,并警告他,如果再发现捡破烂就撵走他。
但张德子还是偷偷地捡,看见破纸箱、废报纸,还是往他的储藏室里拎,只是背着蒋树方。
张德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过得很平静,波澜不惊。
下班后,人走了,楼也空了,有时候,整栋楼就剩下张德子一个人了,有时候是两个,还有蒋树方。
蒋树方是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还兼着机关党总支的书记,因为领导有时候要值班,所以经常晚上住在机关里。在煤矿,每个矿领导一个月要值六到八个班。其实值班也没多少事,就是待在机关院里,偶尔矿务局安监处的人会突然袭击来矿上查岗,查值班矿领导是不是在岗,是不是不值班回去抱老婆了。
矿领导的办公室都带有套间,套间里有床有铺盖,还有夜宵。在煤矿,级别到了矿处级,各种待遇都上去了,矿领导不仅配发有香皂、牙膏等日用品,每月还配有水果、牛奶、方便面等,以备值班充当夜宵。
蒋树方是个文化人,先前在矿务局团委当干事,后到矿务局矿工报社当记者,因为文章写得好,深受矿务局付泉林局长的信赖,后任报社新闻部副主任、主任,后调到李庄子矿任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据说下一步要接任矿党委书记。
蒋树方还喜爱书法,他自少年时开始习练书法,初始临摹开封书法名家刘庚三的楷书,八十年代初,考入河大后,对书法的认识渐趋深刻,又把目光锁定“二王”的碑帖,后经过多年的苦练修行,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艺术语言。每当他写了一幅书法作品后,就用图钉钉在办公室的墙上,让大伙欣赏。大伙们就都围过来,指手画脚,称赞哪一句写得好,哪几个字有功夫,他就面带得意,如有谁向他讨要书法作品,他总要推让一番,拿不出手,拿不出手,在他人的再三索要下,才答允下来。
蒋树方的家在矿务局兴苑小区居住,他有时在家里住,有时在机关里住,有时,不值班也来,偶尔碰到人,就说矿里僻静,能静下心来练字、写文章。
因为西楼是党群楼,所以下班后就人去楼空,因此,一到晚上,通常都是整栋楼就剩下蒋树方和张德子两个人。
蒋树方的办公室在党群楼三楼,蒋树方晚上来值班,每天晚上都要从张德子的储藏间上面走过,所以,蒋树方啥时候来,啥时候出去,张德子比任何人都清楚。
有一天晚上,张德子听见蒋树方又来了,不过,这次好像不是一个人,因为他听见有女人高跟鞋的声音。因为蒋树方的老婆偶尔也会过来,所以张德子也没往心里去。等张德子一觉醒来,也没听见有人下来,张德子以为自己睡熟后人家走了。
以后,蒋树方值班的时候,差不多总有女子高跟鞋的声音,有时候是和蒋树方一起,有时候只是一个女人,张德子就留了意。又一天晚上,张德子又听到有女子上楼的声音后,就蹑手蹑脚跟在后面上了三楼,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来到蒋树方的办公室门前,轻轻一推,门开了。不一会儿,就传出两人低低的说笑声。蒋树方的老婆张德子见过,属于高高大大的那种,但这个女子身材窈窕,铁定不是蒋树方的老婆。张德子还往好处想,以为这女子是来找领导说事的。但时候不大,屋子里的灯灭了。
张德子很生气,暗暗骂道:“蒋树方呀蒋树方,你不算人,你家里有老婆有孩子,你还干这些缺德事!”
张德子要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是很容易的。
……
那个女人张德子认识,也是机关院里的,他经常见到。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把她和蒋树方联系起来。
这事自然也瞒不了机关里的其他人。
有一天,张德子去南楼提水的时候,碰见李福军,李福军是抓多经的副矿长,问了几句张德子家里的情况,孩子在哪区队上班,有没有困难,并说有困难可以找他。聊了几句闲话后,话锋一转,问道:“你晚上在西楼住,是不是发现经常有女人往蒋书记办公室里去?”
张德子一听,李福军要抓蒋树方的把柄,李福军和蒋树方不对劲,在李庄子矿很多人都知道。李福军也是矿务局下来的,以前和蒋树方都在团委待过,听说早些年曾共同追过矿务局电视台的一个播音员,结果李福军追上了,但李福军总觉得蒋树方和播音员也有一腿,特别是新婚夜播音员没有见红,更是他一辈子的心病。
张德子见李福军问蒋树方,就连忙说,我不知道,不知道,没有的事不能瞎说。
张德子庇护蒋树方,不是因为蒋树方,而是因为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张德子认识,还很熟悉。那女的是张德子刚上班时的师傅诸子中的女儿诸玲,诸子中八四年出了事故死在了井下,诸玲是顶替诸子中上的班。
以后,张德子捡拾破烂就不太避蒋树方了。蒋树方呢,有时候看见张德子的门口堆得小山似的破纸箱旧报纸,也像没看见一样。
日子像树叶般飘过。过了年,房产办突然通知张德子,让他去领钥匙,南山家属区新盖的家属楼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说是矿上对伤残职工的特殊照顾。
面对从天而降的好事,张德子没有感到一点高兴,而是心里酸楚楚的。
张德子还是继续当他的清洁工。
又一年六月,蒋树方提任张庄子矿党委书记,李福军平调去矿务局后勤处当了副处长。再后来,蒋树方被查出患了癌症,查出来已是晚期,不到一年就死了。同年秋天,李福军去郑州办事,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和一辆大货车相撞,受重伤抢救无效死亡。
再后来,张德子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