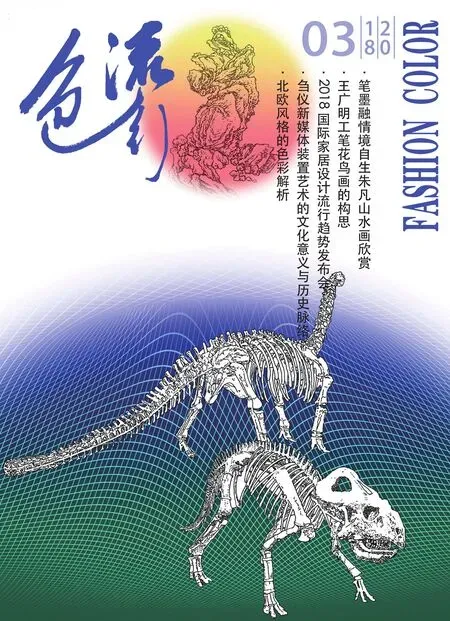读书的情趣与艺术
—— 萨特
林衡哲、廖运范 译
选自《读书的情趣与艺术》

我是从书堆里开始我的生活的,就像我将在书堆里结束我的生活一样。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他禁止别人碰这些书,只一年一次,在十月份开学之前才能给这些书掸去灰尘。还在我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些竖着的石头倍加崇敬:它们或者直立、或是斜立,像砖块似地在书架格子里挤压着,或是间隔摆着,犹如古代石柱形成的通道,高雅而壮观。我感到我们全家的兴衰全系于这些石头。它们都很相像,我在这所小小圣殿里嬉戏,周围是低矮、古老的文物,它们曾看到我出生,也将看到我死亡,它们的永恒保证了我的未来将与过去一样的宁静。晚上常常偷偷地触摸它们,使得手有幸沾上它们的灰尘。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怎样做才好。每天我都看到一些场面,却不知其含义是什么。比如,我的外祖父平时特别笨拙,还得我母亲给他戴手套,可他摆弄这些文物书籍时他的手却像主祭那样敏捷娴熟。我曾千百次地看到他漫不经心地起来,绕他的桌子转一圈儿,一两步就穿过了屋子,准确地抽出一本书。用不着选择,一边翻着书。一边回到他的座椅上去,刚一坐下,就用拇指与食指联合动作一下子翻到需要的页码,并让纸张发出一种皮鞋般的响声。有时,我走近这些盒子,它们像牡蛎一样打开着,我发现里面裸露着的肌体,灰白发霉的叶片,有些肿胀,覆盖着黑色的脉络,吸着墨汁,散发着箘味。
在我外祖母的房间里,书都是倒着放的。她常从一所阅览室里借书,我从未见她一次借两本以上。她借的这些玩艺儿使我想起新年时吃的糖果,因为这些书的纸张又薄又闪闪发光,好像用砑光纸做的似的。这些纸页闪光、洁白,几乎都是崭新的,它们似乎都包含着神奇的奥秘。每星期五,我外祖母都穿装打扮,准备出去,并且向别人说:“我要还书去”。可她回到家来,先摘下黑色帽子和短面纱,然后就从手笼里把书抽出来。我莫名其妙,自忖道:“这是不是还是原来的那几本书呢?”她把这些书小心翼翼地“盖”起来,然后从中选出一本,她拿着书坐到靠窗子的地方。她坐在那把带有野图案的安乐椅里,戴上她的老花镜,不断发出幸福面又疲倦的叹气声。她低下眼睑看起书来,嘴上露出使人愉悦的微笑。后来我在蒙娜丽莎的嘴上又发现了这种微笑。我母亲此时则一言不发,也要我保持沉默。这情景使我想到了弥撒、死亡和困倦,因为此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神圣的静寂。路易丝不时地小声笑了起来,她喊女儿过去,用手指指着一行字,这两个女人便交换一个会心的眼色。但是,我并不喜欢这些装演过于讲究的小册子。这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书,我外祖父就毫不掩饰他的鄙视态度,他瞧不起这些给女人写的玩艺儿。星期天,他常常无事可做,便进妻子的房间,像柱子一样站到她面前,一言不发。大家都注视着他。他把玻璃窗敲得咚咚直响。后来,他想不出别的新花样,便转身对着路易丝,从她手里把小说夺走。她愤怒地喊道:“查理!你把我的页码捣乱了!”这时,我外祖父已眉飞色舞地读了起来。突然,他用食指敲打着小册子,说:“不懂!”
“你怎么会懂呢?你不从头看!”我外祖母反驳道。他无可奈何地把书往桌上一扔,耸耸肩走了。他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写书的人嘛。我很了解这一点:他曾指给我看过在书架格子上摆的书,那是一些厚厚的硬皮大部头,棕色的帆布封面。“小东西,这些书都是外公写的”。多么令人自豪啊!我是创造这些圣物的专业巨匠的外孙,他像管风琴制造者、教士的裁缝师一样受到别人的尊敬。我亲眼目睹他为自己的著作呕心沥血:每年他都要重版(德语读本)。假期时,全家都在焦灼不安地等待着重版的清样。查理忍受了这样无所事事的闲呆着。邮差终于送来了一些又大又软的包裹。有人用剪刀剪断捆包绳,外祖父便打开长条校样,并把它们按次序摆在饭厅的桌子上,挥动红笔改起来。每发现一处印刷错误,他便从牙缝里挤出“见鬼”的咒骂声,直到女佣说已到吃饭时间,要在桌上摆刀叉时,他才停止骂人。此时,大家都很高兴,我则站到一把椅子上,兴高采烈观赏着这些带着血红条痕的一行行的黑字。查理·施韦策尔告诉我:他和发行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外祖父从来不会算帐,由于无生活优虑,他花钱随意挥霍;由于好显示富裕,他对人慷慨大方。到了晚年,他变得吝啬,这是八十岁老人常有的毛病,是老人行动不便、怕死心理的结果。那个时候,他的这种吝啬表现为对别人的疑神疑鬼:当他收到稿费汇款时,他总是举起双臂,喊叫说别人在掐他的脖子,或者跑到外祖母房间,阴沉着脸宣称“我的发行人抢了我的钱,就像树林里的强盗一样”。我从这里吃惊地发现了人剥削人。这种可恶的事情幸亏少见,若是没有这种事世界该多美好啊,老板可以根据能力付钱,工人则可以根据本事拿钱了。为什么这些吸血鬼的发行家不这样做,却要喝我可怜的外祖父的血呢?因为外祖父的献身精神没有得到报偿,我对他更加尊敬了,把他看作圣人。由此,我很早便把教书看作是一种神圣职业,把文学看作是使我入迷的嗜好。
我那时还不识字,但已很时髦地要求要有“我的书”。外祖父便到了他那个可恨的发行家那里给我要来了诗人莫里斯·绍尔的《故事集》。这些故事源于民间传说,作者自称是仍保留了儿童的眼光,根据儿童的特点把它们改编成故事的。我想马上弄懂这些故事,先选了两本最薄的书,用鼻子闻了闻,又用手掂了掂,随意地把书打开到想看的那一页,同时把那页纸弄得发出响声。真是白费劲,我并没有感到弄懂了什么。我又试着把这些书当成玩具娃娃,摇晃它们,亲它们,打它们,这一切也毫无结果。急得我要哭起来,最后便把书放到妈妈的膝盖上。她从针线活儿上抬起眼睛,看着我问道:“亲爱的,你是要我给你读这些仙女故事吗?”我怀疑地反问道:“仙女是在这书里吗?”这个故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母亲常给我讲它,当她给我洗完脸,要给我擦花露水的时候,或当香皂从她手里滑到浴缸底下伸手去寻找的时候,她都给我讲这个故事。对这个太熟悉的故事,我总是心不在焉地听着。我心里只有安娜·玛丽,这个我每天早晨都听到的姑娘,耳朵里听到的只有她的那种奴仆特有的颤抖声音。我喜欢这种故事:讲讲停停,讲了上文没有下文,刚才还自然流畅,一下子又支离破碎,最后变得不可收拾,在一种富有旋律的松散结构中消失,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又重新组合起来。况且放事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是自言自语的联系物。我母亲给讲的时候,我们都是单独的两个人,远离人类、众神和牧师,犹如树林里的两只牡鹿,只和其它牡鹿和仙女们在一起。我简直难以相信能把我们的这种散着香皂和花露水香味的世俗生活片断编进一本书里去。
安娜·玛丽让我坐在她的对面,坐在我的小椅子上。她向前探着身体,垂下眼睑,睡着了。从这副雕像般的面孔发出一种石膏制品的声音。我糊涂了:这是谁在讲述?在讲什么?在给谁讲?我母亲早已离开了我,因为我既看不到微笑,也看不到心心相印的表示,我被流放了。而且,我也不凿她的语言。她哪儿来的这种泰然自信呢?过了好一会.我才明白:这是那本书在说话,一些句子从那里出来,使我感到恐惧。这些句是真正的千足虫,它们集在一起,舞动着音节和字母,拉长了二合元音,震颤着双辅音;它们忽而歌唱、忽而鼻音嗡嗡、忽而间隔着停顿和叹息,充满着陌生的词语;它们自我陶醉,得意于自身的九曲回肠般的结构,丝毫不顾忌我是否能忍受得了。有时候,这些句子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就消失了,还有的时候,我早已懂了,它们却继续雍容高雅地说下去,连一个逗号标点也不肯漏过。当然,这些话不是对我说的,至于故事是美丽动人的:砍柴人,他的老婆和他们的两个女儿,还有仙女。这些小老百姓是我们同类却都染上了庄严崇高的色彩,他们明明是衣衫槛楼,却说成是衣着华贵,真是文过饰非,横增色彩,把一切行为都变成常规典礼,把一切事都变成堂而皇之的礼仪。有人开始有了疑问:我外祖父的出版商专门出版教学用书,他从不故过任何利用年轻读者的简单头脑的时机。他好像是对一个孩于讲话:他若是砍柴人,他会怎样做呢?两个女儿中他会更喜欢哪一个呢?他会同意对巴拜特的惩罚吗?幸亏,被问的这个孩子不止是我,我害怕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我还是回答了,我的声音很小,谁也听不见,我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安娜·玛丽也一样,她像个头脑非常清醒的盲人,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感到自己是所有母亲的孩子,而她就是所有孩子的母亲。当她读完的时候,我便迅速地把书从她手里拿过来,夹在胳膊底下.连一声“谢谢”也不说就走了。
日子久了,我就迷上了这种使我感到超脱自己的轻松游戏。莫里斯·布绍尔以大商店柜台老板为招徕顾客而常有的那种殷勤关心着儿童,这使我感到受宠而得意。我突然喜欢上了这些事先编造好的故事,而不再喜欢那些临时拼凑的玩艺儿。我对字句的严格连贯性开始敏感了:每次读书时,老是同样的字句不断重复,而且按同样的顺序重复,我听了上句等下句。在安娜·玛丽的故事里,所有的人物都是得过且过,任人摆布。就像她自己的遭遇那样,各有不同的命运。而我却像是在教堂里望弥撒,那些同样的名字和事件翻来覆去,永无休止。
我那时嫉妒妈妈,决心取代她的角色。我拿到一本名叫《在中国:一个中国人的苦难》的书,来到了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在那里,我高高地坐在一只折叠式的铁床上,便装模作样地读了起来。我看着那一行行的黑字,一行也不放过,并且高声讲着一个故事,自己讲自己听,尽量读好每个音节。人们吃惊地发现了我——或是说我让别人吃惊地发现了我——人们惊叫起来,并决定:该是教我学字母的时候了。我热心地学起来,就像一个初学的人。我竟至要求自己单独加课,我拿着一本埃克多·罗的《流浪儿》爬到我的折叠式铁床上便读了起来。对《流浪儿》的故事我都能背出来,我便一半是背故事,一半是连蒙带猜地读了起来,我一页一页地翻读,当我读完最后一页时,我已经会读了。
我欣喜若狂。属于我了,这些书页中的干哑的声音,这些声音我外公用目光使之变活,他听得见,而我那时却听不见!今后,我也要听到它们了,我也要满腹经纶,我也要知道一切。人们允许我在图书室里随处活动,于是我便向人类的智慧冲锋。正是这一点造就了现在的我。后来,我经常听到排犹主义者指责犹太人不了解大自然给人的教益和宁静。我对他们的回答是。“如此说来,我要比犹太人更像犹太人。”农民孩子的那种甜蜜的天真和滔滔不绝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无从找到,因为我从未搬弄过土块,也没有掏过鸟窝。我从未采集过植物标本,也从未用石子打过鸟雀。但,那些书曾是我的鸟和鸟窝,我的家畜,我的牲畜棚和我的农村。图书室就是一面镜子中反映的世界,它有无限的深度,变化无穷,不可预料。我开始了难以令人相信的冒险。我爬到椅子上、桌子上去够书,不怕书会像雪崩似地倒下来把我埋起来。书架高层上的书我好长时间仍然够不到;有些书我刚刚发现就被人从我手里夺走了;还有一些书藏了起来。我拿到书,便读了起来,有时我以为把书放回了原来的地方,却经常是经过一个星期以后才再找到它们。我看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我打开一本画册,看到一张彩色插图,上面有非常难看的昆虫,好像在蠕动。我趴在地毯上通过读封特耐尔、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做枯燥无味的旅行。那些句子和那些东西一样让我看不懂:必须注意观察它们,绕圈子,假装离开、突然回来在它们不戒备的时候逮住它们。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仍保持了自己的秘密。我成了拉佩鲁斯、麦哲伦、瓦斯科·德加玛,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土著居民:在特伦斯用十二音节诗翻译的作品里发现了“欧冬狄毛鲁门诺斯”人,在一部比较文学的著作里发现了“特异反应”人。一些佶屈聱牙的词如“尾音节省略”、“交错配列法”、“无瑕宝石”,还有许许多多难以理解,闻所未闻的怪词儿突然出现在某页的什么地方,只要这些字一出现整个段落都变得支离破碎了。这些艰涩而隐晦的文字我只是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才懂得它们的涵义,甚至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它们构成了我的记忆的腐殖土。
图书室里的书无非都是些法国和德国的伟大的经典作家的作品。也有一些语法书,几本著名小说,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一些艺术品——一幅鲁本斯画、一幅凡·戴克画、一幅迪耶勒画、一幅伦布朗特画——这都是我外祖父的学生送他的新年礼物。这是个狭小的天地。但是大拉露斯词典为我取代了一切:我随意地在写字台后面倒数第二层的书架上拿了一册,上面标有A-Bello,Belloc-ch或Ci-Dmele-Po或Pr-Z等字母(这些字母的组合变成了专有名词,它们各自表示普通常识的某些方面,比如有Ci-D区Pr-Z区,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那个区域的动物和植物,那个区域的城市,伟大人物以及他们参与的战役等等)。我把这册书放在外公用的吸墨纸的垫板上,我翻开这册书,我在里边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真实的鸟类,我在里边捕捉真实的蝴蝶,它们都落在真实的花朵上。人和动物都在里边,活灵活现:那些版画是它们的躯体,那些说明文字便是它们的灵魂,它们的各自独特的本质。实际上,还有一些模糊的草图,多少有点像真实的样子,虽然尚不完美。这可能是因为动物园里,猴子不大像真猴子,而在卢森堡公园里人也不大像真人的缘故。我的精神上是属柏拉图学派式的,习惯从概念客体,我从概念上能发现更多的真实性,而不是在客体实物一样,光是从书本上认识宇宙的:理解它,把它加以划分,给予名目,加以思考,它还是神秘得可怕。我从书本中得到的混乱的个体同现实中偶然发生的事件混合在一起。我的这种唯心论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后来用了三十年时间才得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