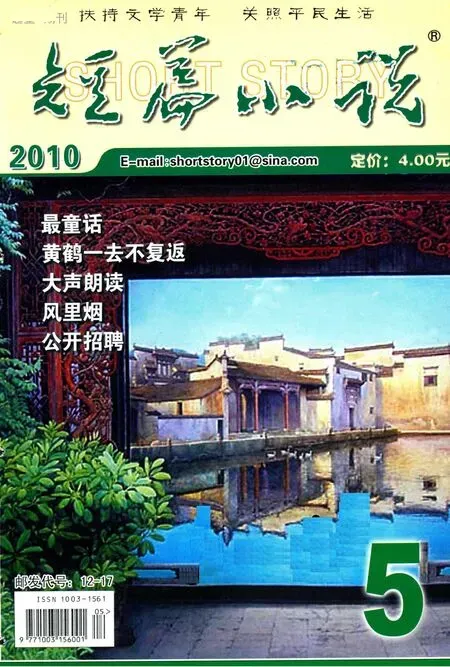叫魂
◎赵丰超
1
姑姑被捞上来时像条水蛭,赤条条地往一团蜷,两条腿直打摽。我跟奶奶一起把她抬到斜坡上,头朝下倒放着。奶奶按着姑姑的两肩,让我掰她的脚。奶奶说,把她拽直,别拧巴了。我想起娘晾床单时的情景,床单太长,一个人拧不动。她喊爹来帮忙,两人各抓一头,爹真是好力气,他往反方向一用力,水就藏不住了,刷啦啦地往下滴。姑姑的脚就像浸饱水的绳子,我使劲一拉,竟发出咯叽咯叽的声音。水往低处流的真理被验证,她的鼻孔和嘴巴泉眼似的,汩汩地往外冒水。期间姑姑抽搐了几下,还要蜷缩,奶奶一屁股坐了上去。
姑姑活了,像条沁药的猫,蜷着身子,咯咯呛着,每呛一次嘴巴里就蹿出一小股液体,深绿色,里面有水草也有淤泥,说不定还有水蛭。水蛭很能活,不怕干不怕淹,据说水蛭能钻进人的血管,在人体里躲猫猫。
夜突然浓起来,除了蛙声,大地好像死了,村庄离我们很远很远,四野空落落的。姑姑不吐了,奶奶这才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大把大把的,也不知是河水、汗水,还是眼泪。她还不放心,把中指伸进姑姑嘴里一阵抠挖,姑姑好像很难受,嘴里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奶奶说,屄妮子,让你死,让你死。每说一句,她就挖得更深一点。姑姑又开始吐,这回吐出的都是水草叶子,吐了一地,谁也猜不到她的肚子里装了多少东西。
河风吹过稻田来到土坡上,有点凉。夜已经深了,天上也没月亮,密集的树林和庄稼全变成墨色,蛙不知疲倦,叫得人烦。姑姑的呕吐声吓着了树上的老鸹,它们飞离巢穴,在树叶间穿梭,发出扑棱棱的声音。那些树很高,我跟堂哥曾爬上去过,本指望掏回几个鸟蛋,谁知快到鸟窝时树枝断了,堂哥一头栽进河里,幸好河里有水。为这事爹打过我一顿,当时要不是姑姑拦着,说不定我的腿就断了。姑姑很疼我,她给我讨过一条小花狗。我和奶奶救姑姑的时候,小花狗也下了河,这会儿它趴在斜坡上晾毛,时不时打几个哆嗦。
姑姑终于吐干净了,她抱着两个膝盖开始抽泣,嘤嘤的。地上的青草真厚,姑姑坐在上面,白鱼一样的背脊随着哭声颤抖,脊骨耸动,在夜幕里泛着鳞白的光。我把我的汗衫给她披上,可是汗衫太小了,只能盖住她的肩膀。
2
北河原本没有名字,因为它从村子北头穿过,大家便叫它北河。其实北河并不大,它是淮河的一条小支流,不知发源于何地,绕过几个镇子拐到淮河去了。但是北河很骚,像个婊子,大屁股扭来扭去,左拐右拐,能把男人的魂勾走,还能把女人带坏。这话是“话匣子”说的,话匣子是个大嘴婆,她的屁股才叫大呢,比磨盘还大。
姑姑投的就是北河。
姑姑虽然活了,却只剩半条命,好几天不吃不喝,也不出门。她惯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抱着膝盖望天,眼神空洞,面无表情。我那时刚好学到《坐井观天》这一课,我问奶奶,姑姑会不会变成蛙?她用手指把姑姑的眼皮撑开,凑近看了看。她说,魂丢了,要叫叫。
我不懂叫魂。奶奶叫我到村外的树林里砍把青扫帚,青扫帚是什么我也不懂。奶奶说,傻子,青扫帚就是带叶子的柳树叉子,大一点,最好打起来像把伞。我点点头,带了一把斧头顺着屋后的小路去了。午后的太阳照着大地,田野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夏蝉吱吱地叫着,野地更野了。小花狗本来跟着我,奶奶却把它撵回了院子。其实我有点怕,怕走夜路,也怕在午后到旷地去,我想要小花狗陪着我,多少算个伴儿,奶奶却不让。她说魂儿太轻,就像一口气,花狗一叫就吓跑了。我听不懂。头几天,我梦见奶奶打小花狗,过门槛时把门牙磕掉两颗。那两颗牙焦黄焦黄的,就像风干的苞谷籽儿。小花狗护疼跑了,一个劲儿地往田野跑,跑到一个坟头上蹲着,像条引颈啸天的狼。我往树林去要经过那座坟。
稻尖子开始泛黄,稻浆的香味飘在田里,再过些日子,就该收割了。稻田像块毯子,小风一吹就起波浪,一波一波往前赶,一直赶到一块土泡子边才停下来。那儿是座长满皂荚树的大坟,隐在稻浪里,像一艘绿船。大人们说坟上长树好,长树就能抓土,坟头越来越大,不用年年包坟,包坟是很累的活儿。
皂荚树不高,乱蓬蓬的,周围一圈藤条耷拉下来像给树穿了件裙子。风一吹,裙角飞扬露出树的身子。树也不嫌丑,疙疙瘩瘩长满了树包。这是野树,没人看,长不成材。但是皂荚的叶子有用,是天然的肥皂,姑姑没有投河之前,去北河洗衣服时总要采一篮子。她把皂荚叶包在衣服里,蘸饱了水,就着石头用木棍捶打,衣服里会挤出一些小泡泡。我把泡泡捧起来使劲吹口气,泡泡散了,一个一个飘起来,幻着彩光,小花狗跳起来追着打。姑姑采皂荚叶子的时候很好看,提着篮子,踮着脚尖,很像散花天女,我在烟盒纸上看过,天女的篮子稍微漂亮一点而已。唯一不般配的就是那座坟,天女怎么可能往坟头上散花呢?
有一回,我和姑姑到坟头上去摘皂荚,突然从皂荚树上跳下来一个男人,我吓得回头就跑,姑姑吓得蹲在地上哭,小花狗一个劲儿地朝他叫。他却嘻嘻哈哈,好像没事儿似的。我折回来找姑姑,他提着篮子爬到了坟头上,姑姑还在哭。后来他提着摘好的皂荚来哄姑姑,说了很多话,我都听不懂,我只知道他学小花狗很像,一会儿在地上打滚,一会儿扭屁股。姑姑打了他几拳。姑姑说,你就是个活鬼。他嘻嘻笑,帮姑姑端着衣盆朝北河去了。这个人是姑姑的同学,住在北河对岸的庄子里,经常游过来吓人。我不喜欢他,小花狗也不喜欢,一见到他就汪汪叫。为了讨好我们,他说他要到对岸偷西瓜给我们吃。他脱下上衣露出健硕的肌肉,扎个猛子下了河,他仰起头,像只长颈鹅,拍着浪花就过去了。河对岸有个老头叫朱家庵,在河沿上种了一块西瓜。我在河这边都能瞧见,朱家庵正在地那头的瓜棚里摇扇子。他胆子真大,迅速摘了几个西瓜扔河里,还站在河边冲朱家庵扭屁股,扭得真丑,像头发情的牛犊子。朱家庵从瓜棚里出来,捡起一个土坷垃撵他,他还在扭,边扭边喊,朱老头,我偷你瓜了,过来抓我,谁不抓谁是驴养的。朱家庵快到他跟前时,他像条鲶鱼,一头扎河里去,推着几个西瓜,赶羊似的,不一会就到了河这边。朱家庵气得直跺脚,却只能望河兴叹。
他把西瓜捶开,递给姑姑,姑姑甩手扔河里了。她说,偷来的西瓜,谁吃你的?他还在嘻嘻笑,小花狗又朝他汪汪叫。
我爬到柳树叉子上回头看,村庄很远很远,有两条老黄牛在村口的溪边吃草,牛背上站着两只老鸹,呆呆的,好像在打盹。我几斧头就砍下一把青扫帚,树枝上还粘着蝉哩。往回走时,我的背脊里汗津津的,不敢朝皂荚树那儿看,我怕坟头上真蹲着一条引颈啸天的狼。
3
奶奶找来两个去年的苞谷棒子,要我把苞谷籽儿褪下来。我坐在门槛上,一圈一圈褪,苞谷籽儿就像剥落的牙齿,整齐而清脆地攒在手心里。我把苞谷籽儿递给奶奶,奶奶蹲在地上细数着,我不知道她上过学没,反正数起来很费劲——用根小木棍一粒一粒拨开,共数出二百粒苞谷盛在白瓷碗里。她说,你再数一遍看看对不。我接过碗开始数,一粒一粒翻到地上。
对了,正好二百。我把苞谷籽儿重新盛进碗里递给奶奶,她掂掂白瓷碗,有几粒不成样子的,她看不上,换了。
她说,别弄错了数儿,到时候我叫一声你跟一声,跟完丢一个籽儿,丢完就停,可不能多了。
我问,多了咋样?
奶奶说,多了不灵。
我们等了一会儿。奶奶也不说话,我问她几时开始,奶奶说还早,天黑了才灵,你去把水缸灌满。
傍晚,北河边最热闹,提水的不止我一个人,女人们也在那。北河边有很多石头,大的有磨盘那么大,小的就像鸡蛋鸭蛋鹌鹑蛋。常到河边洗衣服的女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石头,她们坐在石头上,一边捶衣服一边笑,鬼知道她们笑些啥。我舀水时认出其中一个女人是话匣子,她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侧脸贴在水面上洗头。河水打湿了她的青色的粗布裙子,薄布裹在她的身体上,露出轮廓清晰的大屁股。她背对着我,她说,你们知道她为啥投河吗?她捋了捋滴水的头发说,肚子被搞大了,就搁这儿。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块苞谷地。她说,那娃子还怪有劲儿哩,从河里把她抱到那儿,不知道踢倒几棵苞谷。我看得真真的,还以为牛犊子在里面祸庄稼哩!有个女人笑她,你咋看恁清?她说,不信你去苞谷地看看,松土上还留俩屁股蛋子戳的坑呢!
水缸满了。奶奶把一块硕大的缸拍子盖上,又在拍子上压了两块石头。水缸上沁满了水珠。
我说,缸出汗了。
奶奶说,出汗好,汗出完命就有了。
缸肚子圆鼓鼓的。靠近地面的深褐色缸圈上趴着一条水蛭,蠢蠢地爬着。
我问奶奶,姑姑肚子大了吗?
奶奶朝我后脑上打了一下,瞪着我,谁说的?撕烂她的屄嘴。
话匣子说的,我说。
奶奶叫我把青扫帚洒上水,又把姑姑的一件裙子系上去,青扫帚更像一把伞了。太阳转到西边去了,小花狗趴在门槛上吐舌头,蚊虫在它头顶上打转,任它尾巴摇来摇去也赶不走。奶奶在磨菜刀,嚯嚯的。她说,给我抓只鸡。天快杀黑了,鸡都缩在笼顶上,我随手抓了一只。我从没有叫过魂,也不知道鸡的用处。奶奶接过鸡,在鸡脖子上拽下几撮毛,手起刀落把鸡杀了。她把鸡血滴在卫生纸上,纸卷就像个血喇叭,啪嗒啪嗒往下滴血。她没有说话,径直朝村北去了。我跟着她,小花狗跟着我,小花狗嗅到了鸡血的腥甜,焦躁地喘气。
女人们从河边回来,有的端着衣盆,有的挑着水桶,稀稀拉拉地往村里走。话匣子还在说话,看样子一路都没消停。她摆着大屁股,两个脯子一跳一跳的,就像俩兔子。奶奶迎上去说,大屁股你给我站住。奶奶本来有些佝偻,这会儿不知哪来的力气,一下子站直了,甩手把沾满鸡血的卫生纸掷了出去。卫生纸不偏不倚地贴到话匣子脸上,还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可见鸡血蘸了多饱。
肚子大了身上咋还来事儿?你给我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就别走。奶奶指着血淋淋的话匣子,说起话来像座山神。话匣子一脸狰狞,一手抹脸上的血,一边学鬼叫。大概她身上一辈子也没来过这么多血,话也没说,她甩着两片大屁股跑了。
奶奶说,我看你屄嘴比屁股还大哩。
4
稻田像块大毡子,平坦得很,绿里泛黄。幸好视线尽头的地方有一排山墙似的大树,不然根本分不出稻田的边际。太阳放完热气,漫过大树的杪子下山了,树的巨大的阴影铺满了稻田。天刚杀黑,热气渐渐消退,院子里朦胧一片,小花狗衔着苞谷梗在院子里玩,一会跳到碾盘上,一会钻进鸡笼里。
从院门楼里往外看,庄里零星地散着几户人家,相继都点了灯,爹和娘下地还未回来。奶奶在屋里给姑姑喂饭,可能姑姑还是不张嘴,我听见当的一声,奶奶好像把碗摔了。过了一会儿,奶奶出来重重地坐到堂屋前的石阶上。她说了一句谚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坐在院门下的木槛上,小花狗从我腿上跳过去,引得蚊虫都来围攻我。我突然想起水缸上的那条水蛭,就跑过去抓住它,水蛭也怕,很快缩成一个小球球,像块黏糖,既软又韧。为了弄死它,我从扫把上折了根竹签,捅进它的肠道,再反过来一捋,使劲把它扯直,它再也缩不成球球了。
奶奶说,走吧,天要黑了。她起身朝青扫帚走去,我把串着水蛭的竹签插在院门口的沙土里,慌忙捧起白瓷碗。
奶奶似乎长了力气,一下把青扫帚扛了起来,也不等我,起身就走。我连忙跟过去,我们从屋后绕过去,顺着田埂往北走。走之前,奶奶叫我把小花狗关进了院子。
稻子长得真好,这几天正在抽穗子。稻叶从田里漫出来,显摆似的,在田埂上互相握手,本就狭窄的田埂被挤占了,露水已经爬上稻叶子。越往旷地里走,路就越窄,天也越黑。奶奶还好,我个子太矮,稻穗超过了我的肩膀,从稻叶里挤过去,胳膊腿都被稻叶子剌出了红道道。我把湿透的裤管往下拽拽,抬眼奶奶却走远了。她扛着青扫帚,真像打着一把怪伞。那件月白色的裙子,被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像块诡异的幡。
天空蓝汪汪的,稻田一眼看不到边,我捧着碗慌忙跟上奶奶,不敢回头看。所过之处,稻叶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跟在身后似的。
姑姑投河的地方离村子很远,我们在稻田里转了两次弯才看到河边的几排大树。这些都是白杨,直挺挺的,连在一起像道墙。稠密的树叶挡住了本就微弱的天光,只有几只忽明忽暗的萤火虫在树林里闪烁,发出幽绿的光。借着这点微光,我发现有株白杨上起了个包,黑黢黢的,像山鬼脸。我扯着奶奶的衣角,紧跟在她背后,不敢回头看,也不敢看向河对岸,对岸更阴暗。
终于到了姑姑投河的地方,奶奶放慢了步子。
奶奶说,萍儿耶,来家……
我说,来家了。
这是奶奶事先教给我的。说完这句话,我从白瓷碗里捏出一粒苞谷丢进河里。借着微光我朝河面看去,本来平静的河水被点破了皮,漾起一圈圈细波迅速地扩散开去。我能听到苞谷籽儿入水时的脆响,它们肯定成了鱼儿的美食。刚到夏天的时候,我用蚯蚓在这钓过虾,这条河里有很多大草鱼,我亲眼见过。奶奶喊到十几声的时候,河面有了动静。我指着河面喊,奶奶,鱼。大草鱼搅动尾巴,正在抢食苞谷籽儿。谁知奶奶没看,回头给我一巴掌,不甚响亮,却吓我一跳。她没有说话,也不让我说话,她继续叫。
我们顺着北河往前走,越走越远。夜风有点凉,风吹树叶和稻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奶奶走得很慢,她把声音拉得老长,声音不大却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她一叫,我就觉得河面好像变宽了,大地变广了。夜更浓了,村庄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
萍儿是我姑姑的名字,也是一种水草。
——基于《全元文》的考察